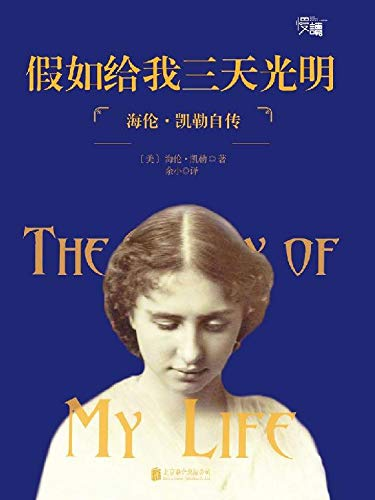張傑
不知從何時起,每每身體有所不適的時候,總自發恐懼死神的降臨。胃炎帶來的折磨已熬半月有餘,絲毫不見痊癒的跡象,這使我愈加陷入身患絕症的臆斷裏不能自拔。於是,對於論文完成的進度,我開始不自主地推遲,雖然置身在大埔墟的自修室,依然不曾強迫自己多看一眼攤開的作業。
廣福道在落日催促下,布滿趕路的人流,我行在匆忙的暗影中,感受不到歸家的幸福,腦海湧現的只是諾大的「空」,柔奴說,「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吾鄉」是縱然你離開二十年後推門再回來,依舊不會覺得陌生的地方。對於此時的我而言,香港暫時還未讓我感到心安,唯有在模糊的記憶中努力找尋慰藉。 外婆手搖著芭蕉扇,外公腳踩著碎磚路,我越過鄰家黃杏的飄香,縱身激起一地的塵土,我瞪圓了雙眼,順著身後他們爽朗的笑聲回望,只見那目目慈祥的投射,映在日日桌面發黃的舊照中。父母打小不在身邊,陪伴我的只有他們。春節攜手燃放的煙花,怎能煙消雲散?暑假一起敲開的西瓜,怎能沖淡嘴角?中秋牽手沐浴的流光,怎能溢出瞳孔?春天我舞著外婆為劍弝編織的蘭纓,幻想騎著白馬隨鷹佇立樓蘭;冬日我推著外公為雪人安裝的輪椅,夢想帶著「夥伴」隨風飄向遠方。如今時光逝過了二十年,我卻沒有膽量叩開故鄉的門,我怕那些回憶會趁著開門的縫隙溜走,猶如早已離開的外公、外婆,再也無法觸摸。
有人說,當我們開始追憶之時,恰是人老之刻。稀薄的髮絲,褶皺的容顏,臃腫的身形,昏花的眼神,老杜三十已過長嘆老矣,我亦何嘗不是?功名宜早,可走過八千里路的雲和月,一切還是塵與土,不是世人都有髯蘇「休將白髮唱黃雞」的豁達。

白粥的香滑,炒麵的爽口,灶臺外公、外婆年輕的笑臉,不見炊煙熏酸的眼,我努力控制將要落下的淚,在碗底的燈光裏打轉。張平子對故鄉滿腔而作的〈南都賦〉,我沒有能力「把控」,只想到年少時拜讀郁達夫的《沉淪》,卻不願也沒膽如先生那樣直面自己病創的靈魂。
我拖著疲憊的軀殼,昏沉的大腦盯著模糊的文獻,不斷用力的擤鼻涕及清嗓子,來提醒還未完成的作業。我無法逃避拖延的作業,也無法逃避逝去的外公、外婆。也許死亡並不可怕,僦居也並不難堪,可怕的是我的心似乎並沒有安處,難堪的是我的夢也並未有兌現,我想回到那遠去的故鄉,再看一眼外公、外婆的青冢,再回首一抹他們在夕陽散下的身影。
劉恆遺詔有言:「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如果天地真的存在另一個空間,我相信日後可以在那裏與外公、外婆再相見,與那些逝去的親人再相見。望著樓下企立的夜燈,我想到夜晚沿著林村河回來的路上,感慨的幾句話:
穿過沉默的林村河
看不到信宿的漁夫
怎問,夔州的老翁可好
鼓枻走後的大夫
是否拂去懷中的沙?
風暗暗地回答:這一地逝去的薔薇
這一地的薔薇,一院的香
是外公、外婆蒲扇舞動燎著的沉香
是薄霧爬滿他們歲月的離傷
我曾在長安的樓臺相思
他們卻在江南的津渡斷腸
試問這世間能有什麼難忘?
不過是音容的濛濛,煙水的茫茫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張傑簡介:香港都會大學哲學碩士在讀,現作杜甫在香港的接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