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為忻
有一本書我一直放在枕邊:海倫.凱勒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
海倫·凱勒以失明之身,在她《假如給我三天光明》這本書裏,告訴我們一種活法,叫做「向死而生」。
她以眼睛為比喻,告訴我們,「善用你的眼睛吧,猶如明天你將遭到失明的災難。」她進而認為,如果我們把生活當作像明天就會死去那樣,那,才是人生最好的規則。
海倫·凱勒說:「我擔心我們全部的天賦和感官都有同樣的懶惰的特徵。只有聾人才珍惜聽覺,只有盲人才體會重見天日的種種幸福。這種看法特別適用於那些成年後失去視覺和聽覺的人。但是,那些在視覺和聽覺上沒有蒙受損害的人,卻很少能夠充分地利用這些可貴的感官。他們的眼睛可都模模糊糊地吸收了一切景色和聲音,他們並不專心,也很少珍惜它們。我們並不感激我們的所有,直到我們喪失了它。我們意識不到我們的健康,直到我們生了病——自古以來,莫不如此。」
海倫·凱勒深切體會的,其實是「無常」兩個字。
有一篇空難的報導,十分貼切地演繹了海倫.凱勒所說的「無常」:
「每一名登機的乘客臉上都掛著笑容。這笑容在飛機起飛後的十二分鐘後,卻變成了驚恐和失措。
飛機無休止的俯衝與攀升,機尾爆炸燃燒的巨響與煙霧、行李架散落、氧氣罩彈出。
人們呼吸不暢、孩子哭喊、女人尖叫,飛機上的五百二十人陷入了絕望。
在空中垂死掙扎了三十分鐘後,飛機如同一隻失去翅膀的雄鷹,一頭栽下,埋入山林。墜落。爆炸。燃燒。隨後引發了山火。是啊,我們總懷著對生活的美好企盼。可這世間,實在有太多的猝不及防。前一天還漂亮整潔的大飛機,轉眼間成了滿地殘骸。
在飛機墜入山林的最後一刻,有人祈禱,有人親吻,有人從容,有人哭叫…… 這混亂的一切在飛機墜落起火後歸於沉寂。
山林死一般的沉靜,指揮臺的顯示器上代表這家航班的小紅點永遠消失在了歷史的塵埃裏……飛機上的幾百人全部遇難。」
讀這樣的文字,你可以想像,當遠離家鄉的遊子、攜子帶女的父母、白髮蒼蒼的老人急不可待地踏上這本可以載著他們飛向故土的航班時,他們當中,誰會想到,剛剛登機前與戀人、朋友那最普通、最尋常的道別,竟會成了今生的永別。
無常!這看似不短的人生,實則充滿無常啊!
我們常常以為一切都來日方長,未來可期,卻耐不住措手不及的意外;我們自認以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做某件事,見某個人,其實這是最大的迷思,最大的障礙,最劇烈的毒。當意外先於明天來臨,我們會捶胸懊惱,為何將時間一股腦地獻給了工作和錢財,卻忽略了我們身邊難得的美好。
當然,睿智的哲學家告訴我們,生和死是一個整體,是生命的一部分,這恐怕是對的。
但對的又怎麼樣?凡夫俗子還是希望生,害怕死。我們說的「斷離捨」,也就是一般的事物,到生命這件事上,大概還是有點患得患失吧。
各種宗教試圖解釋生和死的問題。許多宗教非常細緻地描繪了死以後的情景。我想,這對生活在今生今世的人,對下一生的期望和憧憬,尤其是揚善除惡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對天堂的崇敬和嚮往,對惡的懲罰之害怕,都可以使今生今世變得更有意義。於是我們敬畏生命,敬畏神明。
但沒有一個天堂回來的人,可以向我們訴說,她/他對生和死比較的認識,就像史鐵生所說,這是一個既不可以證偽也不可以證實的事情。
於是,我們大多數人都把人生視為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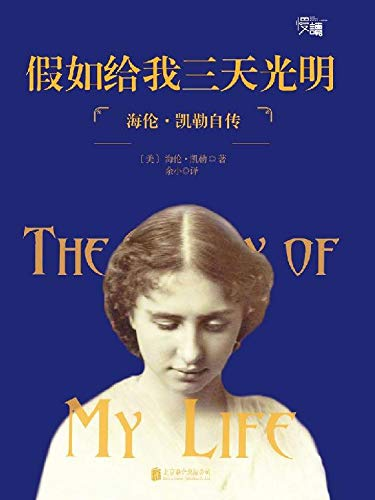
坂本龍一說的對,「因為不知死何時將至,我們仍將生命視為無窮無盡、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許就只發生那麼幾次。曾經左右過我們人生的童年回憶浮現在心頭的時刻還能有多少次呢?也許還能有四五次。目睹滿月升起的時刻又還能有多少次呢?……但人們總是深信這些機會將無窮無盡。雖然我們心裏都明白,有一天,我們一定會死去。」
一般的人總會感覺那一天極其遙遠。尤其是我們處於精神活潑,身體輕快的健康狀況,死亡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我們難得想到它。於是,日子延伸到無窮無盡的遠景之中。我們於是總是做些無價值的工作,幾乎意識不到我們對生活懶洋洋的態度。另一方面,畏懼死亡卻成為天經地義。「死亡」兩個字是人們連聽都不想聽到的,覺得晦氣,恐懼,想要逃避。
可奇怪的是,人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將時光大把揮霍。遇到心愛的人,不敢上前;與不愛的人假裝幸福;做著不喜歡卻貌似有不得不做的工作;說著口是心非的話語;不敢放肆大哭,不敢開懷大笑,一天一天這樣過。
我們從未意識到,每一個已經變成昨天的日子,其實都是死亡的日子。已經喝過的茶,已經涼去,不再會回到面前;已經消逝的日子不會重演,不再觸手可及。我們每一天,其實都在經歷死亡。
孔子說過,不知生,焉知死?
但應該怎麼「生」,又變得五花八門。
是的,我們每天本來是懷著友善,朝氣和渴望去生活的。但是,當時間在我們面前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不斷延伸開去,這些品質常常會喪失。
要想尖銳地強調生命的價值,恐怕只有抱著「明天就是來生」這種態度。因為知道有完結篇,我們才會在有效期限內特別珍惜!例如一道美食、一趟旅遊、一段生活。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今天晚上就要失明,我們一定會依依不捨地真正欣賞一下每一根青草,每一片雲,每一粒塵埃,每一道彩虹,每一滴雨珠。
有一位哲學家說得好,人在這個世界上大多數時間是稀裏糊塗的,只有到生命的極限時,腦子才會忽然清醒過來。這個道理,常常和我們在遇到大的變故時,才幡然醒悟是一樣的。
當年輕鮮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床邊有換下的襪子,桌上有吃了一半的飯菜,冰箱裏有剩了半盒的牛奶,洗衣機上有未曾洗滌的髒衣,書桌上有看了一半的小說,還有,銀行帳戶上那些冷冰冰的數字……
你會相信柏拉圖說的,「哲學,就是練習死亡!」
我們怎麼提醒自己,生而有涯,好好的活一輩子呢?
我們大家都讀過這樣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裏面的主人公只有一點有限的時間可以活了。有時長達一年,有時短到只有二十四小時。然而,我們總是能很感動地發現,這些註定要死亡的人,如何想辦法度過他最後幾天和最後幾小時。
這類故事使人們思索,很想知道我們在同樣的情況下將會怎麼辦。
有一個九一一的倖存者說:「正因為看到了人生無常的一面,我意識到人生的繁華、苦難、夢想和欲望,在頃刻間都有可能紛紛落下,我的人生軌跡也發生了變化,開始重新思考人生,思考活著的意義。」
我們作為必死的生物,處在這最後幾小時內,會充滿一些甚麼樣的遭遇,甚麼樣的感受,甚麼樣的聯想呢?我們回顧往事,會找到哪些幸福,哪些遺憾呢?甚麼時候,你會覺得名利權情無非是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無論你名聲四海皆知,響徹雲天,也無非是一時獵奇。各種各樣的人,揣著各種各樣的心態唾沫四濺過後,你仍然是你。
其實,你一直是你,只是別人在談論的時候,你忘記了你自己是誰而已。只有死亡,或者死亡的臨近會提醒我們!
面對死亡最坦然的要算是蘇格拉底,他認為生命之所以值得珍惜的,就是因為它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常常練習,把死亡拉到眼前來看,就可能改變這種隨意浪費時間情況。
人的生命是在時間當中表現的。甚至可以說時間就是生命。如何掌握自己的時間,就是如何安排自己的生命。如果沒有把死亡拉近到自己眼前,很容易誤以為時間永無止境,可以讓人隨便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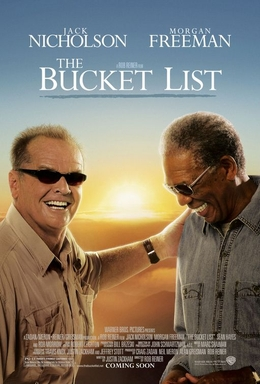
有一部美國的電影,叫「遺願清單」,講的是兩位身患絕症,在醫院裏如何成為好友的故事。重點是,他們仔細斟酌,回首往事,而後各自列下一個願望清單:在離開世界之前,還有哪些事情要做。
兩個人當中,一個很富有,一個很貧窮。那位富有的,頓悟了錢的真正意義,下決心用他的金錢,去幫助那個貧窮的,按照單子上的先後,一條一條地去實現那些多少年來,念茲在茲的計畫,直到各自生命的盡頭。
是的,我們應當常常問自己,假定明天就是來生,我今天要做甚麼。而「我今天要做甚麼」,又與另一個問題相關,那就是,「我到底要甚麼」。
所有的人生,終究歸於這個問題。
不同在於,有人自覺,有人不自覺。自覺的人中間,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不同,就是自覺者各以不同的位置與身分,在考慮我到底要甚麼?其位置與身分,決定其考慮的深度和廣度。
是不是可以根據「我到底要甚麼」而不斷的給自己書寫「願望清單」,不斷地照這個清單上的專案去一一施行。一張清單完成之後,發現自己還在人世,就再來一個清單。
我們讀到許多故事:命運已定的主人公,通常在最後一分鐘,由於遭遇好運而得到拯救。然而,他的價值觀,幾乎總是改變了。他更加領悟了生命及其永恆的精神價值的意義。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活在或者曾經活在死亡陰影中的人們,對他們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賦予了一種醇美香甜之感。
當我們手邊有一杯咖啡,有一杯茶時,要好好享受它。享受它的滋味,享受與我們一同品茶的人,以及周圍的一切:風聲,雨聲,時鐘的滴答聲。
當我們與心愛的人在一起,與孩子在一起,用心去愛他們,全心投入。也記得時刻關愛自己。因為,這一模一樣的時刻,不會再有,過去了的,就永遠過去了。
在你忙碌的時候,在你埋頭趕路的時候,停下來,等一等自己的心和靈魂,靜思自己真正需要的是甚麼,真正缺失的是甚麼,然後,調整自己的方向,再次出發——生命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供我們浪費。
其實,日常生活天天會發生的事情,大和小,很難區分。但是,與生死一比較,這界限就明白了。這就是為甚麼,在生和死的那一刻,人們的腦袋會豁然開朗。往後看,許多事情就輕輕如也。甚麼重要,甚麼不重要,甚麼值得珍惜,甚麼不值得留戀。「練習死亡」的意義,就在於這裏。
也只有碰到生死問題時,有些人才會把一些掛礙放下。
所以,木心說過,人活著,時時要有死的懇切,死了,這一切又為何呢?那麼,我活著,就知道該如何了。
把人生當成你的最後階段,唯一值得努力的目的,是把平凡的一生變成有意義的一生。這實在是因為,生命的變化太快,太殘酷,來不及準備,也無法預料。所有的美好都在當下。所有的變化也變得美好。
願我們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不再懊悔有那麼多的遺憾和來不及,而是可以從容地告訴命運:「這一生我活得很幸福,感謝生命中有你們!」
向死而生,不停地準備願望清單,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生命就會豐滿起來。這,就是為什麼泰戈爾說:
「死之流泉使生的止水跳躍!」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黃為忻簡介:教育:上海財大碩士,日本國際大學碩士,荷蘭Erasmus大學博士。經歷:插隊,進廠,大學(七七),研究生,八六年負笈荷蘭,攻讀博士。九十年代初起在荷蘭任職于荷蘭銀行。有金融專著數本在海內外出版。多篇文學散文、譯文如〈夫妻之間〉,〈改變自己的三星期〉等發表在各種文學雜誌、公眾號,如《讀者》、北美《紅衫林》、《新三屆》、香港《明報月刊》、《香港作家》等。〈在希望的田野上〉知青作家杯一等獎;散文集《昨夜星辰》第三屆東方散文獎;〈童話的世界真美麗〉第四屆中國當代散文精選獎。歐華筆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