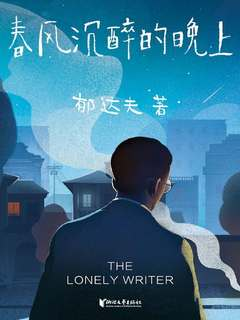孫重貴
生與死,是人生最深刻且不可避免的課題。本人長期以來就這個課題,進行了文學上的探討。其中我特別創作的一首新詩〈曇花〉(此詩於一九九二年發表於香港《新晚報》,後於一九九七年收入本人詩集《香港魂》),試圖以詩歌語言構築深邃的哲學意境,通過曇花瞬間絢爛與凋零的自然特性,投射出對生與死、生命價值、存在意義與審美哲學的獨立思考。
〈曇花〉
不求永恆
只求燦爛
編織一個
美艷的夢
匆匆嫁給
多情的夜晚
剛披上
潔白的婚紗
就踏進
死神的門檻
追求的
已經擁有
何苦爭
生命長短
不嫉妒
山茶紅梅
不羡慕
芙蓉牡丹
那凋謝的香魂
悄悄
與泥土
為伴

創作〈曇花〉表達生死觀有如下特徵與寓意:
一、生死辯證:刹那永恆的詩學重構
詩歌開篇以「不求永恆/只求燦爛」打破傳統對永恆的執念,重構生命價值的評判標準。曇花以「美艷的夢」對抗時間霸權,將「匆匆嫁給多情的夜晚」轉化為主動的生命選擇,暗含存在主義式的決斷——生命的意義不在於長度而在於深度。「婚紗」與「死神門檻」的意象並置,形成戲劇性張力,揭示生與死並非對立而是共生的本質,恰如海德格爾所言「向死而生」,終極價值的實現正蘊含於對消亡的清醒認知中。
二、意象系統的象徵隱喻
本人構建了一套相互映照的意象系統,讓詩歌語言的表現更加突出:
1,婚嫁意象:「多情的夜晚」擬人化為新郎,「潔白婚紗」象徵純粹的生命綻放,將自然現象轉化為浪漫的儀式感,賦予凋零以神聖性。
2,植物對比體系意象:山茶紅梅(經冬耐寒)、芙蓉牡丹(雍容長久)作為傳統審美符號,被曇花主動拒絕,凸顯其反世俗標準的價值取向。這種「不嫉妒/不羡慕」的宣言,實為對主流成功學的詩意顛覆。
3,泥土歸宿意象:「香魂與泥土為伴」化用「落紅不是無情物」,但更強調主動選擇——凋零不是悲劇,而是生命完成式後的安然回歸,暗合中國哲學「塵歸塵」的循環宇宙觀。
三、語言藝術的減法美學
詩歌採用近乎箴言的凝練句式,與曇花轉瞬即逝的特性形成形式呼應。階梯式分行製造視覺停頓(如「悄悄/與泥土/為伴」),模擬花瓣飄落的節奏感。否定詞「不求」「不嫉妒」「不羡慕」的重複使用,形成決絕的語勢,而「何爭」的反問句則將說理轉化為頓悟,體現東方哲學的超脫智慧。在生死交織的故事中,找尋生命的光輝與永恆。
四、文化原型的現代轉化
本人重寫了中國古典文學中「曇花一現」的悲情敘事,將其從「紅顏薄命」的哀嘆轉為存在主義式的頌歌。西方哲學中尼采「燃燒殆盡」的超人精神與莊子「安時而處順」的生命觀,在此達成奇妙融合——既頌揚刹那輝煌的狄奧尼索斯精神,又保有華夏順其自然的哲思理性。深刻反思生命的價值與意義,喚醒人們對時間的加倍珍惜。
五、現代人的精神寓言
在當今快節奏時代,本人希望透過文字,讓這首詩成為生死的某种啟示錄,讀者在面對生死時能夠坦然接受,並珍惜當下,活出真實而有意義的生活。曇花的選擇隱喻著現代人生死觀的破解之道:當永恆不可企及時,唯有聚焦當下的生命強度,在有限中開拓無限。一位評論家指出:〈曇花〉其美學價值不僅在於精準捕捉植物特性,更在於構建了一個超越時空的生命詩學——消亡不是終點,而是價值完成的最終儀式。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孫重貴簡介: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國際華文詩人協會會長,《世界華文詩報》總編,創作出版專著三十餘部,五百萬字。作品發表於各國百餘家報刊,入選中外選集及教材。榮獲「冰心兒童文學獎」五次及「全國十佳詩人」、「國際華文詩壇終身成就獎」和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文學藝術成就獎」等百餘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