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重貴
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一部抗戰史,結緣兩座橋。全面抗戰史上有「北起盧溝橋,南止深河橋」之說。然而,現今盧溝橋及「七七事變」家喻戶曉,深河橋和「黔南事變」卻鮮為人知。
據貴州《獨山縣誌》記載:深河橋「距獨山縣城北面九公里,建於明隆慶五年(一五七一)。橋高十六點三五米,跨度十二米,橋寬五點七米,全長三十七米,橋墩高度九點五米」。眼前的深河橋是一座二戰後重新修復的石橋,然而當年這裏卻是廣西進入大西南的要衝和通往貴陽和陪都重慶的唯一孔道,在二戰期間是西南鐵路終點站、黔桂公路的必經之地。
深河橋周邊的地理環境十分險要,河流深切峽谷,兩岸山勢陡峭,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萬里遐征」,於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三月二十七日,經廣西南丹入黔至此,對這片深谷和深河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地在日記中記道:「有澗自東谷走深崖中,兩崖石壁甚陡,澗嵌其間甚深,架石其上為深河橋。」行走天下的徐霞客,也被貴州高原的深深河谷和架石其上的深河橋深深震撼。
二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為擺脫軍事上的不利局面,日軍發動了侵華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攻勢——「一號作戰計畫」,準備在中國戰場打通被分割的華北、華中和華南佔領區,妄圖以此打通縱貫南北的大陸交通線來挽救敗局。
日軍集結了五十萬重兵,自一九四四年四月起先後發動了豫中會戰、長衡會戰和桂柳會戰,在打通平漢、長衡線,攻佔鄭州、洛陽、長沙、衡陽等戰略城市之後,日本侵華派遣軍第六方面軍以橫山勇的十一軍、田中久一的二十三軍,共八個師團、兩個旅團的十八萬兵力,於九月上旬從湖南、廣東分兵三路,對桂林、柳州、南寧等地發起攻擊。
同年十一月,桂林、柳州、南寧相繼失陷,十一月中旬,日軍在佔領廣西宜山后,為擴大戰果,趁貴州防務部署尚未就緒,派兵向黔南進犯。日軍第十一軍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布「向獨山、八寨追擊」命令,並由日軍第三和第十三師團分兵三路入侵貴州黔南,逼近貴州省府貴陽,陪都重慶為之震動。
蔣介石急調第二十九軍由四川奔赴貴州救援,先頭部隊第九十一師在師長王鐵麟將軍率領下,於十一月二十八日乘車抵達獨山,立即在黑石關、白臘坡、甲撈河一帶布防,構築工事,阻擊沿黔桂公路北犯之敵。隨後二十九軍軍長孫元良親臨獨山,與王鐵麟師長協同指揮對日作戰,打響了「獨山戰役」。
三
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原戰役後,二十九軍奉命由陝南調往四川整補,剛於十月二十六日在合川集結,又被緊急調往貴州布防。該軍於十一月三日奉命出發,徒步六百多公里到達遵義,隨後轉乘汽車進入黔南,先頭部隊九十一師於十一月二十八日進抵獨山。
獨山,明代萬曆五年(一五七七)知州歐陽輝置建州府,是座歷史古城。抗戰時為貴州第二公署駐地,一九三四年修通的黔桂公路,一九四三年修通至都勻清泰坡的黔桂鐵路,縱貫縣城南北。城郊建有駐華盟軍飛虎隊的西南抗日空軍前沿基地——前進飛機場。獨山既是當時黔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保衛雲、貴、川、康、藏大後方五省的軍事重鎮。自一九三九年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四分校、汽車兵團、傷兵醫院等八十餘家中央和地方機關、團體陸續遷來,加上過往軍隊、難民,獨山城聚集人口約十八萬人,一度繁榮熱鬧,時人稱之為「小上海」。
九十一師由於匆匆調防,兵力未獲補充,兵員僅二千五百人,而實際投入戰鬥的不足千人。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一時,該師搜索部隊在獨山下司與沿黔桂公路北犯之敵先頭部隊步騎三百餘人接觸,隨即展開激烈戰鬥。在敵後續部隊增援下,搜索部隊退回黑石關主陣地。十二月一日,日軍先頭部隊一〇四聯隊,混入難民群中侵入我黑石關警戒陣地,未幾即展開血戰。戰鬥直至十二月二日拂曉,敵以數倍之兵力猛攻,突破黑石關要隘,然後採取迂回戰術,由黑石關兩側突入獨山縣城,並妄圖回頭圍殲該師。為避免造成更大傷亡,九十一師由黑石關經白臘坡、甲撈河陣地向平塘方向突圍。之後九十一師主力陸續在平塘卡蒲、擺卡一帶構築陣地防守,其搜索連則在深河橋北岸阻擊日軍。
為阻止日軍繼續北犯,十二月二日下午盟軍炸毀深河橋。這座長度不足四十米的古橋,竟然成為日軍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礙,一舉阻斷敵人進犯的步伐而成為日軍侵犯中國領土的「嘆息橋」。當年參與炸橋的美國盟軍上尉富蘭克回憶道:「要阻止日軍北犯,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炸毀深河橋。我們把橋炸掉幾分鐘後,日軍的先頭部隊就來到了深河岸邊。深河橋被炸斷後,日軍行動受阻,之後就在深河橋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深河橋阻擊戰。」

作者考察深河橋
四
日軍左路主攻部隊為第十一軍十三師團的步兵第一〇四和一一六聯隊,山炮兵第十九聯隊,工兵第十三聯隊及輜重兵第十三聯隊,共四千餘人,經河池、南丹向獨山進犯。中路和東路分別為日軍第三師團的主力三十四聯隊、六十八聯隊和第六聯隊,分別由廣西思恩(今環江縣)經黎明關向荔波和三合(今三都縣)向八寨(今丹寨縣)、都勻進犯。
進攻獨山的第十三師團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的一個甲種師團,編入華中方面軍的上海派遣軍,由松井石根統領,下轄第三、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六和第一〇一師團,參與攻陷南京,屠殺中國軍民三十萬,犯下了滔天罪行。隨後日軍所屬部隊繼續向華中和華南地區進犯,第三和第十三師團於一九四四年九至十一月參加桂柳會戰,後入侵貴州。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這兩支「不可一世」的日軍師團於南昌被繳械,在中國戰場上以戰敗者的身分正式投降。
當年在獨山境內,中國軍隊對日軍層層抵抗,在深河橋展開了一場生死存亡的阻擊戰。進入獨山的第十三師團的日軍雖然抵達城北的深河橋頭,因遭到二十九軍九十一師的頑強抵抗,不僅無法再前進一步,最終也沒能越過深河橋。橫行中國半壁河山的日軍在名不見經傳的獨山深河橋遭遇了侵華以來的「滑鐵盧」,深河橋成為日寇望洋興嘆的「天塹」。從此,深河橋被譽為「貴州抗戰第一橋」。
由於日軍入侵獨山等地的兵力僅有四千餘人,戰線拉長,給養不足,又遭到中國抗日軍民和盟軍的不斷反擊。日本侵華派遣軍第六方面軍首腦為防腹背受敵,傳令日軍十一軍軍部,十二月二日當晚向入侵黔南的步兵第三和第十三師團下達退卻命令。十二月四日黃昏,第十三師團日軍開始反轉,放火焚燒獨山城區房屋、工廠、被服、衛生、糧秣倉庫、彈藥庫、桐油庫、汽油庫,車站、機車、車皮,隧道、鐵路橋、公路設施等。爆炸聲接連不斷,獨山變成一片火海。
日軍所到之處,四處燒殺擄掠,無惡不作。時稱「小上海」的獨山縣城頓時火光衝天,大火連續燒了七天七夜,城內一片焦土。僅獨山縣城被殺死、凍死、餓死的民眾達一萬九千八百多人,縣城被燒毀房屋有一萬六千多幢,給當地人民生命財產帶來了巨大損失,一座繁華的古城成為廢墟,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黔南事變」。
慘案發生後,馮玉祥將軍夫人李德全女士,作為國際紅十字會成員來到獨山慰問,見此慘象悲憤寫道:「一夕流言閭巷空,風號月暗夜飛紅;卻驚鐵騎來何速,尚有雄兵勢豈窮。幾輩名成焦土後,萬家淚落冷灰中;此情那堪重追憶,相對唏噓你我同。」
五
在我愛國軍民同仇敵愾的打擊下,日軍第十三師團主力於十二月四日夜開始退出獨山城。十二月七日,二十九軍九十一師向獨山進發,於十二月八日拂曉收復獨山,緊接著該師又乘勝追擊收復了上司、下司、麻尾。日軍第三師團入侵之敵被打擊後,也相繼由丹寨、三都、荔波倉皇退出黔境。至十二月十日貴州全境收復,進而又收復廣西南丹,向河池攻擊挺進。
「黔南事變」終於以中國軍民的勝利,日本侵略者的失敗而載入了抗戰史冊。而全國軍民的全面抗日功績,也在由盧溝橋到深河橋的戰鬥歷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傳奇一頁。
自「獨山戰役」後,日軍入侵西南腹地的戰略計畫徹底破滅。日軍從獨山深河橋撤退以後,便節節敗退,直至次年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告無條件投降。深河橋因而成為侵華日軍敗亡的歷史轉捩點,這裏是抗日戰爭中有著特殊和重大意義的地方,全面抗戰史上因此有「北起盧溝橋,南止深河橋」之說。
歷史並不如煙,深河橋——這座充滿傳奇色彩的「貴州抗戰第一橋」,歷經風雨和滄桑,穿過歷史的雲煙,至今依然驕傲地挺立在中華大地上,挺立在貴州省黔南州獨山縣大山裏,成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一座豐碑。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孫重貴簡介:香港中華文化總會副理事長、國際華文詩人協會會長,中外散文詩學會副主席、香港散文詩學會會長,《世界華文詩報》總編,《香港散文詩》主編,歷任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和四間大學客座教授,創作出版專著三十餘部、五百餘萬字,作品發表在《香港文學》、《香港作家》、《人民文學》、《詩刊》等百餘刊物,入選眾多中外選集及教材。其散文作品別具特色,發表五十餘萬字並多次獲大獎。榮獲「冰心獎」五次及「全國十佳詩人」、「全國十佳散文詩人」、「國際華文詩壇終身成就獎」、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文學藝術成就獎」等百餘獎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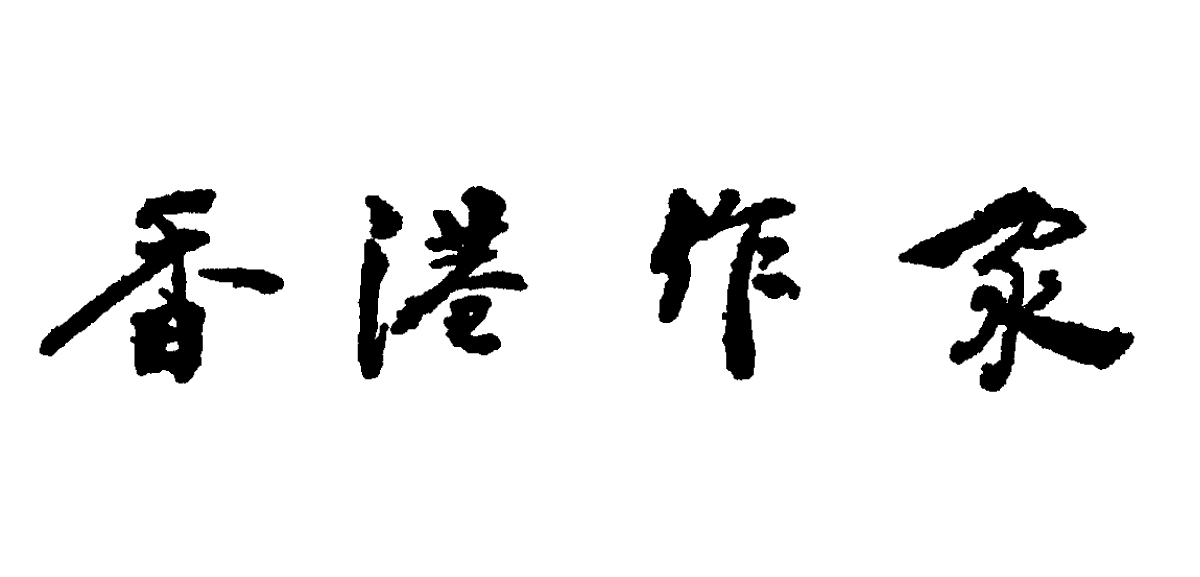






贵州深河桥让沿途人民躲过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军事入侵,真的是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