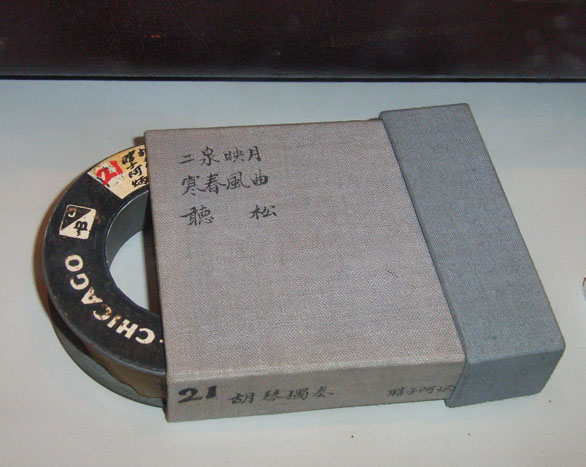林釗勤
三月的風還帶著料峭,窗臺上的綠蘿卻悄悄抽了新芽。嫩得能掐出水來的綠,卷著的葉尖像嬰兒攥緊的小拳頭,一點一點舒展,像是在試探著和這個世界打招呼。我蹲在窗邊看了許久,忽然想起鄰居家上個月剛出生的寶寶,裹在米白色的繈褓裏,眼睛還沒完全睜開,卻會在聽到媽媽聲音時,無意識地歪著小腦袋,嘴角漾開一絲極淡的笑意。那一瞬間,我忽然懂了人們為甚麼總說「新生是光」——它不是刻意的照亮,而是一種帶著溫度的、蓬勃的「在」,是生命最本真的宣告,也是生與死這道永恆命題裏,最柔軟的開篇。
生,從來都不是一個抽象的「開始」,而是無數個具體的、帶著煙火氣的瞬間。媽媽總愛講我出生時的模樣:萬物生長的初夏,她躺在床上,聽見接生婆抱著我出來時說「哭聲真亮,將來肯定是個結實的娃」。後來我翻家裏的老相冊,有一張照片是我滿月時拍的,裹著紅色的小薄棉衣,臉蛋圓滾滾的,手裏攥著一塊長命鎖,眼睛亮晶晶地盯著鏡頭,彷彿已經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那時的我不會知道,「生」會意味著甚麼?會意味著第一次學走路時摔得膝蓋發紅,卻還是咬著牙要再試一次;會意味著第一次背著書包走進校園時,既緊張又期待地攥緊書包帶;會意味著第一次收到朋友的禮物時,心裏像揣了顆糖,甜得能溢出來;也會意味著第一次面對挫折時,躲在被子裏偷偷哭,卻在第二天早上依然願意對著鏡子笑一笑。
這些細碎的、甚至有些笨拙的瞬間,構成了「生」的底色。去年夏天,我去鄉下老家小住,看到田埂上的孩子追著蝴蝶跑,褲腳沾滿了泥點,卻笑得比陽光還燦爛;看到老人在院子裏摘豆角,摘完了就坐在門檻上擇,一邊擇一邊和路過的鄰居聊天,聲音裏滿是家常的暖意;看到父親在菜園裏澆水,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水珠落在青菜葉上,折射出細碎的光。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生」的意義從來不是轟轟烈烈的壯舉,而是在這些日常的褶皺裏,認真地活著,認真地吃飯,認真地聊天,認真地看著太陽升起又落下,認真地對待每一份小小的喜悅與感動。就像田埂上的野草,哪怕被風吹倒,也會在下一場雨過後,重新挺直腰杆;就像院子裏的老母雞,每天都會準時下蛋,然後咯咯地叫著,彷彿在宣告自己的小小成就。這些平凡的生命,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詮釋著「生」的力量。
可「生」的另一面,是「死」。這個字眼曾在我童年時顯得格外遙遠,直到祖父的離開,才讓我第一次真切地觸摸到它的溫度。祖父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一輩子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他的院子裏種著一棵老梨樹,是他年輕時親手栽下的。每年春天,梨樹上會開滿白色的花,風吹過的時候,花瓣像雪一樣落下來,落在祖父的肩頭,落在他翻土的鋤頭把上。我小時候總愛纏著祖父,讓他給我摘梨吃。祖父的手很粗,常年握鋤頭的掌心有厚厚的繭,卻總能精准地避開枝椏上的刺,摘下最甜的那顆梨,遞到我手裏時,繭子蹭過我的掌心,有點癢,卻暖得很。
祖父走的時候是秋天,梨樹上還掛著沒摘完的梨,黃澄澄的,卻沒人再去碰它們。那天我站在梨樹下,看著風把葉子吹得沙沙響,忽然覺得整個世界都安靜了。再也不會有人在我放學回家時,坐在門檻上等著我,手裏拿著剛摘的梨;再也不會有人在我犯錯時,不罵我,只是默默地帶我去菜園裏澆水,說「莊稼和人一樣,得慢慢長,急不得」。我蹲在梨樹下哭了很久,直到外婆走過來,輕輕拍著我的背說:「你祖父沒走,他只是換了個方式陪著我們。你看這棵梨樹,每年都會結果,他還在看著我們呢。」
後來的每年春天,老梨樹依然會開花,秋天依然會結果。家裏人摘梨的時候,總會想起祖父,想起他當年種樹的模樣,想起他遞梨時溫暖的手。我慢慢明白,「死」從來不是生命的「消失」,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延續」。就像祖父種的梨樹,雖然他不在了,可梨樹還在,每年都會用花開和結果,提醒我們他曾認真地活過,曾用自己的方式愛著這個家;就像那些逝去的親人,他們曾說過的話、做過的事、給予過的愛,會變成我們記憶裏的光,在我們遇到困難時,在我們感到孤獨時,悄悄給我們力量。

去年冬天,我在醫院陪護生病的老人,看到過一位老人安詳地離世。那位老人的兒女都守在床邊,握著他的手,輕聲說著話,沒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平靜的告別。老人走的時候,窗外的陽光正好照進來,落在他的臉上,顯得格外溫柔。後來我聽護士說,老人是位老教師,一輩子都在教書育人,退休後還經常給社區裏的孩子輔導功課。他走之前說,自己這一輩子沒甚麼遺憾,教過的學生遍佈各地,看到他們有出息,比甚麼都開心。那一刻我忽然懂得,「死」的坦然,源於「生」的充實。當一個人認真地活過,認真地愛過,認真地為這個世界留下過一些美好的東西時,面對「死」,便不會有太多的恐懼與遺憾。
就像秋天的落葉,春天的時候努力地生長,夏天的時候為人們遮擋陽光,秋天的時候雖然會落下,卻會化作泥土,滋養著明年的新芽。生與死,從來都不是對立的,而是生命循環中,相互依存的兩個部分。沒有「生」的鮮活,便不會有 「死」的厚重;沒有「死」的沉澱,便不會有「生」的希望。就像夜空裏的星星,有的星星會熄滅,可新的星星又會亮起,它們在宇宙中閃爍,構成了永恆的星空。
現在的我,不再像小時候那樣害怕「死」這個字眼。我會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週末的時候,陪父母逛逛街,聽他們講過去的故事;過節的時候,和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說說笑笑,吃一頓熱氣騰騰的飯。我會更珍惜和朋友相處的時光,難過的時候,和朋友聊聊天,心裏的委屈就會少很多;開心的時候,和朋友分享,快樂就會變成雙倍。我會更珍惜每一個平凡的日子。早上醒來時,看看窗外的陽光;傍晚回家時,聞聞路邊的花香;晚上睡覺前,想想今天發生的開心事。
三月的風又吹過窗臺,綠蘿的新芽已經完全舒展,變成了一片翠綠的葉子。鄰居家的寶寶也學會了笑,每次我路過的時候,他都會伸出小手,像是在和我打招呼。院子裏的老梨樹,枝椏上已經冒出了小小的花苞,再過不久,就會開滿白色的花。我站在窗邊,看著這些鮮活的生命,忽然覺得,生與死這道命題,從來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就藏在每一個認真活著的瞬間裏,藏在每一份真誠的愛裏,藏在每一次對當下的珍惜裏。
我們無法阻止「死」的到來,卻可以選擇如何「生」。選擇認真地對待每一個日子,選擇真誠地對待每一個人,選擇為這個世界留下一些美好的東西。這樣,當我們面對「死」的時候,便可以坦然地說:「我曾認真地活過,我沒有遺憾。」而那些我們愛過的人,那些愛過我們的人,也會因為我們的存在,因為我們留下的愛與溫暖,在這個世界上,以另一種方式,永遠地「活著」。
這便是生與死的真諦——不是恐懼,不是悲傷,而是在時光的流轉中,認真地活,坦然地逝,讓生命的光輝,在每一個瞬間裏,靜靜綻放。
(本文圖片由AI生成)
林釗勤簡介:筆名曉林,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曾多次獲獎。作品散見《詩歌月刊》、《中華詩詞》、《新民晚報》、《作家文摘》、《海外文摘》、《詩選刊》等刊物。另外,人民網、新華網、光明網、學習強國等媒體平臺亦有拙作見諸於世。出版有散文集《有情天地》,詩集《落地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