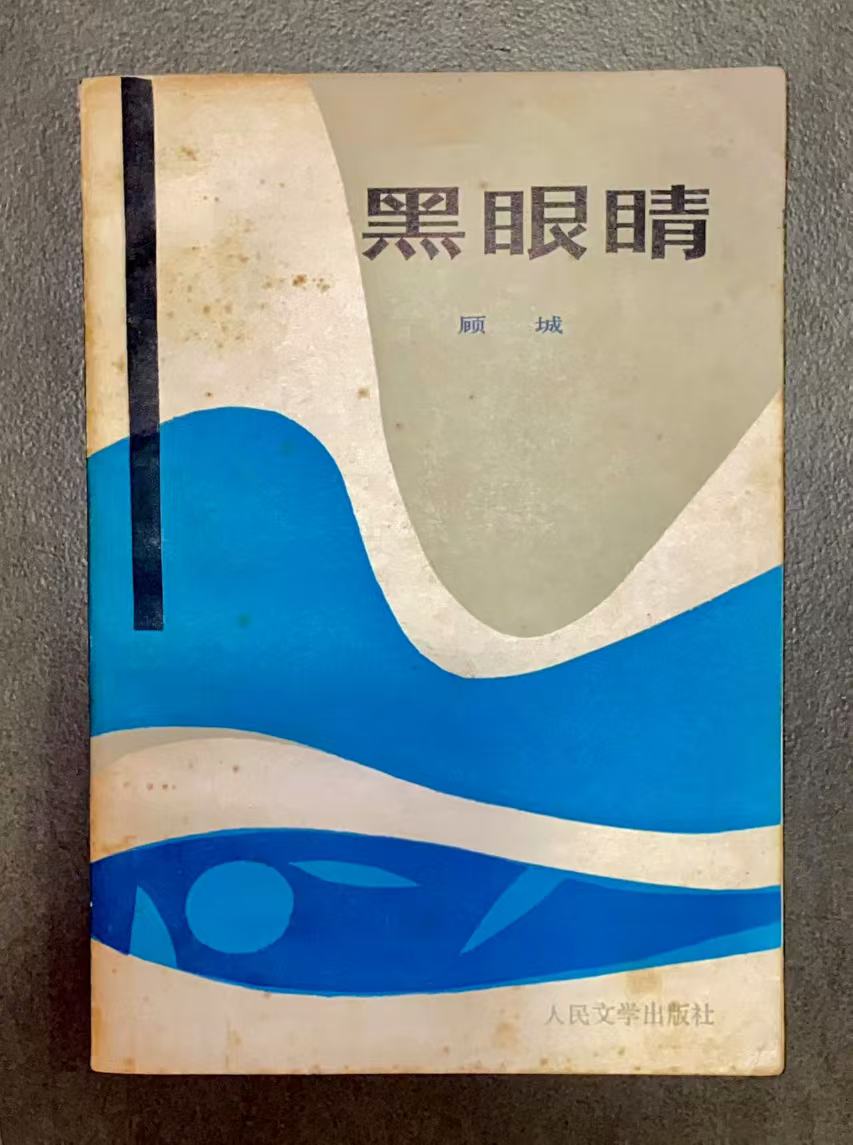汪立穎

與秀蓮的認識,得上溯至一九九三年,她初遊巴黎找住處,由她的舊同事、我的好友渝芳牽線,就來到我的小寓所了。秀蓮在其散文中屢次提及「庭院深深」的古宅,位於塞納河畔,她為樹影婆娑,墨綠書箱鱗次櫛比,而「醺然若醉,興奮得難以形容」,「電光火石」即刻激起了一股寫作衝動……
寫作動力日勝一日,文思化作文字,文集一冊冊問世了,我這小宅或亦與有榮焉。
今次蒙秀蓮邀我這籍籍無名的人寫序,明知力有不逮,仍勉捉禿筆為之,以不負其望耳。
在欣賞作者的散文之前,可先琢磨其題目,讀者不難發覺七字句的特別多,如第一輯收集了十二篇,其中十篇的題目均由七個字組成。其他各輯各有差異,粗略統計,全書五十四篇,七言句佔了二十六篇,將近一半。
區區七言,情與景,凝結於一地名,地名隱顯了作者之情感及當下之景色;若返溯之,則情景潤色了地名,使之躍然而出。如「幾回踏過雀仔橋」、「燈昏影雜南昌街」、「鄉愁暫厝旗山上」等是為其中的佼佼者。又有脈脈詩情,韻味漫溢的,如「唐樓碉樓月色同」、「京都舊夢鬢雲間」。每一題的平仄協調,形動詞巧妙得當,讀來抑揚頓挫,猶如出乎一首七律。
尚未見全豹,已予讀者一遐想。
描述其「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大概無人能出其右。一座石橋,一條尋常大街,一處隱蔽古蹟;還有社會小人物:鞋匠、小販、車衣女工……都在她細膩的筆下呈現異彩。
擺攤看相,席地弈棋的南昌街夜市,作者如是說:
把城中一角已深沉的夜色照得半昏半昧,掩映微明。放眼望去,只見街燈之下,另有光芒,一焰一焰朦朦朧朧的漾開,而人影錯雜,三五而聚,把燈花圍住。
先描繪與他處不同的燈火半明,神秘兮兮的背景,而後直述造成夜市的兩行業:
隨地而擺,佔地甚小,相士與客對坐小板凳上,客先坐定,正襟端坐,不可亂動。原來農村夜裏捕捉田雞,只要用燈光直射,田雞頓時不能動彈,恰像提燈看相未敢妄動之片刻,故此把看相戲謔為「照田雞」。
弈棋文雅,講求理性,有君子之爭,無街頭之霸。善弈者在地上擺下白底印上紅線的棋盤紙,紙張已舊,摺痕斑駁,偏又紙質單薄,怕給風吹翻,便用小石子鎮住四角。火水燈或者大光燈,照亮棋局,弈者常常讓客三子,顯示自己有力追回;……
相面看掌和公開鬥棋原是到處可見、中外皆有的。妙的是一只小板凳、一張棋盤紙鋪地就可開檔,且有「攤子首尾相啣之盛況」。謀生道具,因陋就簡以至於此,確是舊日香港風情,也唯有香港人具此能耐。
我離開香港已達半世紀,走過不少國家的小城鎮,兜兜各處的露天菜市場已成習慣,亦是感受當地風土人情的捷徑,所以各種各樣的小販見過很多。但使我重現腦海,難以忘懷的,乃如秀蓮所述:
賣蔬菜水果的已摸黑到菜欄果欄,……最教人動容是全家上陣,媽媽胸前掛藍布錢袋,一面買賣,一面反手哄拍孭帶裏的嬰兒。二三小童挨近媽媽,低頭在水果木箱上做功課。
六七十年代,這樣的街頭實景,在香港司空見慣,有幾人為之「動容」呢?回想當時年青的我,也屬於無動於衷的一個。而後入世漸深,方明這實在是一幅香港小販的拼搏畫:面對困苦艱辛,沒有眼淚,含著希望——小孩在水果木箱上專心做功課。怎能不令人感動?
香港的繁榮滲透著他們的血汗,秀蓮抱著同情、尊敬、讚揚,把這些底層人物,如無名英雄那樣寫進了香港歷史。

〈病染傷寒生死間〉,這篇散文結構,富有小說的懸疑、轉折、跌宕,題目中「生死」兩字,就把人心懸起了。開篇只言大學剛畢業,「最後一個悠長假期……滿懷憧憬」。接繼而來的卻是「救護車突而駛進大學保健處,啊,擔架床把我抬上車」。讀者不能不出乎意料!寫作人隱去已病一段,直接描述上救護車,「嘭一聲關上門,我躺臥車廂」,快速剪接,一如影片。入院三四天後,確診為傷寒,「又叫腸熱,會傳染的」,文章轉入緩慢,病人陷入淒苦:要遭隔離,家人也不能探望,因而「抽抽答答哭起來」。獨立的小樓,孤零零,護士兇巴巴。作者將心情融化在景物中,外在物的描寫表達內心感受。引出「這地方住不下去的」結語。
淒涼狀況極短,奇峰突起:「翌晨一個護士笑盈盈走進來」,原來是中學同窗,病房重逢。從天而降的白衣天使,馬上使陰霾化為陽光:她母親的「那口開平鄉音高興得發抖」,孤獨的隔離病房「一下子變成豪華私家病房」,病人似乎這時才注意到病房有「伸出半空的舊式陽台,可與家人揮手作別,可仰觀日月星辰哩」。
這一峰迴路轉,猶如小說手法,讀者亦為之欣喜。不用說「接著的留院日子就在恩典中度過」:母親送來湯水、報紙;大哥買來名牌錄音機;護士和藹可親,雜務員盡心盡力,還有「薑花香氣滿室瀰漫」。隔離留醫,何可更勝於此?
「小說」的情節發展,至此達到高潮。
生病住院本不稀罕,但各人的幸與不幸,生與死的一線之隔極不相同。讀過奧威爾〈窮人如何死〉一文的人,忘不了他所寫的那家巴黎貧民醫院:長長的一通間,低,昏暗;靠得很近的三行病床,擠著六十個病人,飄著令人作嘔的氣味……病患是否傳染,沒人理會;護士挨著一個個病人做同一式的拔罐,從不消毒。每天早上總會發現某個病床上的人躺著不動了。最諷刺的是有個囚徒病人竟然逃回了監獄,而不願留下!
不過那是遠在一九二九年,作者入院的親身經驗。遲他三十多年後的六十年代初,我自己也有一經歷,與秀蓮的相比較,有天壤之別;若對照奧威爾的,我則幸運莫名了。記得我小學還沒畢業,傳染上了當時肆虐江南一帶的白喉。(另有腦膜炎、小兒麻痺症也是那時的流行病。)先發燒,喉嚨越來越痛,三四天後母親發現我的喉部出現灰白膜及白點,覺得情況嚴重,必須馬上去醫院。由我哥哥陪同,走到了較近的第二人民醫院。那二十多分鐘的路程,使我累上加累,疲乏不堪。時近傍晚,候診室還是坐得滿滿的。輪到我了,護士測體溫,已高達四十一度。醫生問病情,檢視咽喉,按壓一下脖子耳根,不需更多折騰,即刻診斷為白喉,屬於急性傳染病,得即刻轉去傳染病醫院隔離。醫院在城外,怎麼去呢?「叫三輪車去啊!」護士說。理所當然的口氣!那個年代,除了用兩條腿,可代步的唯有三輪車了。計程車還沒存在,至於救護車,全市該有幾輛,但輪不到我。坐在三輪車上,只感到陣陣寒風,我全身冷顫,瑟縮一角,用手帕掩住口鼻,生怕坐在旁邊的哥哥給傳染了。那段路,伴隨著吱呀吱呀的車輪摩擦,似乎沒完沒了。漫漫長路,我至今記得。
在傳染病醫院,我有幸給送入二樓的女子病房,那裏已有兩個病人,我的病床在她倆之間,顯然是臨時加搭起來的,只留下一人可過的通道。病床前沒有可遮掩的長簾,房門敞開,盥洗室、廁所都在房外。走廊的一邊也排滿臨時病床。物質匱乏,並不減低我們對醫生、對醫院的絕對信任。我自己一點不憂慮,既然進了醫院隔離治療,我的白喉桿菌一定會給殲滅掉。對白喉可能引起的窒息,以及心肌損傷後遺症,惘然不知。我擔憂的是住院費用,那筆錢將怎麼付?當時母親因健康關係,被動員「自動退職」,沒了薪水。小小年紀已感受到貧病交迫。所以,我特別乖,聽從醫護人員,打針不叫痛,吃藥不說苦;醫院一日三餐都只供應一碗稠稠的粥,專為病人的半流質食物,我哪會嫌單調,吃得光光的。有一次一個護士在房外大聲吼:「你不怕難為情啊,哭個不停!人家女孩子都沒哭,還比你小,你可是堂堂中學生呀,羞不羞?」那個可憐的男生就睡在走廊的病床上,可以望見我們的病房。護士以我為榜樣了,不免有點得意。
我被隔離了多久,已不記得,至今沒忘的是哥哥兩次騎著自行車送來當時很難買到的梨子。他只能在大門口的傳達室放下東西,然後到醫院籬笆外等我在窗口出現。我們隔著一個操場,高興地揮手,我舉起護士傳遞來的裝著梨子的紙袋,讓他知道東西已到我手中。可惜離得太遠,沒法說話。這該是我最興奮的時刻,兩個同房病人羨慕不已。
在悠長遼闊的時空中兜了一匝,三類迥異的醫院景象,頗真切地反射著其時其地的社會面貌,對照一下,不無意義。話歸原題,秀蓮在其文章的末段,集中描寫她大病不死的感激之情,面面俱到,包括港府對傳染病的醫療政策,竟然「住院一月,分毫醫療費也不用支付」,確實值得讚揚。最後,於養育之恩的父母,滿腔感念傾瀉而出:
當年天天登山探病的母親如今已年逾九十,竟爾連子女都認不出了。父親哩,半生貧寒,在製衣廠的熨衣部揮汗如雨,盡力撐持一家,所以對於金錢,向來非常節儉。可是驚見女兒一病沉疴,命若游絲,竟然毅然決定傾盡畢生積蓄來救治。我從未想過父親會作這樣打算,都怪自己不體念親心,……生死渡頭,矮矮胖胖的父親為了搶救女兒,竟是一副勇不可擋的姿勢。二十年前,我再次立在生死渡頭,軟弱乏力,淚下如雨,忍看捏住紅簿仔,獻上一生血汗的身影,遽逝於煙水茫茫。
父母劬劬,讀之如見其貌;再添一筆與其父親之死別,讀者亦將淚下如雨。
此文題目中的「生死」二字也於此再顯,作出另種回應,首尾圓合。

秀蓮來巴黎,經常小住一月或二旬,從不作走馬觀花的遊客。她筆下的花都,點綴著巴黎人的普通生活。如〈趁墟在巴黎〉描寫露天菜市場;〈白露筍與Crêpe的滋味〉,前者為春季時鮮,「其色如玉,素白通透」,熟後則「清而爽,甜而脆」,故而人人寵愛;後者crêpe是去餐廳的較廉消費。用黑麥麵粉做的薄餅,在作者筆下變為「餅是圓的,這食店把鹹餅四邊撐起,再合攏,如花瓣圍抱花蕊,餅底便由圓變方,簡直一尊黑色立體雕塑,非常現代感地奉客」。
這大概便是一個寫作人與普通人的不同,他們的敏感和想像力變平凡為神奇!〈趁墟在巴黎〉一文中同樣表現了作者的敏銳觀察,市場一般的果蔬、芝士和牛羊雞肉類等等之外,「還有花卉盆栽、地毯、古董,更有維修古董家具的攤子,嗯,沒有這些,也不似巴黎了」。售賣地毯、古董和維修家具同在菜市場中,他處確實不多見,作者的眼睛馬上逮住了這獨特。「出於懷舊情意結吧,加上露天購物有一種自在的情趣,墟市頗受歡迎。」一語中的!周末的墟市,人丁興旺,有推著嬰兒車的年輕媽媽,有帶著孩子的上班族爸爸,購食材與散步,一舉兩得。攤主和熟客一邊稱貨一邊拉家常,若臨近某個選舉,總有人公開譏諷他所不喜的政黨、政客。而派政黨傳單的,就在一側。我自己也習慣趁墟,熟知哪個攤檔販賣直接從農場來的有機蔬菜、沒有打針的雞鴨,多付幾歐元也值得。何況讓小農小販賺,勝於把錢花給超市的大老闆。若只存在冷氣襲人、千家一式的超級市場,巴黎豈不失色?
「趁墟吧。」秀蓮說。
許多法國作家也擅長描述秀蓮所針對的主題,即其所生之地,平平無奇的大街小巷,日常的集市,及其底層小民。Henri Calet(1904-1956)寫的Le tout sur tout 或可譯為「全之全」[1];另一本JacquesYonnet之Rue des Maléfices,中文即「巫魔的街道」[2],都可與秀蓮的文章對照來讀。中法作家相同的是對巴黎的情有獨鍾,而大相逕徑的在於一方歌頌巴黎,讚美人間天地;另一方刻畫窮困悲慘的花都,人性之惡。安徒生的《冰雪皇后》中,魔鬼打造了一面魔鏡,當它粉碎下落,紛紛碎片碰觸到的人,就變得像男孩加伊一樣,冷酷無情,再無仁善。秀蓮該屬於少數幸運者,沒受到魔鏡碎屑侵襲。所以,美與善,永遠驅逐了醜與惡。
作者追悼故人的文字,總使我覺得好像就此認識了被悼念的人。如前一文集中,憑電學知識有求必應地助人的堂姐夫,誨人不倦的譚福基先生,知名與否,都讓人恨不能相識。至於對其恩師余光中的緬懷,字字發自內心,華實過於藻麗,感人肺腑。本文集中有兩文追憶余師母,文筆一以貫之,記其生前:
師母可不只是「跟得夫人」,……更因雙手靈巧,懂得設計及編織中國結,在台灣享負名氣,成為專家了。《玉石尚》是她的著作,圖文並茂,把古玉與中國結美麗地結合。
數言點出其個人的藝術成就,再及其慷慨性格。作者述完鑽婚故事,讚美道:
珍珠項鏈的綿綿情意,溫潤完美地留在文學史裏。鑽石戒指的璀璨,不曾閃耀在她的指間,卻長留在原居民的心田。

作者赴高雄旗山,向師母告別,寫下安厝骨灰罈的一刻:
木魚輕敲,梵音響起,檀香浮動,觸動了西方極樂的聯想。余教授骨灰位的門本應緊閉,此刻卻打開了,啊,多麼體貼,多麼周到!讓我們親眼看見兩個骨灰罈並排,陰陽分割六載,今夕重聚,終於圓緣。……這靜室,暫厝了文學史裏觸動萬方的鄉愁,暫厝了甲子而永恆的恩情。
秀蓮不愧為余光中的高足,由寫實景,進入想像老師師母先後逝世,今又重聚之終極圓緣,亡者同安息再無遺憾。悼文至此已極圓滿,可點上句號了,但作者遐思不止,更向亡者情愛永存之境飛去:
這靜室,從此於無聲處,會有悄悄情話,別人無法聽見,他倆卻說個綿綿無盡。
拳拳且眷眷,師生之情千古矣!
本文集中許多值得細細研味的篇章,筆者於此不再贅言。秀蓮的散文已創出一己的風格,簡言之,詞彙豐富絢麗,善用排比句法,如「校舍有情,菁莪樂育,讓孩子俯仰其中,琢磨品格,切磋學問,磨礪意志」屬於一種相向相聯的對偶,重筆突出意義。再舉同一文中的正反排比:「分明知道這建築存在偏又未窺全貌,似曾相識偏又印象朦朧,似在近鄰偏又陌生,似乎高不可攀偏又俯視鳥瞰,如今雖然一知半解,總算一睹廬山。」運用一正一反的相背句法,展現作者所「撼動」之因緣。此類修辭法在文集中不勝枚舉,形成作者的風格之一。
文章優美雋永,固然來自於深厚的文學修養,個人認為秀蓮尤其深諳「文質附乎性情」,是「為情而造文」,非「為文而造情」者。猶如《文心雕龍》所言:「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拙文天馬行空,掛一漏萬,不守傳統序文規矩,尚請作者與讀者海涵。
註:
[1]此書描寫一九〇五至一九四八年的巴黎,尤其是作者出生地的第十四區。注重普羅民眾、小商人、手工藝者的生存之道。
[2]此書背景是四十年代德軍佔領之下的巴黎,作者將現實與想像融合起來,組成似真似幻的短篇。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汪立穎簡介:蘇州人,香港新亞研究所畢業,旅居巴黎數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