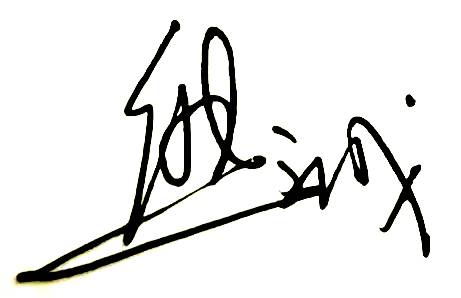 熊 城
熊 城
廣東著名作家
少年的初中時候,是容易想起的一段人生。在繫紅領巾的半大兒童小學期間,我們都還稚嫩,同學中發生的很多事兒,很容易就被小腦瓜自動刪除了。最有印象的少年時候,自然是從小學轉換到初中的生活。尤其是我,只經歷了初中,就下鄉到廣闊天地了。
記得,我踏入肇慶中學的校門,頓時像跨到一個新天地。從這刻開始,懵懂的腦袋開始思考,喜歡閱覽《十萬個為什麼》等課外讀物,對顯微鏡下的活潑草履蟲和牛頓被蘋果砸頭而發現的萬有引力,都充滿新鮮好奇。
不過,要說追尋初中同學的情誼,我又似乎有點淡漠。一來初中僅有三年,共處時間不長,學業又繁重,同學間彼此難有深交。二來那時學校講究男女有別,自然早早被壓住了春心的萌動。
喚起初中的記憶,有些課外生活倒很鮮活。放了學,我私自跑去幾公里外的星湖野泳,自個兒浮在清涼的湖水之中,仰面看藍天白雲,真有點像初生牛犢,不知死活。嘴饞啊,常去家在行署大院的同學那裏做作業,就知道他母親總會切鮮甜的西瓜來招待。西瓜,那個時候,是多稀罕的水果。有同學喚去郊外,說蔗農要砍蔗了,田頭有蔗頭蔗尾,讓吃。跟同學去古城牆下大菜地,把著銅臉盆,在太陽曬得水皮發熱水裏涼快的水塘摸螺螄;用簸箕撈色彩斑斕的小鬥魚,把它們放到玻璃瓶裏游鬥,添加點燈芯水草來欣賞,也是趣事。可惜,這些快樂並不長久,隨著課程節奏的加快,同學們大都開始埋頭書本,心思著如何順利上高中,企盼高考的金榜題名。不知不覺,初中的日子,就變得簡單而又平淡如水。

對同學話題引起胡思亂想的,是由一次初中同學會而引發。那回本來是純同學聯誼的場合,大家多年不見,相互之間大體講些拜年好話就算完滿了。不承想,我卻碰到質疑個人出身的怪事。
之所以認為怪,也勾聯於文革初期的一件事。那天,偶然路過操場,見球賽精彩,我就參加了圍觀。賽畢待散,卻見帥哥中鋒徑直向我走來,熱情地問我姓名,問我是地委還是專署大院的子弟,邀我參加幹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戰鬥隊。
這種關乎一個學生出身的問詢,在文革唯成份論的時刻,是很敏感的。如果家庭背景有國民黨的嫌疑身分,子女就會遇到連累。我父母是普通的醫院行政幹部,算是不紅不黑吧,不明白這位籃球中鋒何以會誤認我是大院高幹子弟。
星移斗轉,日月如梭。以什麼出身去決定人的處境,早就被變遷的光陰磨蝕了。沒料到,一個在廣州的女同學在微信問我:你父親是國民黨嗎?現在有同學在群裏私聊,問你是不是國民黨員哦。
有人研究我是不是國民黨?國民黨又怎麼啦?這位女同學也認為怪異,所以憋不住說出了此事。她說,在同學聚會時,某同學激昂發言,表示國家大事匹夫有責,為了江山統一,不惜一戰!在鼓掌時,有人注意到你有不屑的表情,微微鼓掌也明顯是在裝模作樣。這算什麼事兒哦,讓我哭笑不得,我那時根本沒有在意什麼人在講什麼話。當今還有人詢問出身?歷經改革開放,白髮蒼蒼的老同學還有如此強烈的階級劃分觀念?還有一顆火紅年代那樣的鬥爭精神?怪不得,這幾位大爺大媽總喜歡在群裏相互曬出唱紅歌的雄壯畫面,播出懷念大集體的視頻,歌頌著他們認為的正能量。為免引起誤會和麻煩,我只好請這位女同學向群裏轉告:我父親是無黨派民主人士,母親是一九四一年抗戰入黨的中共黨員,文革後期獲得平反,恢復離休幹部待遇。其餘,無可奉告。隨即,我正式退出同學群。
當年問我是否幹部子弟與幾十年後問我是否國民黨,可見時代留痕有多麼深刻和頑強。這個事情,說來雖有點黑色幽默,但又似乎有點可悲。哎,都翻篇了罷,我以為不值得再去搭理什麼同學的鳥事了。
二○二四年大暑,南方在高熱中又常有大雨驟至。這天暴雨半夜而起,小冰雹零亂地敲打著窗戶,雨水浙瀝著,點滴到天明。打開窗子,流經順德的碧桂江吹來涼爽的晨風,分外愜意。伴隨刀郎的《羅剎海市》新奇古怪的詞曲,我刷起微信,竟見一條信息跳出:「記得初中的他嗎?昨天走了。」
這個「他」是初中同學,那次同學會沒見到。在寫小城肇慶變遷的一篇散文中,我曾寫到他的母親。他是正宗的地區專署大院子弟,白白淨淨,文質彬彬。他母親是東北抗聯女英雄趙一曼的警衛員,隨大軍南下,在肇慶這個小城市裏因傷休養。她自然是資深的老幹部了。她有東北人的直爽,說話無所顧忌。文革時這位老幹部出乎意料地出頭反對市革委會抓人,被進城聲稱保衛革委會的農民用禾杈刺傷,幾乎殞命。也就是在文革初始,我這位同學成了紅五類某戰鬥隊的小司令。我們身份已然不同,雙方無話可說,便不再聯繫了。他沒下鄉,當了兵。他的人生走向如何?歷經什麼風雲和榮辱?我不了解,也不想探究。
他走了,如風而去。隨著心裏的一聲嘆息,我看到陽光透過茂盛枝葉灑下的光束,看到一地斑斑駁駁的時光亮點。他雖是幹部大院子弟,但在文革之前,在我們如鶯飛草長般熱鬧的同學裏,他卻只是一般的學生,連學習小組長都輪不到他。
他走了,仍有人關注並傳訊各個同學。我想起一句禪語:十年修得同船渡。
同學少年,在一起讀書、相處,也是緣份。
想到大家命途有異,修為不一,見解和觀念自然有不同。同學間的一言不合甚至誤會,我何必介懷,又何必有執念。
同學會發生的那個不愉快,正好勾起了少年的回想。
不過,初中同學雖相互為伴,少年時卻沒有在意很多的事情,不了解各自的經歷。有些傳聞不知真假,也不好記載。好在只把自己腦中閃爍的片斷映像回放,卻是不難。就像挖出了秦代竹簡,不懂專業的一般人並不珍惜,而專家對竹簡記下民間保甲夫役日常的流水帳,卻視為考古寶貝。想像著,未來有人看到某個年代,處於西江中游的肇慶中學,有文字記下了該校一些少年學生真實的生態片斷,說不定也會有點意義。
又或許,這些文字沒什麼意思,在別人眼裏只是作者少年情結的化不開,尋求自我渲泄而已。我想,不必囿於有什麼看法,碼這文字,意欲一了少年同船渡的緣分罷了。

我們班叫初中丁班,在甲、乙、丙、丁排序中算未尾。那時的班級排序,並沒有重點與普通班區別的意思。在我眼中,丁班和其他班一樣,出入教室的都是品學兼優的少年,生似春色滿園中在牆頭探出的花骨朵兒。
我們考進的肇慶中學,是地處廣東粵西的省屬重點中學,有著舊「肇慶中學府」的百多年歷史傳承。在開學典禮上,司徒校長在台上正襟危坐,他講話的一舉一動,在我們眼中都是神一般的威嚴。老師們也都是我們心目中的權威,在課堂上咳嗽一聲,我們都不敢有嘻笑的反應。一位教數學的關老師上課笑嘻嘻的,講數學到興奮時得意忘形,他嫌來回拿刷子擦得慢,竟然常常用衣袖來擦黑板上的公式,讓人忍俊不禁。最有儀式感的是班主任鄭老師,他來上課,頭髮總是梳得整整齊齊,每擦一次黑板,也不忘記掏出小梳子再梳一遍髮型。每次上課開講前,他都鄭重其事地慢動作把帶銀鏈子的一塊懷錶取出,先向同學們掃視一周,然後把懷錶在案桌上擺好,仔細地觀看其長短針定位。他一板一眼的講課,嘎然而止時,總是踩準鈴聲。
肇慶中學高中班級多安排在幾幢三四層的高樓上,初中各班級則在中軸線校道的東邊花園區,初中課室是合圍式佈局的平房。花園的北面有深綠色琉璃瓦頂的科學樓,東南處有孤形穹頂的大體育館。花園裏,亭台水榭,小橋流水,綠樹紅花中曲徑通幽。
肇慶中學,由於高考升學率較高,又擁有眾多體育、文藝尖子人才,一直享譽全省教育界。我雖是普通的初中生,每當胸襟上戴上校徽,臉上就感到光彩和驕傲。
我也為初中丁班自豪。就說在學生中引人注目的校歌舞文工團吧,三十多個成員中,我們班的同學就有好幾位。我們班長是文工團的話劇男主角。富有表演天份的同學其實還不少,有個李同學,平時安安靜靜,不顯山不露水,也不是校文工團演員,但在七十年代,他竟成為肇慶市宣傳隊的台柱,是出演樣板戲的英雄主角。
我的同桌,是校文工團樂隊的樂手。說起同學,就用化名罷,這裏稱他為小燾。
小燾個子粗短,剪個平頭,氣場很凌厲。一分配到我座位旁,他就用小刀刻出桌子中間的界線,聲明雙方各不逾越。我只知男女同學會劃界,沒想小燾同學也會來這一套。
他各科成績分數壓我一頭,坐在旁邊,讓我總是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他常在課室外的小花園練習笛子獨奏,指頭雖然粗短,卻十分靈活,指尖在笛孔上跳躍起伏,旋律在花叢綠樹裏飄蕩回旋。小小竹笛,被他吹出活潑又優美的樂韻。他拿出《廣東音樂》雜誌,指著曲譜說哪首樂曲創作或編曲的作者,就是他的哥哥。廣東省作家協會專職副主席楊幹華曾告訴我,六十年代,他在《羊城晚報》發了一首短詩,收到三元稿費,轟動了全縣,他成了農民作者。回想起,和楊幹華同時代的小燾他哥哥,這時已經在省的《廣東音樂》刊物發表好幾首廣東音樂樂曲了。我崇拜小燾的哥哥,我認為這哥倆都有天賦異稟,今後前途無量。
這次同學會沒見到小燾。打聽了一下,得知他下鄉回城後在一家外貿公司一直當倉管員,退休了。至於他那個有廣東音樂創作才華的哥哥如何?沒人知曉。
班裏令我佩服的還有各學科的科代表,都是學霸。數學科代表林同學,考試每每獲得年級的前三甲,被學校資深數學老師看高一眼。還有憨厚愛笑的陳同學,初三時竟已自學完高三課程。
說起年少的同學,自然離不開班裏的女生。
她們像快樂的小鳥吱吱喳喳,巧笑倩兮,面若桃花。只是,我不敢正眼看她們的眼睛,講句話更會臉紅。記得初中開學的晚會上,報幕員說,下一個節目由初一丁班同學表演新疆舞。兩位女孩子上台了,是我們班的,我自然十分專注她們的表演。我至今不能忘記那飛旋的許多長辮子,柔美的妙曼舞姿和飄飄的裙擺。我這個小學畢業生,首次感受到愛美而產生的一種抨然愉悅,在偷偷瞄看漂亮的女同學時,感到自己在長大著。
那位告知我同學會事端的女同學,當年就坐我後面,苗條清秀而標緻,我甚至感到她弱不禁風。讓我佩服的,她是校文工團樂隊的樂手,拉二胡。有一位女同學下鄉時跟我同一個大隊,住在隔壁,平時低調隨和,早出晚歸,忙個不停。她和我回城後都在肇慶市技工學校唸書,她留校當了老師。有次,我從一個畫展中看到她的名字,有點吃驚。我雖不懂畫,但從她畫筆下繪出絢麗多彩的大自然景物和人像,讓我刮目相看。我曾把她創作的粉彩和油畫作品圖片讓中國美術家協會馮遠征、溫尚光等著名畫家品評,他們都很欣賞,給予了上佳的評價。
班裏女生如春花爭艷,自然惹不少男生注目。有位男同學甚為調皮,喜歡撩逗,被女同學罵他咸濕好色。老師在班裏多次點名批評他。多年後,沒想到他有信寄到廣州,邀我到江門市一聚。他在信中不無自豪地說,記得老師當年一直把他當壞學生批評嗎,嘿嘿,這個壞學生現在是某單位的黨委書記了。
我看過網上有很多同學會的段子,有顯富貴的,有舊情復燃的,有因支付餐費而嘔氣的,煞為熱鬧。我參加的這回同學會,安排在肇慶市風景區的星湖牌坊廣場,沒有網上吐槽的同學會戲劇性情節,甚至沒有我以為應有的歡聲笑語。有點不太明白的是,積極組織同學會活動的幾個女同學,初中時她們似乎並不顯得活躍。
出於觀察人的寫作習慣,我對尋找大家花樣年華時的痕跡有些興趣。我看到大家都失去了年輕的容顏,有的幾乎認不出來了。這次同學聚會,氣氛不怎麼熱烈和活躍,不少人似乎是為了禮貌而來。看到這氛圍,我不好多問別人的往事經歷了,只默默打量,尤為關注當年令我佩服傾慕的幾位出眾同學。我驚訝地發覺,好些人說不會用智能手機,手上的老年機沒有微信可加。問起工作單位,囁囁嚅嚅,呑吞吐吐。後得知,不少同學大都拿企業職工的退休金,似乎不好意思。此情此景,遙想起當年,他們是那樣春風得意,那樣神采飛揚。升高中,考大學,前面的大道金光燦爛。
星湖的堤岸鳳凰樹繁花如火,我坐在樹下的石櫈上,遙望廣場遠處有一個高大的舞台。舞台上空蕩蕩,看台下也空蕩蕩。我不由得浮想聯翩。從少年走過來,舞台上演的不是花好月圓,而是真真切的暴風驟雨。倘若沒有天雷滾滾的渡劫,以我們班的同學少年時就展現出的才華,他們之中必會有眾多光芒四射的社會精英,必然能騰飛出多少人中之龍鳳。
看著周圍三三兩兩散落的老同學,有的談著什麼,有的自玩手機,有的茫然呆坐。沒有興致勃勃,不見驚喜寒喧。我向一女同學搭訕,說以前老見她憂鬱不開心,如今退休了可好?我知道她有私宅,家庭是資本家,估計終於擺脫成份的陰影了。誰知她很詫異,說從小就根本沒有什麼憂慮,她一直很快樂。我無言了。
初中同學見面,誰又知道誰的心裏對人生有什麼感受?只有一個事實難以否定吧:什麼才華出眾,什麼天賦異稟,當天崩地裂之時,無論參天巨木,無論嬌花野草,統統都會雨打風吹去,殘紅滿地,面目全非。
那些年月,那些際遇,那些走向,那些現狀,如星湖的水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
少年青春踏歌行,山水一程,人各有命。
從肇慶中學六十六屆初中丁班的同學寫來,思維中似尚有鯁在喉,不吐不快。
說到少年的同渡,其實並不限於初中的丁班同學。下鄉到高要縣蜆崗公社當知青,同一個大隊裏也有初中同級的甲、乙、丙班學生,也有高年級學生,甚至有廣州的高初中學生。然後陸續結識其他大隊的知青,我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這條船,我看到知青中傳閱著描寫青春際遇故事的手抄本;我聽到泥磚壘的知青屋裏,破舊留聲機傳出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世上原來有四隻精靈般美麗的小天鵝;從知青苦練小提琴,我知道了《梁祝》的少年戀情在神曲中是如此的悱惻,如此令人迷戀又震撼。夜裏九點統一停電後,我看到知青屋裏的煤油燈下,有人在埋頭翻書。悶熱中,大家搖著大葵扇數報紙上排成一列列的蚊子,比拼誰打死的最多。夏天,我起床,見到床上的草席印上大片汗漬,哦,太累了,以致睡得太沉,不知夢裏也大汗淋漓。冬天,僅有的一雙膠鞋捨不得穿,我瘦削的肩膀勒著繩索拉縴著船艇運物資,在河灘被霜冷龜裂起的土塊尖緣上踩踏,腳板被割刺出道道傷口,寒風吹得裸露的手腳皮膚像樹皮般皺裂。送公糧時,我咬牙挑起滿籮筐一百四十多斤重的糧擔搖搖晃晃地走上木橋。把稻穀傾倒到倉庫的一刻,才長舒一口氣,慶幸自己居然能撐得住擔子的沉重。在遙遠的田壟,我看到女知青累得癱坐田埂上抱頭嚎淘大哭,抽泣著喊媽媽。我心裏湧上一陣陣酸楚和淒戚。有次見老漢抄起棒棍打兒子,大罵兒子敗家,討媳婦是要能幹活能生孩子的,不是討個花瓶來供著。他兒子是生產隊李副隊長,我問,那女知青是我們的校花喲,怎會嫁你?李隊長紅著臉道,她說受不了這個苦,回城也沒希望了。
隊裏的一個老頭在旁邊抽著竹筒煙,嘟囔著說,造孽呀造孽。
這條船,同時也載有鄉下的少年。雖然與知青比,他們受教育程度不是一個層次,但他們生存的頑強和能力,有許多方面顯得比我們都強。在生產隊裏,教我們用竹篙撐艇,學犁耙插秧;幹重活時伸出援手的,往往是隊裏的少年人。夏夜裏,有知青拉手風琴、吹笛子,引來村裏許多小年青。我認識了一個叫智才的小夥,他能吹鎖呐,拉出一手好二胡。熟悉了,有一天他神秘地偷偷掏出一張線路圖,問願不願意一起泅水偷渡去那邊找一條生路,這勇氣和膽略著實讓我驚愕。他果斷走了,冒著叛逃的危險穿過鐵網,投入怒海。少年人呵,不論身處何方,生存的本能讓他像種子落在巨石縫裏,但凡有一點機會,死活也要伸出它的綠色枝葉。
是的,無論是不是一個班的同學,一個校的學生,一個地方的少年,我們都在同渡。有時候,我們只能抱頭蜷縮在船艙裏,不知彼岸,茫然地任航船在江海顛簸。
想起江海之遠渡,有個一八八一年出生在西江,一九三三年在香港逝世的世界著名哲學思想家陳煥章,很值得提一提。
我曾來到西江的硯洲島。從車窗往島堤下看去,岸邊農田綠意盎然。豆秧間有木樁渡口,悄無人影,一隻小船橫繫水邊。這兒是陳煥章故居舊址。
不知外界有多少人知道陳煥章?
應一個企業邀請,我與金融投資人到這個西江小島上作投資開發的考察。主人帶我們去看島上的資源和歷史人文環境。來到陳家祠堂,我才知道這個僅有幾百家農戶的江島上,竟出了個近代國內外聞名的大師陳煥章。
我驚訝,同是西江人,我還算是這地方出來的文化人之一;而且,認識的當地各界名流也不算少;卻在上島之前,竟然從沒聽到有人說西江有個陳煥章!實在慚愧。
陳煥章的故居只剩殘址,只有旁邊翻修過的陳氏祠堂裏展示著陳氏後人對陳煥章的介紹和掛上的一排照片,有幅康有為手書的「勵剛書院」舊牌匾冷落地倚在牆角。祠堂前的地坪,豎立著進士的石碑旗杆基座和一些石雕刻。江風把附近蕉林吹得嘩嘩作響。
陳煥章從西江上的硯洲小島參加鄉試,連接考上秀才、舉人,進京考上進士。殿試時,他的才華被隆裕太后一眼看中,即下旨聘陳煥章為三歲皇上溥儀的老師。辛亥大變後,陳煥章遠渡太平洋到美國。以中國皇朝科考的進士而又擁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他是中國歷史上的唯一。他是首個在國際上全英文撰寫出版中國國學等鴻篇巨著的學者,長篇代表作《孔門理財學》至今是經典。與密友康有為的政見不同,他擁護北洋政府的民主憲制,他站上了社會變革的潮頭,他受聘為兩屆北洋政府總統顧問。只要在網上搜索,有關陳煥章的學術研究和評論,無法計算,陳煥章在國內外的聲譽,可謂如雷灌耳。現代國際兩大哲學思想流派領袖,一個叫凱恩斯,主張用政府行政計劃之手干預社會經濟;一個叫哈耶克,主張以市場經濟的民主、自由限制約束政府施政。令人頗為震動的是,這兩位哲學觀點對立的巨人,卻一致讚賞陳煥章萃取中國文化資源的政治經濟學術思想。遺憾的是,陳煥章在祖國土地上發芽,盛名卻遠播西方。
看著掛在牆上陳舊的鏡框照片,少年陳煥章頭戴小瓜皮帽,有點模糊的肖像仍透出俊朗英氣。這位盤著髮辮的西江少年,帶著藤編的舊書箱,隨烏蓬小艇在江濤中乘風東去。他越過長江黃河,風塵僕僕到了褚紅色的高高紫禁城牆內。我有點好奇,他面對高貴而頑劣的小一尊,如何調教?能往小皇上手心打戒板嗎?在清末風雨飄搖的皇朝巨艦上,這對師生,如何船渡?裏面有著多少秘聞故事?沒見文史記載,看來只有塵封在歷史之中了。

我從陳煥章故居到了島東面的包公祠,這是廣東現存有香火拜祭的包拯廟堂。路邊擺滿售賣土特產的小攤,老農們熱情地向遊客介紹島產的粉葛、劍花、魚乾、藥材。同是硯洲島上人,看模樣,他們與陳煥章應差了一個輩份。
我彷彿戴上了人工智能眼鏡,眼前呈現出一幀幀全息圖像。少年陳煥章與同在島上生活的一代代農家少年,在不斷比對變化,光影不斷閃爍,迷幻地快速掠過。在時代的大船上,同一塊土地生養,人生卻有朝堂和鄉野的迥異,這就是天差地別。
我和同行的朋友邊走邊聊,我隨意生發出了感嘆。豈料,朋友中有人卻持異議:這些擺攤的老農不一定羨慕陳煥章大人。也許,他們認為自己現在的生活就挺好,多賣出些農作物,就會開心。誰能說他們自己感到不幸福。
我默言。生活裏,確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知和限度,他們的生存和經歷,不可預知。誠如井裏的蛙,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在幽長不見光線的地下河,不是有的生物退化到有眼睛卻沒有視覺嗎,但它們仍然頑強地繁衍,真是神奇的造化。至於有什麼評說,它們不知道,也不會在意的。
少年同渡,這個話題,似乎太豐富,又有著讓人能不斷思考的魅力。
我住的碧桂園社區,有一所遠近名聞的碧桂園學校。曾和幾位經歷過創辦學校的校長們一起喝茶,他們是全國率先搞國際教育的一批專家,我在聊天中尊稱他們是教育家。叫滿園的女校長直率地認為我說得不妥,她說,我們只是教育工作者。滿校是四川人,辭去公立學校職位加盟初創的碧桂園學校,她曾被評為廣東省優秀教師,還親手培養了三個廣州市「羊城小市長」,同時也是國內比較早接觸生涯教育方面的專家之一,並與朱樺院士一起出版了初中《生涯教育》教材,我自然認為她完全有資格稱為教育家。
滿校聽到我的解釋,笑了。她說:「你把青少年的教育看得太簡單了吧?能把教育工作者的初心體現出來並能完成一定的使命,我就滿意了。可是,這很難很難。」看我有疑惑,她說,不要以為我謙虛,這是真話。你想想,學生的青少年時期不但要學習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了解怎麼認識現在和未來,要知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裏?」、「我怎樣去到那裏?」,他們不是工廠流水線可以生產出來的,他們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活體。同一個課堂,同一間學校,可每個少年都是不一樣的,都是獨特的,將來都有著自己的人生道路。學生們的黃金時期如何渡過,不僅將關係著他的未來,而且關係到家庭和社會,關係到國家和民族。
這番話,讓我一震,猶如醍醐灌頂。
滿校起身從書櫃中取出一疊國際教育的有關資料給我看。有一張複印圖片,裏面是一群身穿清代服裝,頭上有髮辮的兒童照。滿校指著舊圖片說,這是清代洋務運動首批官派美國留學的學生照。從新加坡歸來的琳達和她們創辦的國際教育培訓學校,一直把中國第一批少年留學對個人發展和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作為學校辦學的宗旨。
「那時,富家子弟是不願去夷蠻的洋人那兒學習的。只有明白讀書才有出路的人家,願意讓孩子出洋。就這樣,官方也好不容易才湊了百名兒童。這些孩子,心驚膽戰,害怕著陌生的大洋彼岸。他們的曲折不講了,就講結果吧。學成回國的少年,都成為中國各個學科、各個領域的首創人,是國家各現代學科的開山大師和巨匠。有一點很重要,這些同渡大洋受到國際教育的少年,大多數是一般的孩子,可不是學霸呢!」
我看著滿牆貼著的一張張世界名校錄取通知書影印件,而這當了解到這些學生原本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學霸學生時,難以想像,這該得要有多專業的指導、該付出多少艱辛的努力呀!
優秀人材,不一定是天才、學霸。少年的黃金期如何渡過,遇到了什麼,認識了什麼,獲得了什麼,昇華了什麼,對一個人,一個家庭乃至國家民族的未來,有著難以估量的意義。
少年,學習、磨難、幸運,這些話題,實在豐富我的視野。
有一段對話,也有意思。
香港歌手譚詠麟問刀郎,聽說你少年時從四川跑到了海南歌廳,老喜歡唱我的歌,為什麼?刀郎老老實實地答,因為大家喜歡聽你的歌,我唱你的歌,可以多賺點錢。我沒錢。
刀郎,四川人,十六歲先是在內江歌廳,後到海南做流浪歌手。顯然,刀郎連高中都沒讀完就輟了學。刀郎在海南認識了新疆來的女歌手朱梅,二十四歲跟朱梅去了新疆。在新疆接觸豐富的西域民歌和地方風情,幾年後的二○○二年,他創作出《西域情歌》,名聲大作。同年,歌壇上唱響《二○○二年的第一場雪》,刀郎獲全國通俗流行歌大獎。最讓我驚奇的是,二○二三年刀郎的《羅剎海市》,一經演唱,火爆全球。網上傳唱播放量十一天八十億次,打破二○一七年西班牙紅歌手創下的五十五億次的吉尼斯紀錄。在寫本文時,我查了百度,至二○二四年夏季統計,《羅剎海市》全球播放量竟然達到驚人的二千億次。刀郎,少年便自駕一葉小船,在波濤中破浪。他沒有專業學院的學歷,沒有名歌唱家的指導,駕馭孤舟遠渡,終於登上高高的藝術彼岸。
我把手機放一邊擱著。我靜靜地思索,世上有天驕少年,有各種傳奇的船渡。更多的是普通平凡的少年,每人也都有著不為人知的故事。對江河之砂礫,對一花一世界的綻放和謝落,我是無法窮盡了解的。我只感覺到寫著身旁的同渡人,苦難往往類似,快樂卻難以相同。
不得不感嘆啊,人生苦短,同渡瞬間。
記起蘇軾一詩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天上有人間?在星際的光速或超光速的宇航艦船裏,人生幾何?少年幾何?
我忽然有點冒昧的扯淡:
少年同渡,你好嗎?
同渡少年,你以後好嗎?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