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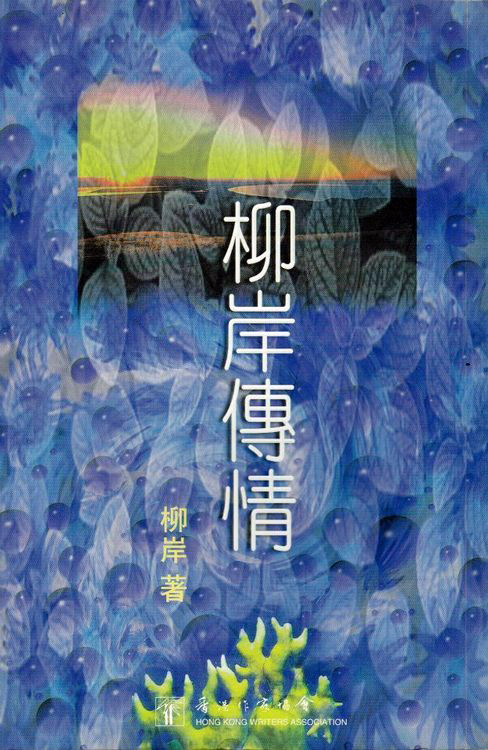
一
阿棠這幾天不用上班,在家中百無聊賴反而有些不習慣。他一個人獨居,感到不做工作時間真難度過。做了六十多次掌上壓,翻身躍起,坐在沙發上,隨手撿起放在身旁已看過的舊報紙看。翻了兩翻,索然無味,便隨手一拋,丟在沙發上,聞到自己一身汗臭,便入浴室沖個早涼。
阿棠剛脫去衣服,正要塗肥皂的時候,電話卻響起來。
「哼!等了許久才打來,偏偏在這個時候。」阿棠口出怨言說。他把浴巾往身上一圍,便步出大廳,走了兩步,他想:「呸!屋裏沒有別人,何必圍著浴巾呢?真多餘!」他雖然心中這樣想,但既然圍上了,也沒有除掉,不過上身結實的肌肉,可見他常常做運動。
「喂!肥福嗎?有冇攪錯?現在才打電話來?」
「他們不容易聯絡上啊,又要他們信我,要自然一點,等兩日算好了!」肥福在電話中說。
「好!少說廢話,甚麼時候見?」阿棠說。
「下午四點,旺角酒店大堂。」肥福說。
「好!一言為定,下午見。」阿棠也不待對方反應,已掛起電話,掩不住內心的喜悅。

二
阿棠挑了件新衣,但不稱身,別人怎樣看,他也是土頭土腦,像個窮光蛋扮紳士一樣,不過他自己卻十分滿意。他故意遲了十五分鐘才到旺角酒店,見到肥福,介紹一個中年漢給他認識,叫陳才。陳才便像個街口茶餐廳的老闆,旁邊還有個三十多歲的女子帶點狐媚。以阿棠的經驗,她是個風塵女子。最低限度以前是,阿棠的內心這樣想。
「這位是何兆棠先生,最近繼承了叔父的裝修公司。但不要小覷他,他公司在大陸接的生意都是過千萬的。」他們坐下後肥福向陳才介紹阿棠。
「久仰!久仰!何先生的生意好大啊!」陳才說。
「那裏!那裏!是叔叔做開的,以前不過普普通通做裝修,這一兩年好運,搭上了高官,在大陸有世界了。」阿棠謙恭一翻,遞上名片。
陳才接了咭片,望望,說:「鴻運公司董事長,失敬!失敬!何先生未繼承這舖子之前是做那一行的?」
阿棠有點吶吶說不出來,肥福在旁說:「才哥是自己人,又不失禮,便說給他聽吧!」
「你不要叫我何先生,叫阿棠好了。」阿棠說「我以前在地盤紮鐵的,也駛泥頭車,有工開使多些錢,無工開使少些。」
「呵──呵──英雄不問出處啊,我估你做工倒勤力,練得身體也結實了。」旁邊的女子說。
「牛力一鋪啦。」阿棠說「實不相瞞,我有三個兄弟,叔父只把生意給我,就是看中我有牛力,不像他們做寫字樓,看不起我們。」
「棠哥快人快語,我陳才交了你這個朋友。陳才說:「廣州有間新酒店,規模不大,裝修費只有七八百萬,我介紹給你,快人快語,回一個佣給我,怎樣?」
阿棠沒有聲,看看肥福,肥福又看看陳才。陳才說:「好哇,大家兄弟,再不用俾佣肥福,在我那一份扣起給他,好吧?」
阿棠點點頭對肥福說:「肥福,我也不難為你,先小人,後君子,他們給你多少我不理,我給四萬元介紹費,你嫌不嫌少?」
「大家朋友,只希望你們做成生意,四萬?好!但可不可以不簽合約,同時立即給我,你知我等錢周轉。」
「好!這樣一言為定,大家也朋友啊」那女人說。
他們四人感到目的已達,高高興興談了一會,陳才結賬,訂下再次會期,便各自散去。
三
在一個密室裏,桌前坐了一個五十多歲肚滿腸肥的胖子。衣飾華麗,頭上只有稀疏的頭髮也打理得貼貼服服。架著一副金絲眼鏡,說話雙眼瞇成一線。陳才坐在他的前面。室內還有三四個人。「你查過羊牯的背景沒有問題麼?」胖子說。
「大哥,怎會不調查清楚呢?我們取了咭片,打電話他的裝修公司,果然有何兆棠這個人。」陳才說。
「我也有到裝修公司探路,他們的老闆果然三個月前病死,由子侄承繼。他們還說繼承人不懂這行生意,只會四處動,揮霍金錢,常不在公司。」和陳才一起的女人說。
「阿娟,你的消息是樣來的?」大哥問。
「借頭借路和他的伙計搭訕,叫他們請飲茶,什麼也套出來了——這樣做不太難吧?」阿娟說。
「我看肥福急於回水兩成,也不敢作怪,他說和阿棠也不大熟,找他做替死鬼也心安理得。」另一個青年說。
「唔,既然大家覺得無問題,就一起做一台戲好了」大哥說,從盒子取出雪茄來,慢條斯理擺弄,對青年說:「大雄,你叫肥福入來吧。」
一會,大雄帶了肥福進來。
「肥福,這是我們的大佬。你夠運,大佬肯回水給你,還不多謝大佬?」大雄說。
「多謝大佬!」肥福恭恭敬敬地說。
「唔。」胖子點一下頭,對阿娟說「你把支票給他。」
阿娟遞過支票,肥福忙收下,猶豫一會,說「說好給現金的,這是期票,可兌換吧?」
「你不信我們嗎?」陳才說「我們行走江湖,最重要講信用,說過回水給你已優待你,你不信,把它撕爛算。」
「信,信,」肥福說,望了支票下「怎麼只有三十六萬?我被你們騙了二百萬,說好回水四十萬的。」
「四九三十六,正好是三十六萬,依行規回你兩成,我們只收你一點手續費。」大雄說。
「那隻羊牯給你四萬,正好啱數。」阿娟說。
「肥福,要不要隨你,不要阻著我們下台戲。」胖子說,話中自有一股威嚴。
「要!」肥福有點無奈「沒有錢我怎能著草呢?阿棠知道了,可能劈開我幾碌……啊!甚麼時候叫他入局?」
「下星期日。」陳才說「你還趕得及著草呢。」
「你們記得發誓說過不爆我出來啊!」肥福哀求說。
「得啦,我們最講義氣!」大雄說。
肥福話也不說,掉頭便走。
「哈…」胖子一聲冷笑「今次的羊牯怎樣?」
「看來比肥福易騙得多,但不能騙多,百多萬算了。」陳才說。
「為什麼?」阿娟問。
「他較年輕氣盛,趕狗入窮巷,他會和我們硬拼,不像肥福有家有室有所顧忌。」陳才說。
「好。」胖子大哥說「我先走,記得先騙要他發毒誓。」
「放心啦,又不是第一次。」陳才說。

四
大哥和大雄離去,只剩陳才和阿娟。不久、阿棠按址上來。
「才哥,娟姐、差點找不到你們,這裏好隱蔽啊。」阿棠說。
「我們說話時不宜太雜,在這裏談最適合了,是朋友的地方。」陳才說。
「依你們的計劃,去騙南北行大少沒問題吧?」阿棠說。
「當然沒問題。」阿娟說「他也不是常給人騙錢嗎?而且他有過億身家,騙他一百幾十萬有什麼大不了?」阿娟說。
「棠哥,這個牙籤大少都扺死,此人刻薄成性,有個老人家由佢伯爺起跟左佢四五十年,找個藉口將人趕走,攪到佢過唔到世,自殺死左。你話扺得佢丫?——我地作左佢的錢,你鍾意,可以分一份俾老工人既孤兒寡婦架。」阿娟娓娓而談。
「仲有啊,佢自己以為賭術高明,逢賭必精添。」陳才說。
「在法律上他不能告我們嗎?」阿棠說。
「你放心,這種事那可以告?」
「他找黑社會出頭又怎樣?」
「放心,他找黑社會,我們也可以找黑社會,如果有叔父輩替他出面,依行規,回兩成水給他。這樣更好,反而乾手淨腳無手尾。」陳才插口說。
「唔──好,我們便合作,但先說清楚,我分得多少?」
「三成啦,最少五六十萬。」陳才說「我們還要再找個人幫手。四個人合作,因你出本錢八十萬,才肯分三成給你。」
「好啦,才哥,見你介紹廣州單生意給我,大家合作玩玩。」阿棠說「那八十萬是預備給判頭的。」
「棠哥,你大把身家,不用扮寒酸了。」阿娟笑笑說。
「什麼話?我現金真不多。咦?不是你落場嗎?」
「不──」陳才說「我們還有一個兄弟,他精於賭術,我們三人暗中合作,這個牙籤大少難逃出我們掌心了。
「不過,為了大家誠意,我們合作前要在關帝面前結為兄弟,發誓不會出賣對方,你肯嗎?」陳才繼續說。
「好主意,才哥,最初我還有些耽憂,你這樣說最好了。我們便在關帝前結為兄弟。」阿棠說。
阿娟弄好香火,兩人上香結拜。
「我陳才今朝在關二哥面前與何兆棠結為兄弟,此後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我若出賣何兆棠則被人當街斬死、毒發身亡。我和何兆棠行騙懲戒趙大少的秘密,也不能向別人吐露,否則應驗剛才的毒誓。」
陳才鄭重的說完,向關帝拜了三拜,虔誠地上香。便要何兆棠跟他說一遍。
「我何兆棠今朝在關二哥面前與陳才結為兄弟……。」阿棠跟陳才的話說了一遍,再向壇前上香,算是完成結義儀式。
「棠哥,現在我們是好兄弟了。明天我們見雄哥,他教你賭術。但你學曉後,沒有我們,千萬不要用騙術啊。」陳才說。
「知道了,我們什麼時候和他賭?」阿棠問。「這星期天晚上,在豪華酒店一間房內。」陳才說。
五
他們賭狀元攤,在一張四方枱上設局。枱上放有用來扒攤的鈕扣,另外尚有一副麻將。用麻將來投注,同時又是籌碼。除莊家外,有三名賭客,各有一批麻將代表籌碼,筒子代表百元,索子是千元,萬子是萬元。花則代表十萬。枱中央放有縱橫麻將各七隻,四角和中央的麻將露出正面,一、二、三、四、五點。五在中央,其餘四角麻將背面向上。莊家扒攤前賭客將代表下注銀碼的牌押放邊角的點數上便可。
大雄在兩天前便教懂阿棠狀元攤的竅門,由阿棠做莊家負責扒攤。大雄在阿棠上家,陳才在阿棠下家。這樣,南北行大少便在阿棠對家。阿棠學懂了玩法,和他們兩人認真練習了一個晚上,以免臨時失手。
阿棠等人在酒店等候對手,對手竟遲了半小時才來,阿棠有些心急。
終於來了,原來是個頭髮稀疏的胖子。有五十多歲,這樣的老人竟然叫「大少」。此人有點邪門,夜裏還架著太陽鏡,果然刻薄可厭。
「這位是南北行的趙老闆」陳才介紹來人。
「這位是鴻運裝修公司大老闆何先生。」
趙老闆微一點頭,說:「帶來了現金?我只賭現金。」他向陳才說「介意我看看嗎?」
陳才示意,阿棠打開公事包,內裏有八十萬現金。陳才說「這裏有一百萬,要數數嗎?」
其實只有八十萬的阿棠有點著急,幸好沒有數。其餘各人也把帶來現金的公事包打開,各人表示大方,只望一眼沒有點數。
「何老闆知道玩法嗎?」趙老闆說。
「這個當然啦。」阿娟在旁說。阿娟今晚負責在旁記賬。
「趙老闆的眼有毛病嗎?很少人在室內也用太陽鏡的。」阿棠說。
「啊!老闆懷疑我啦?」趙老闆將墨鏡除下,交給阿棠說「這是普通的太陽鏡,因為我怕強光,眼壞了,真沒用!」
阿棠接過墨鏡戴上,與一般無異,交回給趙老闆。於是賭局便開始。
最初幾手上落都是幾萬元,阿棠依大雄教的暗號出手勢,五六手下來,阿棠心中盤算已贏了對方二十萬。後來賭注愈來愈大,到了第十五六手,快要開攤時,阿娟以極快的手法將一顆鈕扣撥向陳才的一方,陳才迅即把鈕扣藏起,阿棠懵然不知,結果應扒出四的便成三,趙老闆便由輸家變贏家。點算一下,他贏了百多萬,大雄和陳才也輸了三四十萬。趙老闆這時說不玩了,要結賬。明晚再玩。
大雄和陳才怨天尤人罵起來。但願賭服輸?各人都要拿出鈔票付款,陳才和大雄都要趙老闆明晚再來。阿棠點數,輸了六七十萬。
趙老闆拿錢下樓走了,大雄狠狠罵阿棠。
「棠哥,你怎麼攪的?累我們輸錢,我們怎可以讓他贏錢走?」阿娟說。
「他要走,我也沒辦法啊。」阿棠無可奈何說。
「你手腳就是不清不楚,怎會輸的?這鋪開一開二也好,偏偏開三的?這手贏了今晚我們可以不賭了。」陳才說。
「咦?怎麼枱邊還有一口鈕扣呢?」阿娟說。眾人一看,原來枱角尚有一口鈕扣未計算,其實應該開四,是他們贏了。
「阿棠,給你累死了,你扒攤時怎麼這樣大意,竟扒漏一口,幾十萬由贏變輸。」陳才說。
「應不關我事,當時大家一起看我開攤,沒有出錯的。」阿棠辯說。
「媽的!」大雄怒極,狠狠打了阿棠一巴掌「由你開攤,不是你錯,難道是我錯嗎?」
「…………」阿棠無言以對,撫著熱辣辣的臉頰。
「大家好兄弟,不用吵,明天我們再賭,把輸的贏回來。我總不信我們三人也贏不到他。」陳才作和事老說。
「我也輸了幾十萬,你怎能怪我?」阿棠說。
「輸你老祖,走啦!」大雄仍發脾氣,賭氣便下樓。其實他心裏暗笑,他知這那一口鈕扣是陳才在大家沒注意時從袋中拿出來作弊。
阿棠呆在一旁不願走,陳才和阿娟勸他看開點,可以在房間過夜,好好睡一覺。兩人相繼下樓,偌大的房間只剩下阿棠一人。

六
一會兒,大雄回來了,陳才和阿娟回來了。最後,趙老闆也回來了。還有四個大漢將酒店的房間擁得水洩不通,
「阿棠,究竟是什麼事?」阿娟問。
阿棠沒有作聲,抽一口煙,行到大雄面前,突然舉出右手。
「啪!啪!」兩響清脆的聲音,阿棠向大雄左右開弓,勁勁的打了大雄兩巴掌。大雄不能反抗,原來他被手扣反扣著。
「阿棠,你出賣我們,記得你在關帝前下的毒誓嗎?」陳才說。
「記得!何兆棠和陳才結為兄弟的毒誓。但我不是何兆棠,你也不叫陳才吧?我是新界北區特別重案組的何嘉棠高級督察,派來破你的天仙局。現在全部被緝獲。」
「你…….. 」趙大哥如夢初醒,向陳才怒罵:「蠢才,虧你還說查過他的身份。」
「大哥,他有心裝我們,身份證也可以假的…. 」陳才囁嚅地說。
「哼!——」大哥怒氣未消「你們沒有證據告我們行騙,而且你曾和我們合謀騙人。」
「哈哈,我不過演戲,扮裝修老闆,沒有罪的。我們已用最精密儀器錄得你們的罪證,看法官怎樣說。」
「肥福知道你真正的身份嗎?」大雄問。
「當然啦,沒有他報案,我又怎能混入你們的老千局呢!」阿棠說完,示意來人將他們帶走。
(原載《柳岸傳情》,今修繕刊出。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柳岸簡介:原名楊興安。以筆名柳岸發表小說。多年來從事文教工作。著有《金庸小說與文學》,散文《浪蕩散文》、舞台劇《最佳禮物》,及由香港作家協會出版之小說《柳岸傳情》等著述。現為香港小說學會名譽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