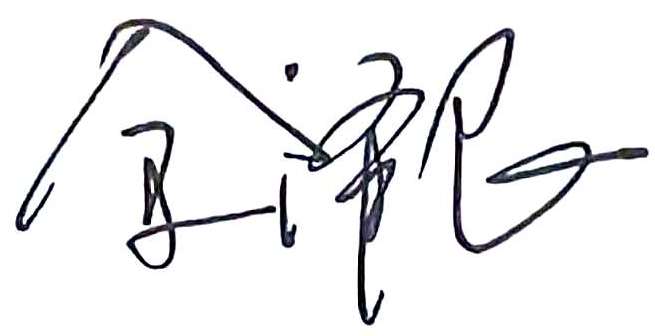
余澤民
中國旅匈作家、匈牙利語翻譯家
去年十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我作為他的老友和中文版的主要譯者也幸運地被國內讀者所關注,關於我與他的相識相知,我已經在不同場合講過不少,但對於《茹茲的陷阱》——這篇我視之為自己文學翻譯之路的重要節點的處女譯,我還沒有仔細地聊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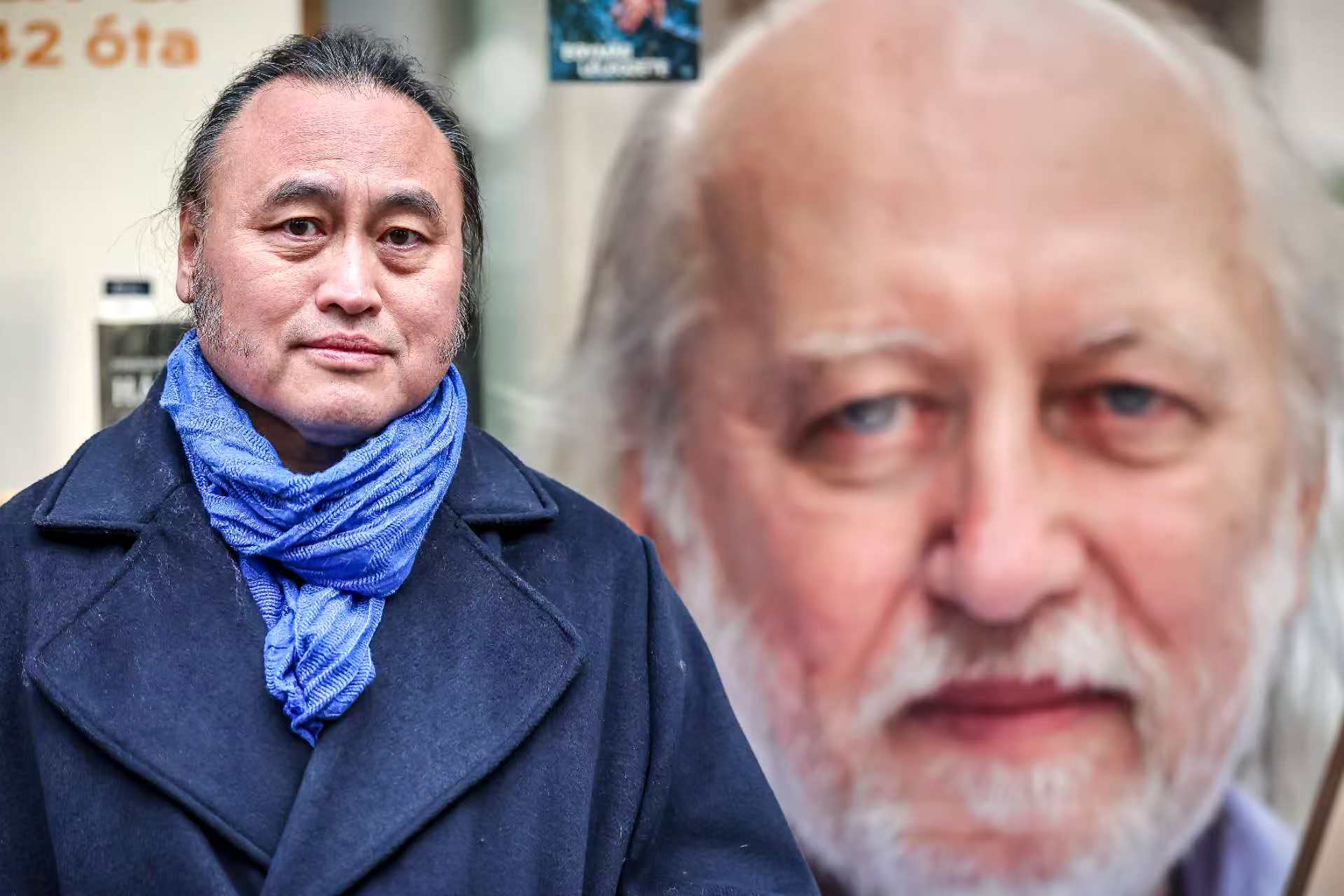
譯者余澤民站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照片前。(作者提供)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在塞格德的朋友家與拉斯洛相遇,當時我二十八歲,他三十九歲。當時他對中國古典文化十分癡迷,對中國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因此愛屋及烏,對我這個來匈牙利闖蕩的中國青年也產生了一見如故的親情,並與我建立了持久友情。一九九八年五月,我作為他的朋友、助手和翻譯,陪他到中國沿著李白的蹤跡走了許多城市,一個月的朝夕相處和沿路錄下的十四盤採訪錄音,對我這個文青來說,是一次影響至深的文學課,讓我對他的寫作產生了興趣。回到布達佩斯,巧的不能再巧,我的房東是位出版人,有一天我幫他將剛從印廠運回來的新書搬進倉庫,作為對我「苦力」的犒勞,他順手拿了一本油墨味還很重的新書遞給我,並說:「你留一本,是朋友寫的」,我這才注意到那黑色的封面:一個帶翅膀的光影,是新版的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短篇小說集《仁慈的關係》(Kegyelmi Viszonyok ),該書首版於一九八六年。
簡直是天意。要知道,當時我的匈語閱讀能力並不好,唯讀些簡單的報刊文章,文學書唯讀英文版的,但由於那趟中國之行,我的好奇心被激發了,拿到書後,我隨機翻到一篇乍看上去似乎「容易點的」,至少章節標題很容易:A→B,B→C,C→D……就這樣,我一腔興奮、硬著頭皮、翻著字典開始閱讀,可開篇的長句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那句子實在太長了,即使我把每個詞都查得清楚了,但還是花了半天的時間——像玩幾百塊組成的拼圖遊戲——才把這個複雜的句子弄明白意思,組裝起來,潤色通順,反覆讀過不下百遍。然而這個下馬威並沒有將我嚇住,反而讓我越戰越勇,當然也多虧了我那段時間失業在家,無所事事,最終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將這篇中文不到一萬字的小說翻譯了出來,烏拉!翻譯完最後一句「在她斜視的眼睛裏爍著撒旦的幸災樂禍的光亮」,我屏息了很久,皺著眉頭回味,真被這篇小說震撼住了。在那之前,我在同齡人中肯定不算讀書少的,但這樣的文字還從未讀過,或者說讀過類似的,比如卡夫卡,但與卡夫卡公文般簡潔的文字相比,拉斯洛的長句如流淌的熔岩,像神秘的迷宮,令人感到沉入深水的窒息。
這篇小說通過三個男人——均以第一人稱——的獨白,講了一串雖不驚險、卻扣人心弦的連環跟蹤與偷窺。作者用貌似無聊的日常小事,刻畫出人類在當下社會中的困窘與焦慮,表現出當代人孤獨、陌生、好奇、惶惑的心態本質,人們既對世界懷有好奇,又擔心習慣了的日子會有所改變,既希望與他人建立聯繫,又擔心喪失掉自己用長期孤獨換來的安全感,於是,人們選擇了自我保護過度的隱藏方式,選擇了既安全又能滿足欲望的暗中盯窺,就像粉絲們追星,追網紅,磕CP,看真人秀,隱藏面孔地在網上人肉,網暴,或像兩戶同住塔樓同層的對門鄰居,即便整日扒在「窺視孔」彼此窺察,也不會在樓道裏擦肩而過時主動打一個招呼,這是一種猥瑣的、病態的脆弱關係,一種虛設的、單向的不真實關係。這篇小說雖然寫於八十年代,但作者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使他預見到今日世界人與人之間既需要關聯、又難以建立信任的淡漠與隔絕。
如果講小說放到歷史和地域的放大鏡下看,這部作品精妙反映出經過社會動盪、體制轉軌後東歐人的精神狀態,既興奮又失落,既幻想又懷疑,既謹慎前行又躑躅回忘,雖然躺在歐洲大陸的版塊上,卻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精神放逐。從某種角度講,「東歐人」是「非歐洲人」的軟性同義語,這種——尤其是在意識形態上的——與歐洲母體的長久割裂,已使他們習慣將皮膚上的疤痕當成胎記,將體內的疝氣當成臟器……因此,偶然的清醒給他們帶來的並不是釋然,而是懷疑:惶惑多餘決斷,懷疑多餘信心,他們不但懷疑剛剛抬腳留下的足印,甚至懷疑曾經千遍萬遍堅信過的東西。懷疑,憂鬱,觀察,驗證,成了當代東歐人、特別是東歐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懷疑不僅給了他們用來反思的理智,也給他們造成自省的困惑。如果說米蘭.昆德拉的作品表現了「群體東歐人」直面人生的勇氣和良知以及對歷史和現實的批判精神的話,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作品描寫的則是「個體東歐人」獨特的心理世界,他們屈從下的懷疑、懷疑後的觀察以及觀察中的希冀。他筆下的人,像是魚缸裏的魚,雖然囚在同一個有限的空間裏,但不會在遊動中彼此觸碰,觀察是他們關係的紐帶,這種觀察是竊睨、無聲、不露聲色的,正是這種忘我的、以否定自身為形式的對他人存在的觀察,使他們印證到自己的存在。小說中的「跟蹤與被跟蹤」,象徵性地描寫了在當時封閉、專制、壓抑的東歐社會中「觀察與被觀察者」的依存關係,在萬馬齊喑的年代,正是這種懷疑的觀察和猥褻的興奮成為人們「還可以活下去」的心理動力,如同絕望中的風景,悲哀中的慶幸。
翻譯《茹茲的陷阱》,對我來說意義尤其重大,因為它是我的處女譯,甚至是第一次用匈語讀小說。正是那次笨拙的努力,讓我從那之後翻譯成癮,在接下來的兩年多裏,我翻譯了不同國家十幾位作家的三十多個短篇,主要通過匈語,但我並不曾做過翻譯夢,只是為了自學匈語,同時開始寫小說。感謝命運的安排,二○○二年,凱爾泰斯.伊姆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我戲劇性地獲得了翻譯他作品的機會,並在兩年內翻譯了四本書,之後我的翻譯生涯就開了掛,至今已經翻譯了約三十部作品,成為許多匈牙利作家的「中國聲音」。
從二○○六年一月份開始,經周曉楓介紹,魏心宏老師委託我在《小說界》開了一個「外國新小說家」專欄,我一做就是十年,譯介了幾十位歐美作家,第一期我推出的就是拉斯洛的《茹茲的陷阱》,那也是他第一次在中文世界亮相。幾個月後我又翻譯了他的另一個短篇〈奔跑如斯〉;十年後我翻譯了他的代表作《撒旦探戈》,隨後是《反抗的憂鬱》和《仁慈的關係》,後者是我與康一人合譯,收入了我的這篇處女譯;去年我的新譯《溫克海姆男爵返鄉》剛已出版,正踩中了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間點。在我們相識的三十多年裏,隨著我們友情的加深和翻譯的積累,我對他作品內涵和風格的理解也愈加深入。在一次題為「發瘋在天堂」的文學講演裏,拉斯洛自己曾這樣闡述:「對於現代歐洲人來說,尋求完美的欲望是如此狂烈,如此令人難以忍受、難以遏制,恰恰如同他們對一切完美事物的懷疑。」因此,他們只能「孤獨地、遠離上帝站在宇宙的中央。」
在我的文學生涯中,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和凱爾泰斯是我的兩位貴人,若沒有他倆,我恐怕至今還在無目的地漂泊。他倆屬於兩代人,生活閱歷和創作主題雖然不同,但精神上有著共通之處,都是自覺接受精神放逐的「遠離上帝者」,用超乎常人的敏銳與執著從作為人類一份子的自身尋找上帝視角。在《茹茲的陷阱》裏,我們通過一雙幾乎不帶感情色彩、俯瞰眾生的眼睛看到我們自己,甚至看到作為撒旦化身的茹茲大嬸出場,她很得意,因為我們都踏著她譜寫的探戈曲在陷阱中跳舞,通過文學,我們既是滑稽忙碌的蟻群,也是饒有興味的觀蟻者,帶著淡漠的憐憫。
世界日趨開放,精神日趨封閉。大資料和自媒體,讓個體變得裸露無助。這是現代人的悲劇:除非作為偷窺者,否則無法介入他人的生活。偷窺,是將自己置於安全的地方而讓他人暴露,進而獲得某種控制的快感。當然,人們之所以選擇偷窺解決好奇引發的焦慮,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心,拉斯洛作品的現代性正在於此。在瞬息萬變、充滿虛妄的資訊社會,安全感是人們應對生存的心理內核。面對欺騙、算計、背叛和愛滋的威脅,人們寧可用意淫代替性愛。拉斯洛描寫的,既是喪失了庇護、在人群中驚慌失措裸奔的人,也是衣冠楚楚、不露聲色地為窺視他人裸體而興奮的人。拉斯洛是一位嚴肅作家,準確地講是藝術家,既重內涵,又求文字,執著於創作,不在乎流行,他不屑使用「二手文字」,而是近乎偏執地用自己的長句搭建城堡,將母語的特點發揮到極致,極大增加了閱讀難度,難怪有匈牙利同行評論說,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筆是一支「語法魔笛」,即使對許多匈牙利人來說,讀他的書也是挑戰,更不要說翻譯他的書了。
卡夫卡說:「在身心完全健康地方,不會存在精神生活。」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承繼了卡夫卡的語言遊戲和思考邏輯,娓娓講述一個又個令人深思、驚詫、甚至毛骨悚然的人類寓言。跟卡夫卡一樣,克拉斯諾霍爾卡伊也生活在動盪時代,前者親歷了二十世紀初的奧匈帝國衰亡,後者則是二十世紀末的東歐劇變,特別是在二○一六年問世、作為《撒旦探戈》續篇的《威克海姆男爵返鄉》,用更繁複的技巧表現出匈牙利人在「新時代」的困惑。覺醒帶著茫然,變形帶著陣痛,封閉帶著憧憬,開放帶著驚恐,好奇帶著焦恐,興奮帶著克制,控制帶著脆弱。這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世界,或者說,根本就是一個熱病時代:城市在摩登的烈日下燃燒,到處是金屬、玻璃、塑膠、路牌與彩色的垃圾,行將倒塌的大廈,痛苦嘶鳴的汽車,倉皇行走的路人,思想的歐洲變成了物欲的歐洲。借用翻譯家、詩人高興先生的一段評價:「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關注人類普遍境況,而無望的等待、厭世情緒、反英雄、末日景象、模糊、不確定性、遊戲、偶然性、無序、反諷、轉喻、內在性、被抽空意義的人生,所有這些為他的小說抹上了濃鬱的後現代主義色彩。」
拉斯洛曾說:「歐洲的新人類,完全將目光轉向了自己,既無理想,也無思想,既不信上帝,也不信柏拉圖……」,人們用智慧計算得失,用汽車搬運欲望,利用戰爭謀利,在和平中建廢墟,用早已破碎了的藝術和宗教的瓦礫搭建虛妄的城市,將不復存在的東西像存在之物一樣保存,克拉斯諾霍爾卡伊通過他寓言式的寫作,通過對人物驚恐面孔的刻畫,轉述上帝的末日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