淵懿
台灣文壇以「冷面笑匠」著稱的作家袁哲生素來善用兒童視角觀察社會,並用冷靜平淡的文字構建出世事無常,世間飄渺的獨特美學空間。這篇《秀才的手錶》講述了一個名叫燒水溝的山村,有一位戴手錶的秀才,雖然嚴格按照時間去郵局寄信,卻總是不能計算出郵差準確的收件時間,甚至和「我」這個沒有手錶的孩童玩猜測郵差準確出現的遊戲也屢屢失敗,最後滿懷希望前往火車站寄信的秀才,卻死於沒有準時出行的火車輪下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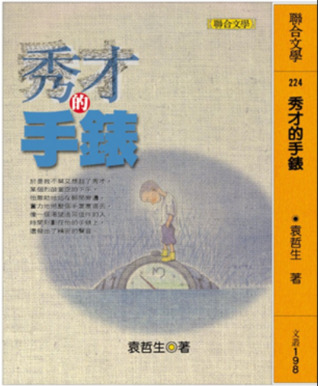
初讀此文迷障重重,一頭霧水,不知作者所言為何物。然,細讀二、三遍,再逐步建立了「人」和「物」之間隱含的內在關聯,此文主旨便撥雲見日,水落石出。
秀才
「秀才是誰?他住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麼人?他的錢從哪裏來?為什麼大家都叫他秀才?」,有關秀才的身世,自始至終也沒有給出答案「三十?四十?或者五十?」,甚至作者自己也在不斷追問秀才的年齡,接著作者又用十分肯定的語氣告訴讀者「在我們燒水溝這個地方,秀才可是少數幾個戴了手錶的人。」,為什麼一個偏僻山村不真實的秀才卻擁有一塊來自西方的手錶?不過作者似乎沒有任何揭曉答案的意圖,只是繼續借用秀才的口吻講到:「自動錶裏面有一個心臟,需要人不時地刺激它一下,否則便會停止跳動死翹翹了。」。此處,作者用手錶的滴答與人的心臟跳動做比,暗示文中時間線有兩個維度,一個是手錶客觀記錄,一個是人的內心律動,這看似不經意的一筆,不僅讓整個故事的內涵和外延得以提升,也為下文的發展和結局埋下了伏筆,這也正是作者行文「於無聲處聽驚雷」的高妙之處。「我」每次陪同秀才寄信,都能夠依靠天生的超人聽力準確判斷郵差的到達時間,可擁有精確計時手錶的秀才卻永遠無法猜中郵差何時出現,原因就在於秀才執著地認為這個世界「就像黃曆上記載的一樣,是按照精確的時間在進行著的」。
「不論春夏秋冬,秀才總是穿著全套的,厚厚的大西裝」,這是秀才除了手錶之外的另一個執著,「西裝」和「手錶」這兩樣西方舶來品都被秀才熱情接納,作者意圖十分明顯,既然被稱為秀才,內心對中國道統定是有所繼承的,但是秀才對西方文化也是全盤接受,甚至頂禮膜拜,這便為秀才「每隔幾天就用毛筆寫一封信」的行為找到了合理依據。
「至少我看得出來秀才的字寫得很用力,也很漂亮」。秀才是道統的繼承者,因此必須有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寫字的態度也必須是極其認真的,但是秀才在信中寫了什麼內容,作者便刻意不告訴你。作者通過郵差的口想讓讀者知道的是,秀才寄出的信不僅不貼郵票,甚至「那些信封上的地址根本就是秀才自己發明的」,可是,對於一封封寄不出的信,秀才卻是毫無怨言,「把信交給我拿著,然後載我到水窟仔那邊去,拿糖果給我吃」。由此可見,秀才寫信的重點不在於寄給誰,而在於認真寫信和執著寄信的過程。行文至此,我們不難看出,對西方文化崇拜的秀才,知道自己的「異想」在閉塞的燒水溝村是不合時宜的,他的內心充滿矛盾和痛苦,他需要宣洩需要表達需要傾訴,但他又不知道向誰宣洩向誰表達向誰傾訴,於是他選擇不斷寫信、寄信的過程來釋放壓抑在內心的沉重塊壘。
最後,秀才從郵差處獲悉,郵局的信都是通過火車寄出的,於是準時趕到車站,最終因不準時出發的列車,而慘死在滾滾的鐵輪之下。這裏,讀者已經完全明白,秀才篤信手錶計時,聽力下降,而導致死亡,他死也不明白這個世界還有一套潛藏在人們內心的時間刻度。
其實,秀才的死亡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為,走出燒水溝村去親自寄信的秀才希望能將信件寄達心中的收信人,並從此獲得徹底解脫,可是秀才的內心也明白他的這封沒有郵票,虛構地址的信是不能改變被退回的結局,對於這樣完全沒有希望的結果,秀才是不能接受的,於是秀才需要以死明志。不過,作者要強調的絕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秀才努力和自我救贖的過程,這樣的死便是拯救整個燒水溝村的——「向死而生」,此處彰顯的深刻與魯迅批判蘸著革命者鮮血治癆病的麻木民眾有異曲同工之妙。
阿公
阿公是燒水溝村的一個普通手藝人,憑著手中的剃頭刀自食其力。在阿公所代表的燒水溝村的普通百姓眼中,秀才「這種人只是『放雞屎的』」。
雖然阿公對秀才橫豎都是看不上眼,但阿公卻有一套和秀才一樣的西裝,不過阿公「每年只有過農曆春節的那幾天才看他穿一下」。燒水溝村的普通百姓對「西裝」這樣的外來事物所抱持的態度是新鮮和好玩。
常把生死看淡的阿公,在一個文中虛指的「那年」又去算命,結果命相特別不好「舊曆十一月十九日和廿九日會有大地動,當中一次會把台灣島震甲裂做兩半……」。
對未來失去信心和希望的阿公,在家人的反對聲中也買了一塊錶,不過阿公帶上手錶後並不是和秀才一樣被手錶的時間刻度所綁架,「雖然他每天的作息還是一模一樣,生意也沒有好起來,但是手錶卻是那樣活生生地讓他安心著。」,這裏作者再次不厭其煩地強調,在阿公為代表的普羅大眾眼中,中國傳統文化是沒用的,「手錶」和「西裝」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也是沒用的。

「我」
「小時候,最令我懷念的,就是陪秀才去寄信的那一段時光」,故事開篇便將「我」與秀才最執著的一件事——寄信,捆綁在一起,而我願意陪同秀才寄信的原因是,能夠憑著超人聽力在與秀才玩郵差到達時間猜測的遊戲中屢屢獲勝,於是「我就有吃不完的金柑仔糖和鳥梨仔」。我不僅可以準確聽出郵差到達的時間,也可以聽到阿公與算命仙仔的對話,於是「我」便於秀才和阿公之間有了某種內在的聯繫。
基於地震情節的鋪排,阿公要帶著「我」離開世代居住的燒水溝村,作者將「我」和阿公的影子比作「一支分針和一支時針被聯結在一起慢慢地走動著」,這除了是一個不錯的修辭外,也是作者想要表達老一輩與下一代的交接。當「我」和阿公見到火車時,便親眼目睹了秀才死於車輪下的事實,於是「我」順理成章獲得了秀才的手錶,「我」也完成了與秀才的交接。
秀才死了,阿公帶著我離開燒水溝這個舊式的空間,我用「放尿」的方式,將傳統束縛的枷鎖拋棄,戴著秀才的「手錶」這個西方文化的象徵走向未來,「我」的過於常人的聽力喪失了,意味著我回歸到普羅大眾。「我」是燒水溝村的新生代,最終是衝出傳統走向現代,還是和秀才一樣的宿命,不過獲得阿公和秀才雙倍加持的「我」,有破也有立,希望是有的……
綜上分析,我們既可以感知袁哲生作品意象巧妙使用和故事不經意鋪排又環環相扣的藝術特色,也能從人物塑造和故事兩條時間線的脈絡中解析文本的主旨——時代變革背景下的眾生,在社會秩序重新構建過程的複雜心理和多維面向。
註:本文引文皆出自袁哲生:《秀才的手錶》,台北:聯合文學,二○○○年。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淵懿簡介:本名袁疆才。七十年代西北邊陲呼喊著跌落人間,隴上人家馬不停蹄野蠻生長。當下,垂釣香江,文字覓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