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祥蘭
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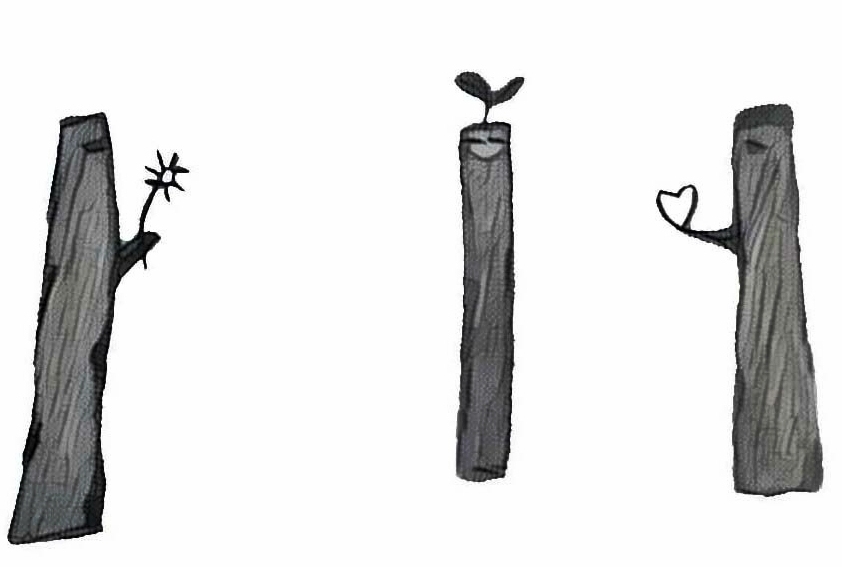
這些長短不一、粗細不等的木棍,在我手裏活了起來。(作者提供)
夏日傍晚,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雨襲擊了小鎮。
我坐在灶坑旁燒火,我要趕在天黑前將晚飯做好。
我偶爾抬起頭,望向門外。
剛才還是瓢潑大雨,現在變成了細長的雨絲,漫不經心地敲打著屋檐。天空被雨簾攪得昏昏欲睡,一點精神也沒有。
我想著還在地裏勞作的母親,這場雨一定將她澆成了落湯雞。
木頭在灶坑裏燒得熱烈,通紅的火苗躥上躥下,映照著慢慢暗下來的房間。
我一邊往灶坑裏添木頭,一邊拿著幾根小木棍玩兒。
這些長短不一、粗細不等的木棍,在我手裏活了起來。
我賦予它們每個新的生命,我為它們每個取一個好聽的名字。我讓那根細長的叫芨芨草,短小的叫蝴蝶;我讓那根表皮光滑的叫玉蘭,粗糙的叫蜻蜓。我還要為它們每個安排一個身份,芨芨草是我們的班長,蝴蝶是我同桌,玉蘭是那個愛哭的女孩,蜻蜓是勞動委員。
好了,現在,我要為它們編排一些故事了。
我讓蝴蝶和玉蘭跳了一會兒皮筋,讓芨芨草和蜻蜓彈了一會兒玻璃球。
我覺得這樣太枯燥,乏味。
我開始讓它們四個玩起了捉迷藏。
這樣玩了一會兒,也覺得沒勁。
要不,就讓芨芨草和蜻蜓玩打架的遊戲。
這樣,好像更沒意思。
還是來點別的吧,最好是有趣的事。
那麼,就讓芨芨草喜歡玉蘭吧,如果蜻蜓也同時喜歡玉蘭會更有趣。剩下一個蝴蝶,我該怎麼安排呢。我想了一下,乾脆就讓她喜歡蜻蜓算了。
我為它們編好了故事,現在開始表演了。
它們現在是有生命的人了,所以,我要用他、她和他們來稱呼。
我左手拿著玉蘭,右手拿著芨芨草,開始登場。
在教室的走廊裏,在日光照耀的地方,玉蘭依在斑駁的牆壁上,認真地看一本小人書。光影投在她白皙的臉上,她長長的睫毛扇子一樣忽閃著,每扇動一下,攪動得光影也跟著顫抖。
遠處,芨芨草正向玉蘭走來。他腳步輕盈,生怕踩碎了一地的光影。他一步一步,一點一點,在光影裏移動,慢慢向玉蘭靠攏。眼看就要接近了,這時,上課鈴聲響了。
玉蘭從小人書上抬起頭,光影也隨即閃去。
她沒有發現,那個踩著光影,正朝她走來的芨芨草。
她更沒有發現,走廊的盡頭,在光影照不到的地方,還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著她。
當然,他們三個都沒有發現,在教室裏,一個女孩透過厚重的玻璃窗,透過耀眼的光影,一聲不響地望著他們三個。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收在女孩的眼裏……
我感覺眼睛發澀,實在太累了。我放下玉蘭和芨芨草,抬起頭來。
門外,雨絲還在淅淅瀝瀝。
暮色正在降臨。
偶爾有雷聲在天邊滾動。
母親還沒回來。
我望了一會兒昏迷的天空,聽了一會兒雨聲,就收回了目光。
我覺得,還是我的遊戲更有趣。
我接著剛才的故事,繼續往下演。
課堂上,語文老師正在朗讀一首愛情詩。我們的語文老師是位漂亮姑娘,她年輕又活潑,像詩一樣風情萬種。她讀得很動情,就像在講她自己的愛情。讀到精彩處,會舞動手臂,伸長脖子,聲音都變了調。
玉蘭聽得入了迷。
蜻蜓的注意力不夠集中。
他的眼睛不時瞄向玉蘭,雖然他很喜歡愛情詩,但他覺得比愛情詩更美的,是玉蘭那優美而光潔的頸項。
蝴蝶的注意力也不能集中。
漂亮的女老師講的愛情詩與她無關,她心裏只想著蜻蜓。她覺得,自己也有類似愛情的東西,在心裏搖曳,像春天的芒草一樣,滋滋瘋長。她迷離地望著蜻蜓,她看見蜻蜓的目光裏全是玉蘭優美而光潔的頸項。而她自己,眼裏全是憂傷。
坐在後排的芨芨草,用不著刻意,只需目光平視,就能看見玉蘭肩頭上的兩條小辮子。他一邊聽著愛情詩,一邊望著那兩條小辮子,感到格外甜蜜。
在這出戲裏,最幸福的是玉蘭,因為她什麼也不知道。最傷感的是蝴蝶,因為她什麼都知道。
天黑了下來。
暮靄衝進了屋裏,東撞西竄,只一會兒功夫,屋裏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我不得不放下蝴蝶和蜻蜓,停止遊戲。
這四根木棍的故事,讓我疲憊不堪。
我收回思緒,抬起頭來。
門外,雨依舊淅淅瀝瀝,叮叮噹噹,不急不徐,敲打著門窗。
我聽見院子裏有腳步聲,看見雨霧裏有人影晃動。
我知道,是母親回來了。
我的遊戲也就結束了。
春逝

春逝(作者提供)
從我家窗口能望見小巷對面的那個花店。
夏天的時候,我推開窗子,就能聞到花的清香。有時濃烈,有時淡雅。時間久了,我可以識別出各種花的香氣。那淡雅的是百合,濃烈的是玫瑰,而那若有若無的一定是茉莉。
我還能看見坐在花店門前的那個小男孩。他叫久久,六七歲的樣子,和我年齡差不多大。久久長得精瘦,因為瘦,他的腦袋顯得特別大。他的眼睛也大,但目光空洞無神。
他總是坐在一把板凳上,看著巷子裏的人走過去,又走過來。他就這樣看著,能看上一整天。
聽大人說,久久得了一種怪病。他父親帶他去縣醫院看了幾次,沒看好,後來就不看了。
每天,久久的父親打理著花店,剪枝、澆水、插花。五顔六色的花擺滿了半條巷子,那香氣會拐彎,隔壁的巷子也能聞到。
久久坐在花店前,看著行人走過去,又走過來。走過來,又走過去。如果長時間沒有行人,久久就望著空蕩蕩的巷口發呆,那裏什麼也沒有。
偶爾,有孩子在巷子裏嬉笑打鬧,捉著迷藏,彈著玻璃球。久久就認真地看著,像是看一場戲,不願意漏掉一個細節。不經意間,嘴角會流露出一絲孩子的笑,眼神也閃亮了一下。只一瞬間,那明亮的眼神又暗淡下去。
每天的午後時分,巷子裏格外靜。沒有行人,也沒有玩耍的孩子。
久久長久地望著巷子裏的那棵柳樹。
有風吹過,柳枝就甩起長袖,像是要抓住什麼。有幾次,久久看見一隻灰山雀安靜地站在柳枝上唱歌。它唱了很久,久久聽了很久,這期間,他們有過眼神的交流。
夏日悶熱而單調,我午睡醒來,推開窗子,看見久久仍然坐在板凳上,一動不動。他穿了一件月白色的確涼襯衫,一條藍色棉布短褲。風吹過來,他的頭髮向空中伸展了一下,又默然垂下。他的樣子是那麼孤單。
秋天的時候,久久穿上了棉秋衣。他坐在板凳上,看著枯黃的落葉被風吹著到處跑,尋找回家的路。
天越來越冷了,雪下了一場又一場。巷子裏的行人也少了。
更多的時候,久久望著光禿禿的柳樹發呆。冬天的柳樹也像個病人,掉光了頭髮,穿上了厚厚的白棉袍。偶爾,有鳥兒站在白棉袍上唱歌,久久就安靜地聽著。 他覺得這只鳥兒就是夏天經常給他唱歌的那隻灰山雀。
當白棉袍上沒有鳥兒的時候,久久就望著天空。寂寞的雪花,還在替蝴蝶飛著。久久覺得雪花墜落的時候,是有知覺的,一定很疼。
冬天的早晨,窗玻璃上結滿了各種各樣的霜花,有森林、梅花鹿,也有牡丹。這些森林、梅花鹿、牡丹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不見外面,看不見花店,也看不見久久。
我開始用嘴哈氣,用手一點一點摳玻璃上的霜花。我摳掉了一片樹葉,又摳掉了一朵花瓣,終於摳出銅錢大小的一塊亮光。我將眼睛貼上去,我看見了飛舞的雪花,看見了花店,也看見了久久。久久坐在雪地裏,一動不動,成了一個雪人。
四月到了,積攢了一冬的雪開始融化。柳枝開始長頭髮了,冒出綠色的逗號。風一陣一陣吹著,逗號一點一點長著。從南方歸來的大雁呱呱叫著,發布了這個春天的流行色。
早晨醒來,窗子乾乾淨淨,不再結霜花。
我趴在窗子上,看見了逗號,看見了花店,卻沒有看見久久。
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久久再也沒有出現。
聽大人說,久久去了天堂,去了綠色的地方。

作者(作者提供)
盛祥蘭簡介:女,出生於吉林撫松,現居住珠海,任珠海傳媒集團主任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作品先後發表於《人民文學》、《詩刊》、《上海文學》、《作家》、《散文》等刊物,著有詩集《偶然》、《我們都是宇宙的一撇》,長篇小說《愛的風景》,小說集《流放的情感》,散文集《彼得堡之戀》、《似水流年》、《童年春秋》等。作品被翻譯成世界語、日語,入選多種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