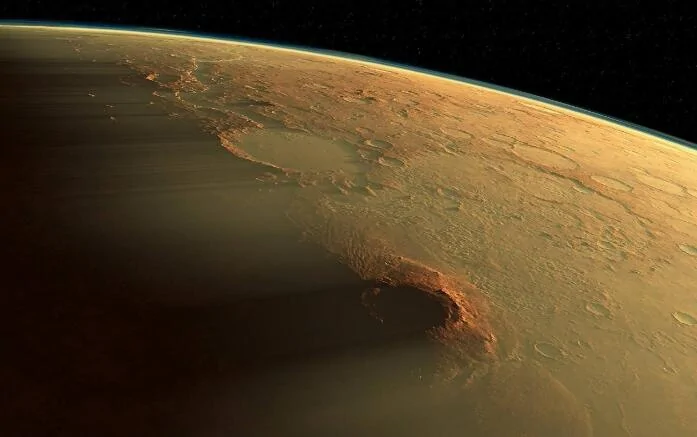柳岸

一
「砰!」麒麟鎮公安派出所的大門忽然被人打開,一個人冒冒失失的衝進來。
「什麼事?———」陳水德反應快,忙喝住來人。定睛一看,原來是同村的陳水旺:「你——?」
「我發現一具死屍——。」陳水旺喘著氣說:「是一具艷屍———。」
「艷屍?」陳水德問:「在哪裏?——什麼艷屍?死者是個年輕少女吧?」
「是,是吧?」陳水旺還喘著氣說:「光著屁股,躺在草叢裏。」
「啊!」派出所的人都哄起來,近期的治安差了,上月便發生了兩宗姦殺案,死者身份不明,大概是外省人到這裏找工作而不幸遇害的,正茫無頭緒,現在又多一宗了。
「你有沒有翻動屍體吧?」陳水德問。
「沒有——。」陳水旺說:「這點常識我倒有,也沒有弄遭現場的線索。我立即帶你們到現場吧。」
「好!立即出發。」陳水德是這裏的大隊長,近日備受上司的壓力,這次兇案,他不憂反喜,因為多了一點偵查的線索。
他們來到現場,原來是高速公路旁。一夥人下了車,隨著陳水旺翻身跳到公路下的草叢。現在差不多晚上九時了,眼前一片漆黑,拿著電筒搜索也有困難。公路上,仍有不少汽車高速的呼呼駛過。
他們向前摸索走了十餘分鐘,有些人不耐煩了。
「老兄,你肯定是這兒嗎?」一個公安問。
「是這裏,不會弄錯吧?」陳水旺敷衍別人,卻問起自己來。
「水旺,你怎會跑到這裏來?」陳水德突然好奇地問。
「唉!我原是要趕路到廣州的,誰知水喝得多了,忍不住,半途便要下車小便。想走得遠一點,撥過草堆,正要小便,卻見到這裏躺著一具屍體,嚇得我………. 。 」陳水旺繪聲繪影地說。
「嚇得你撤尿了……. 。」旁邊一人取笑他。
「不!我舒舒服服把尿痾完………,那時天色漸黑,屍體身上好像還有衣服,屁股卻是光脫脫的映著微光,我便第一時間向你們報案了。」陳水旺說。
「唔——。」陳水德畢竟是隊長,頭腦冷靜,耐心地聽著。
「找到了!找到了!」前面一個公安突然大叫起來。
大家聽到後都有點興奮,一起奔將過去。只見一具沒有褲子的屍體伏在草叢上。大家都默不作聲,陳水旺跑得最遲,喘著氣說:
「你們都看到屍體啦——我沒有說謊吧?」
「怎樣?」副隊長張誠問。
「把她翻過來,小心一點。」陳水德說。眾人見到屍體小腿上還染上一大灘血,小心弈弈地把屍體翻過來,三支強力電筒集中照射在屍身上。
「啊!」
「噢!」
「怎麼?………. 」
公安不約而同喊出來,陳水旺帶著遲疑,竄著身向前一看——。
「噢!怎會這樣?」陳水旺說「怎會是個男的?」
沒有褲子的屍體,一眼便可以看出是男是女,原來是一具男屍。
「這是你說的艷屍嗎?」
「這……….. 這恐怕是吧!」陳水旺說,有點尷尬。
不知道為什麼,「艷屍」是男的,大家好像有點失望。
「怎會這樣呢?」陳水旺喃喃自語說。
「水旺,會不會這樣呢?一個男人被謀殺了,棄屍在這裏,便是這樣簡單。」陳水德說:「你總不能說原來是一具女屍,被我們發現了,變為一具男屍?」
「是……是……。陳水旺還神經兮兮地說「為什麼一個大男人被人殺了,把他的褲子脫去,拋在這裏,一定有內情,有姦情………」
「唔………。這個你也說得對——。」陳水德突然嚴肅起來,這案件太不尋常了。
「現在怎辦?」張誠問。
「小心搜集證據,些微地方也不能疏忽。」陳水德說。
「是!」張誠應命而去。
陳水德和陳水旺兩人仍然呆立當場,摸不著頭腦。
二
「張誠,死者的身份,查出來沒有?」陳水德問。
「沒有,一點線索也沒有。」
「他身上有什麼證件嗎?」
「沒有,他只穿了件普通的襯衣………給泥土污迹混滿了………。」
派出所沒有聲音,又多一條命案,但總是毫無頭緒。
「砰!」突然門外傳來一陣巨響,把眾人嚇了一跳。
「什麼事?」陳水德問。
一人奔出門外,立即回來說。
「老許不知怎麼攪的,拖了架車回來,泊位時卻碰壞了公車。」
「什麼?碰壞了車?不影響出差吧?」張誠說。
「你自己看看好了!」那人說。
「不知誰人把車子停在公路,人卻跑了………。」
「公路上有架空車?——」陳水德說:「張誠,搜搜車上的東西。」
「什麼?——哦——」張誠會意,立即奔出去。
他們在車廂找到一件外套,袋著證件,是中港司機杜有財的。核對之下,杜有財便是昨晚發現的死者。
「噓!——總有點線索。」陳水德舒了一口大氣,回復不少自信。
「我去聯絡他的家人朋友,希望找到線索。」張誠說。
「好!便這樣辦。看看他有沒有仇家,——也看看有沒有桃色事件。」陳水德說。
「好!」張誠說:「我立即去辦。」
「驗屍報告怎樣?」陳水德問。
「最快要三日後才有。」張誠邊走邊說。
陳水德點點頭,取出根煙來,深深吸了一口,好像已回復破案的信心,眼梢望著張誠矯捷的腳步。

三
「他是個好人,每晚放工都回家陪伴我,………想不到竟有人這樣害死他!」杜有財的妻子哭成淚人一樣對張誠說,她專程從香港趕上來的。
「你放心,我們一定盡力破案,找到兇手槍斃。張誠只有這樣說安慰她,頓了一頓,又說:「他常常到內地嗎?」
「還是兩三個月前開始——」杜太太抽咽著:「就是他失業開始,朋友介紹他運貨到內地,一星期最多兩三天,幫補家計啊。」
「唔——。」張誠明白原來杜有財是個走單幫的司機「他有仇家嗎?」
「沒有,他挺愛幫助人的,吃小虧從不計較,所以我說他是好人。」
「唔——好人,他太好人了。」張誠若有所思說。
「你不信嗎?」杜太太微慍:「你對死者太不敬了。」
「信!信!你是他的太太,最了解他的了。」張誠言不由衷地說。他出道以來,從沒有見過肯平白做好人的人。突然,他對杜太太說:
「你有杜先生的照片嗎?可以給我一張吧?」
「唔——,可以,對破案有幫助吧?」杜太太從皮包裏抽出杜有財的照片來。原來她隨身放著丈夫的照片,可見他們真的十分恩愛。
照片是營業車職工會的會員證,是三年前的了。
「照片像他本人吧?」張誠見到照片上的青年,倒也英俊,懷疑與他見到的屍體不符。
「這是十年前拍的。他喜歡這照片,現在快到四十歲了,反而留了一把長頭髮,但認識他的人一定認得是他。」杜太太說。
「謝謝你,這個極有幫助了。張誠把照片收好。「遲些會交還給你的。」
「一定啦,否則不會給你了。」杜太太這樣說,可見她對照片的珍愛。
張誠送走了杜太太,心裏立即有個主意,一個中年男子對妻子這樣好是反常的,他一定在內地包二奶,這差不多是鐵的定律。何況,他死的時候褲子被脫去,一定跟桃色事件有關。
首先,他找好朋友福進,他是做攝影的,他叫福進替他翻做照片,一張翻拍,一張把頭髮弄長了,差不多垂到肩膊,跟發現的屍體一樣。吃完晚飯去取相,見到長髮的杜有財,請驟眼看去果真像個女子,啞然失笑說:「果然像個艷屍呢!」福進還摸不著頭腦,張誠便跑了。

四
下嶺村是著名的二奶村,所以一般女子都漂亮。有些帶著孩子,有些終日無事聚在一起打牌。一些則東家長,西家短說是非。一些解決了生活,香港的丈夫又不在,便繼續營醜業,只是揀好人家才做;一些更大膽,招惹本地較俊朗的男子上牀,大家玩玩便算。這些二奶自成一種氣候,張誠瞧兩眼便瞧出來。但她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怕公安,希望討好公安。
張誠坐在茶樓,人來人往,不知怎樣入手。呆坐一個上午,決定晚上再來。
入夜,吃過了飯,他挑了一家暗營牌局的食店坐下來。七八點了,七八個少婦進入房,劈劈啪啪玩起麻將來。張誠突然舉步入內。
「什麼事?」一個婦人見他進來,邊打牌邊問。
「我是公安。」張誠單刀直入的說。
兩檯麻將霎時停下來,氣氛靜穆可怕。
「我們沒犯事,可為什麼找我們?」一個女子說。
「不是假公安吧?怎麼一個人來的?」另一人說。
「你喜歡大批人來也可以,只要我撥個電話——」張誠傲然說。
大家被他的氣勢懾服,再不敢作聲。
突然,一個店伴走入來,見到場面,也是一呆,隨即說:
「什麼事?」
「公安辦案,你出去!」張誠把證件一揚,店伴見了,默默無聲倒退出去。
「什麼?要抓我們?」一個比較漂亮的少婦說。
「不!我找你們幫忙。幫助我,他日你們有好處。」張誠說。
「哦——。」眾人都鬆了一口氣。
「難得這樣齊全,聚了許多人——。」張誠說著,一個少婦應聲說:
「今天是小娟的生日嘛——。」她說的時候,眼睛瞟向那漂亮的少婦。
「恭喜啦!——」張誠打斷她的話,微微一笑,氣氛輕鬆下來。
張誠掏出杜有財的照片說:
「你們看看,認識不認識這個人——。」
眾人圍攏起來,七咀八舌。
「還英俊啊!我倒希望認識他。」不知誰叫起來,跟著笑作一團。
「會不會是你們朋友中的情人?」張誠說。
「噢!」她們努力去想。
「他犯了什麼罪?」一人說。
「他死了!」
「啊!」眾人又是一陣嘆息。
沒有人認識杜有財,張誠也不盡失望,到底是一起大海撈針。他再把長髮的杜有財照片拿出來,說:
「這個人最近有沒有見過?」
「看看。」眾人又把照片傳閱。
「啊!我認識他——。」一個少婦突然說「他是海珊的老公。」
「海珊?」張誠問。
「是,是阿珊的老公。」那女子說。
「怎麼阿珊有這樣的老公我不知道的?」另一個女子說「她老公不是阿勇嗎?」
「你那裏知道許多,她丟了阿勇。那天在她家中我遇到她們,阿珊正式介紹給我認識的。」這個女子說得肯定,證明她的厲害。
「哦——」張誠想,恐怕是宗情殺案了,便說:「告訴我怎樣找到海珊,你們可以繼續玩牌了。」
「你不要說是我告訴你的——。」那女子說「大家也不要把今晚的事說出去,才是好姊妹。」
「是!是!」
「對!對!」
張誠滿心歡喜寫下地址,說聲打擾便走了,身後卻仍然聽到那群二奶七咀八舌。
五
「你是鄧海珊吧?」張誠問。
「是。」大廳上鄧海珊長得斯文秀麗,怯生生的,怪惹人憐愛。她瑟縮著,很害怕的樣子。
「我不是找你麻煩,是希望你幫助我。」張誠好意地安撫海珊:「你不用怕我。」
「是。」海珊輕輕地點頭。
張誠拿出杜有財的照片說:
「你認識他吧?」
鄧海珊看了照片一眼,想了好一會才說:
「我認識他,他叫杜大富。」
「唔——他只是改了名,他是你的『老公』吧?」
鄧海珊想了一想才說:「最近才是——。」
「什麼是『最近才是』?」張誠被她弄得啼笑皆非。
「我們最近兩個月才相好——。」鄧海珊囁嚅地說:「他犯了法?」
「他死了——。」張誠直接了當地說:「你不知道嗎?」
鄧海珊聽了呆了一呆,輕輕搖頭,淚珠從眼眶中湧出來。
「我到這裏就是偵查兇案,讓他尋冤得雪。」張誠說:「可以看看這裏嗎?也許有些線索。」
「不!」鄧海珊突然臉色一變,要阻止他搜索。
「不是你謀殺他吧?」張誠隨即臉色一沉,向臥室走去。
「不!」鄧海珊大聲地叫,不知是否認,還是阻止他入臥室。
她的臥室簡單,壯上是被窩。被窩隆起,張誠隨手把被窩揭開,鄧海珊這時已衝進來。
打開被窩,見到一個差不多裸體,只穿著內褲的瘦小青年。他見到青年,臉色大變。
「你不是阿勇吧?」張誠問。
「是。」青年說,眼睛露出害怕的神色。
「你知道他叫阿勇?」女的歇斯底里地說。
「哼!全在意料中,但想不到這樣容易破案。」張誠說。
大隊人馬不久來到鄧海珊的居所,阿勇和鄧海珊自然被他們扣留了。
六
「你知道我們告你什麼罪?」陳水德嚴肅地對阿勇說。
「通姦?——」阿勇頓一頓說:「其實我們也快要結婚了,為了錢,阿珊只好陪那個香港人,他倆不是真正的夫婦。」
「那個香港人死了,我要告你們謀殺。」陳水德說。
「死了?這樣倒好。你說我害死他嗎?」阿勇說。
「或者買兇吧!」陳水德說,他也不相信眼前的人可以落手殺死杜有財。
「你們有證據嗎?」阿勇說。
「證據在搜集中,但你們有殺他的動機,你從實招來好了。」陳水德說。
「哼!冤獄,我幹嘛要殺他?他不知道我和阿珊仍有來往,每星期都給錢我們,我才不會自斷財路。」阿勇氣憤地說。
「你因妒成仇,殺了他才這樣說這樣的話。」陳水德冷靜地說。
「要殺他,才輪不到我!」阿勇說。
陳水德聽出話裏有因,忙說:
「誰會殺他呢?」
「小東門的司機便想殺他!」
「為什麼?」陳水德追問。
七
阿珊給杜大富搶去,阿勇深深不忿。阿珊溫柔美麗,是他的初戀情人,她十五歲那年已把身子給了他。後來阿珊要到城市賺錢,阿勇知道了也離鄉別井跟著來照顧她。她很感動,更愛阿勇。但杜大富的出現,他便要迴避,使他深深不忿。他見杜大富對阿珊愈好,便愈想他在這個世界上消失。
這晚,杜大富摟著阿珊在食店飲酒消夜,阿勇遠遠跟在後面,想做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藏身在遠遠的地方觀察著。
杜大富擺闊,要了許多東西吃,卻吃不下。要阿珊陪他喝酒。
「我喝夠了,你自己喝吧。」阿珊說。
「不!你要陪我喝,喝醉了最好。你是喝了酒,臉孔紅彤彤的更美麗,我就是喜歡看。」杜大富說。
「不!你不能說人家臉紅好看便逼人家喝酒。」阿珊說。
「這只是啤酒罷了,沒有酒精的。」杜大富說。
「總是酒啊,誰說啤酒沒酒精?」阿珊說。
「吃了這頓飯,我今晚便走了;自己喝有什麼味道?你看,要了一大桌東西送酒。」杜大富有點氣了。
「哼!有錢吃東西也不能逼女人喝酒啊!」鄰座一個人看不過眼,自言自語說。
杜大富瞧來聲望去,見有四個中年漢,是本地人。
「我和我女人的事,誰要旁人來管?你是什麼東西?」杜大富氣著說。
「朋友,你好酒量。敢不敢和我們對喝?」對方一人說。
「好!我不怕你,比什麼?」杜大富說。
「敢和我們鬥酒?也不用傷和氣,誰勝了拍拍屁股便走,由輸的結了這兩檯賬。」
「哈!原來想騙飲騙食!好,就這樣。」杜大富說。鬥輸了極其量多結一檯賬,也沒什麼大不了。
「不要鬥啊,你還要駕車呢!」阿珊說。「不要怕,你知我在香港,一個人飲勝五個人嗎?」杜大富豪氣地說,一心要在愛人面前逞威風。
「這些餸菜我們也可以用來送酒?」對方問。
「你們再要菜也可以,反正最後是你們付鈔。」杜大富說:「夥計,拿十打啤酒來,什麼牌子也可以。」
「十打?」夥計重複一次,恐怕聽錯了。
「是十打,店子沒有便到外面買。」
「是。」夥計說。
這兩檯人成了眾食客的焦點,大家倒愛看熱鬧。
共一百二十瓶啤酒,分成兩堆。對方推出一個穿藍衣的人和杜大富比賽,喝完的啤酒罐放在後面的桌上。不到十分鐘,兩人都喝了十罐,也吃了一些菜下酒,阿珊百般無奈地看著他們。
忽然,藍衣人說:「我要到廁所小便,你也可以小便,喝了許多酒,小便次數不限的。」
「好!有道理!」杜大富說著,又喝了一罐。
藍衣人從廁所出來,連喝三罐。這次杜大富要去廁所了。他們一群人當杜大富到廁所時,分工合作把六罐杜大富的空罐換上啤酒,自己卻要了那些空罐。阿珊見了,著急地說:
「喂!你們怎可以這樣?………。」
「閉咀!你知我們因幫你才這樣——」其中一人說。
「你說出來明天便要你的命。」藍衣人狠狠地說。
阿珊再不敢作聲。杜大富出來,又喝下一罐。阿珊向他暗打眼色,又瞟向空瓶,杜大富終於會意,說:
「喂!好像你們沒有喝得這樣多,你………你攪鬼,咦?我剛才不是喝了十七瓶嗎?」說著霍地站起來。
「老兄,我看你喝醉了,我錯了——。」對方一人說,也站起來。
「我怎會醉?你們耍我,我不怕你們人多!」杜大富說著,叉著腰,伸出食指點著那人鼻子。
那人吐了一下口水,說:「呸!你敢手指指我?」說完,突然張開口,把杜大富的食指狠狠咬著。這一下奇招突出,人人都感到意外。杜大富吃痛,又拔不出手指,情急智生,忙將手上半罐啤酒迎面向那人頭頂拍下。
「拍」的一聲,那人被他打得昏倒,滿身被啤酒濺濕。一人立即扶起朋友,另兩人向杜大富打去。杜大富拼了命,抓著啤酒罐亂拍。對方一時佔不上風,卻聽到店子夥計大叫:
「打架啦!打架啦!叫公安,叫公安。」
那夥人慌了,打個眼色,只有扶著受傷的同伴離去。臨走前說:
「好!你這個香港人,下次見到你便取你狗命!小心了!」
八
杜有財其實真的沒醉,鄧海珊把他扶起,老闆也走到他跟前說:
「老細,你把這裏弄得一團糟,應該怎樣算?」
杜有財向他瞟了一眼,輕蔑地說:「算我倒霉,也算我慷慨,給你們二千元,也只是我一天的工資,什麼也一筆勾消。」
「好!你挺爽快,我也不斤斤計較了。你到另一桌子吃完你的晚飯吧。」
杜有財和鄧海珊重開筵席。他毫不看重二千元,倒像吐氣揚眉,把敵人打跑的樣子,再大嚼一番才離去。鄧海珊始終默不作聲。
杜有財飯後,和鄧海珊擁別,立即駕車回香港。
汽車在高速公路飛馳,天色已入黑。這天終究晚了,杜有財正想著用什麼理由向妻子解釋。突然,他感到膀胱澎脹,又要小便了。在路上那有廁所?又心急回家,只有忍著、忍著。
愈不想小便,愈感到要小便。忽然,杜有財還感到肚痛,要拉肚子。也只有忍著、忍著。
終於他計算一下,還有一小時到邊關才有廁所,此可忍,孰不可忍也,終於他決定下車小便。
高速公路這時幸好汽車不多,大便、小便最多不過三五分鐘。杜有財小心翼翼下車。望見沒有車,公然小便起來。
「噓——真舒服!」杜有財說。
在高速公路公然小便,令杜有財身心暢快,又有些自豪,有多少人可以這樣呢?
哇!不好了,又拉肚子,索性在公路大起便來。這更有趣,更足以向朋友炫耀……。

九
陳水德聽了阿勇的故事,不用一天功夫,便把小東門有關人等全部抓來。他們都承認事實,但否認殺杜有財。
「好!待我們再找到其他證據,證明不是你們幹的,我們會放你」麒麟鎮的公安說。
「我們怎會在公路上截殺那香港人呢?」藍衣人悲憤地說。
「啊!他死在公路旁嗎?」一個像他們的首領的人問。
「是!」陳水德木無表情地說。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你不要說由我說出來的,可以嗎?」
「你先說說。」張誠說。
「好!我的表侄林小寶也是司機,兩天前打電話給我,他六神無主,說在公路撞死了人,他說超速駕駛。當時天色黑,突然撞倒一個物體,聽到有人大聲號叫,那物體被拋到高速高駕橋下,他感到不祥,又不敢報案,只打電話和我說。」
「——」眾人聽了都是一呆。
「就是這樣?———。」張誠問。
「好!立即把小寶抓來。」陳水德說。
十
「哈哈!這離奇的『艷屍』案總算破了。」張誠臉有得色。
「唔——你知道嗎?整個案情,每一個細節,你們都完全推斷錯了!」陳水德嚴肅地說,像潑下一盤冷水。「這個——」張誠覺得隊長說得對,無從反駁,可是又不甘心小心翼翼:「與桃色有關總沒錯吧?」
「張誠,你不用灰心,你聽過人家說:一切真理,都建立在繆誤之中嗎?」隊長輕鬆地笑著。
「這個——是、是,但把我弄得糊塗了。」張誠也輕鬆地笑起來。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柳岸簡介:原名楊興安。以筆名柳岸發表小說。多年來從事文教工作。著有《金庸小說與文學》,散文《浪蕩散文》、舞台劇《最佳禮物》,及由香港作家協會出版之小說《柳岸傳情》等著述。現為香港小說學會名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