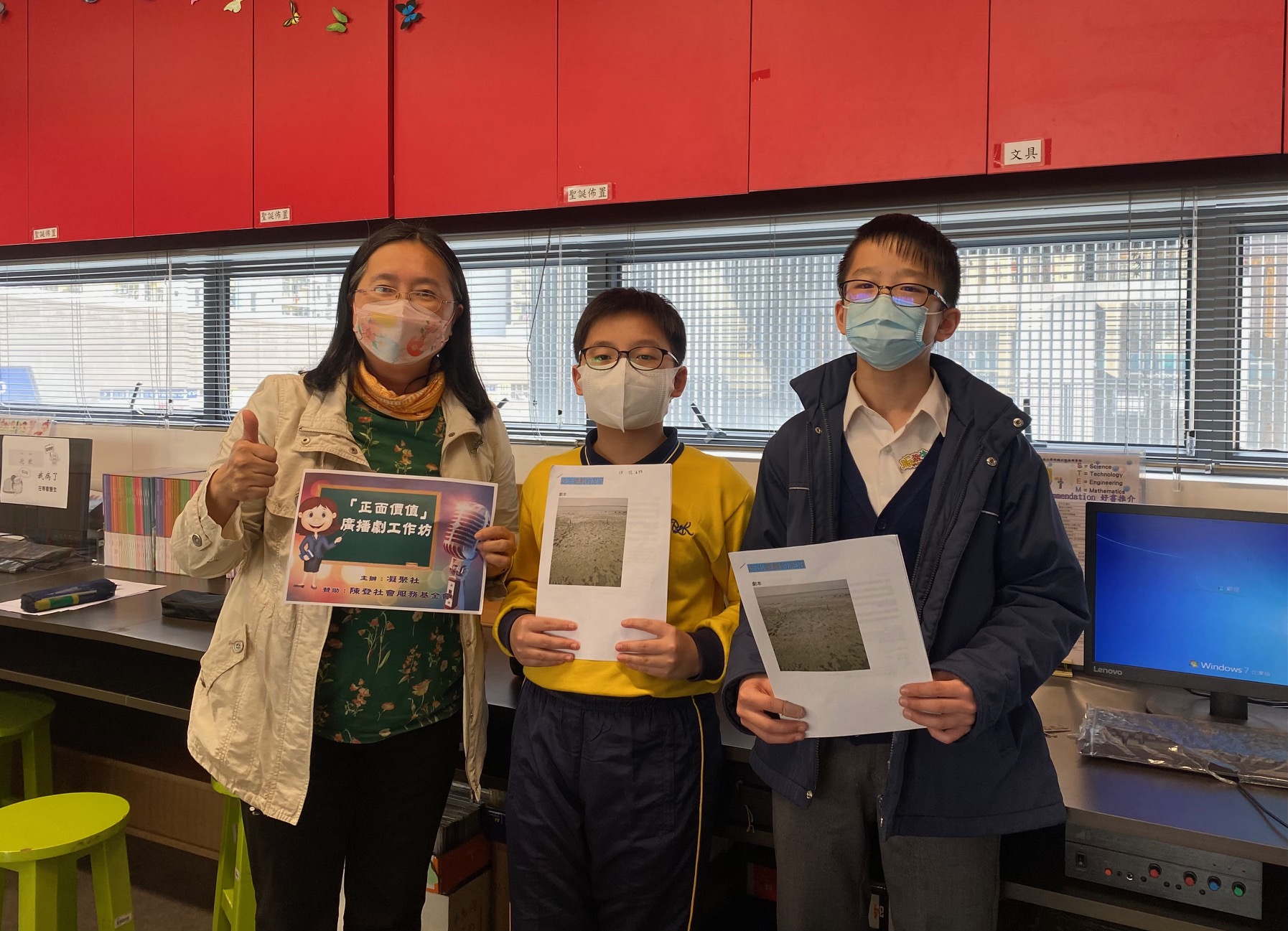董安

在東北,村子一般也被稱為屯。松江屯,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坐落在松江畔的小村子。雖然是小村子,可是一點兒也不冷清,因為從大山裏面開採出來的木材、煤炭、礦石等等資源,一定要用松江水路源源不斷地運出去,而松江屯作為松江最大的渡口,想冷清都冷清不下來。要是到了冬天,幾場雪過後江面就凍得結結實實的,跑馬、拉車都不在話下,松江屯就更熱鬧了。慢慢地,在松江屯就出現了集市,每個月初一一次、十五一次,十里八鄉的老百姓們從四面八方趕過來,有的人為了趕這個集,甚至要走上百八十里地呢。
栓子剛學會走路的時候,就開始跟著家裏的大人們去趕集。栓子最喜歡收穫的季節,從長夏到初秋,爺爺推著車去集上賣剛打下來的莊稼,栓子就可以坐在推車上,背靠著高高的苞米堆,讓爺爺一口氣推到集上去。莊稼賣出去了就有閒錢了,有閒錢就可以再買些需要的東西回家,不買東西其實也不打緊,到處逛逛也挺有意思的。在栓子眼中,集上的一切是那麼的吸引人:活蹦亂跳的鯉魚、泥鰍和鯽瓜子;香噴噴的糖炒栗子、烤地瓜;吹糖人或者捏麵人的少見,價錢也貴,不過就算買不起看看也是好的,反正買了也捨不得吃;至於土豆、蘿蔔、白菜、茄子、豆角、柿子之類的蔬菜,雖然是在家裏的園子中見慣了的,但到了集上,卻也顯得格外新鮮。
後來,集上出現了朝鮮人,操著生硬的口音叫賣著自家醃製的辣白菜;再後來,集上又出現了賣藝的白俄女人,她們穿著花花綠綠的「布拉吉」,跳起舞來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栓子第一次見識了男人可以比女人還瘦,第一次知道了女人可以長得比男人還高。不光是栓子,整個松江屯的目光都被這些來自異域的新奇玩意兒吸引了。夏天的時候在朝鮮人那兒買上一碗冷麵,蹲在道邊兒一邊吃一邊看白俄娘們兒跳舞,舒服的很吶!

終於,日本人也來了,隨著日本人一起來的還有「嗚嗚」叫的火車,在松江對岸吭哧吭哧地緩慢爬著,不時冒出白的或者黑的煙。栓子聽娘說,江對面的鐵路就是大伯和爹去修的,於是栓子每次去趕集,都會隔著江遠遠地望著火車,好像能看見爹站在火車頭上威風凜凜的樣子。然而除了受驚而四散的野兔子、傻狍子還有麻雀,其他的什麼也看不到。時間久了,等松江屯都變成了「滿洲國」的土地,也不見他們回來,栓子就再也不去看火車了。不知道為什麼,栓子總覺得火車出現以後松江屯的集也沒有那麼熱鬧了。
不過日本人也能給集市帶來一些新鮮東西,像「拉洋片」啊、「西洋鏡」啊,這些都是栓子喜歡的,有時候運氣好,還能趕上日本人放西洋電影呢。放西洋電影的陣仗可大了,和過年的時候搭台子唱戲有一比。在一片空地上用黑布圍起來,給日本人五塊銀元便能放進去看上十分鐘。栓子沒錢,只能爬到旁邊的柳樹上,伸著脖子往黑布裏面瞅,其實也看不大真切,只能看到黑白灰色的小人晃來晃去。要是被日本人發現了就慘了,他們會撿起地上的轉頭瓦塊往樹上扔。栓子手腳麻利,只需要抓著柳樹枝那麼一蕩,就在「八嘎呀路」的叫罵聲中跑遠了。
松江兩岸的日本人其實不多,一個縣城裏只有那麼三五個戴鋼盔的日本兵,其他日本僑民要麼是軍人家屬,要麼是滿洲開拓團團員,「皇民」們雖然平時耀武揚威的,但作為滿洲國的「一等公民」,一般也不屑於參與中國人的集市的。「抗聯」鬧起來後,日本人更不敢隨便在中國人扎堆兒的地方出沒了。栓子也就沒機會看到日本人才有的西洋電影了。
可有一段時間,集上出現了一個怪人。基本上每次趕集,這個怪人都會到場。他一身黑色西裝,手上拎著根文明棍,嘴唇上還留著一撮小黑鬍子,走起路來一步三搖的,可有有派頭兒了。他不賣東西,也不見買東西,就是閒逛,東瞅瞅西看看左瞧瞧右望望,哪裏人多他往哪鑽。人們都好奇,三三兩兩地嘀咕著。
「喂,這人什麼來頭兒啊?」
「誰知道呢?」
「看這身打扮,肯定是外國人,看他個頭挺高、鼻子也挺大的,別是俄國人吧?」
「扯淡!你見過黑眼珠的俄國人?要我說,八成是日本人!」
「你才扯淡!哪有那麼高個子的日本人啊?」
「不是東洋人,也不是西洋人,那就是朝鮮人了。」
「放屁!朝鮮人都窮得摳摳搜搜的,穿的還不如我呢,哪能穿這麼一身衣裳。」
也許是聽著了周圍人的議論,也許是因為周圍幾步之內都沒有人而感覺到了異樣,那個怪人轉過頭來,眼睛一瞪,冒出一句「八嘎!」
是日本人!人群「哄」得一聲作鳥獸散。那時候有幾個老百姓敢惹日本人,見著普通日本僑民都繞著道走,更何況是他這趾高氣揚的樣子。
可是躲著歸躲著,交頭接耳地議論可沒停下來。
「這人誰啊?這麼神氣!」
「你管呢,人家是大和皇民,說不定還是什麼大官大商人啥的呢。」
「咱哥幾個兒都別惹事兒,該幹嘛幹嘛去吧。」
那個日本人又來了一句「八嘎」,人群這回倒是安靜下來了。
他倒是不擾民,只不過是偶爾順手拿走一棵白菜兩根黃瓜啥的。損失倒是不大,人們也敢怒不敢言。有一次,栓子眼見著他拿著自己家的兩捆韭菜,頭也不回地走了。栓子張嘴剛想喊,被爺爺一把攔住了。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爺爺搖搖頭,無奈地說。
栓子沒辦法,只好作罷,要不然他真想撲上去狠狠地教訓他一頓。要是能扒下他這身皮穿在自己身上就好了,這樣自己也能在其他中國人面前耀武揚威一次了,栓子這麼想著。
有道是花無百日開,這個日本人在松江屯的集上閒逛了大概一百天後,終於出事兒了。
那是一個剛下過雪的午後,天還陰沉沉的,那個日本人又來趕集了。周圍人都穿上了大棉襖,富裕點的還帶著狗皮帽子,可他還穿著那一身的西裝。雖然比往常多戴了一頂禮帽,但顯然無法抵禦刺骨的寒風。他凍得哆哆嗦嗦的,站在他邊上好像都能聽見他牙齒亂碰亂撞的聲音,趕集的人們看著他滑稽的樣子憋不住的樂。
最終,他自己也受不了了,跑到糖炒栗子的攤上,借人家的爐子取暖。周圍的人們都不敢湊過來,賣糖炒栗子的老頭兒也不好說什麼,只能瞅著他乾瞪眼。
那天這個日本人還戴了一副金邊眼鏡,也許是被爐子的熱氣蒙住了雙眼,也許是太冷了想靠爐子近一點,只聽得「哎喲」一聲尖叫。
日本人被爐子燙了!

這還得了,周圍人群鴉雀無聲。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那個日本人也惱羞成怒,咯吱窩下夾著文明棍,站起身來,罵了一句「八嘎」,踢了爐子一腳,火花四濺。
「哼!」賣糖炒栗的老頭兒也不敢造次,順口哼了一聲。
「八嘎!」日本人又踢了幾腳,罵了一句,轉身走了。
「小鬼子,神氣什麼!」等日本人走遠了幾步,老頭兒又嘟囔了一句。
「八嘎呀路!」這日本人耳朵真好使,被他聽見了這句嘟囔。他轉過頭來,文明棍一下子杵在了老頭兒的胸口。老頭悶哼一聲,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不敢再言語了。他見老頭兒不吭聲了,又罵了一句「八嘎呀路」。
很多日本人罵完「八嘎呀路」後都會接著罵一句中國話「滾蛋!」這樣就算是聽不懂日語的中國人,聽到這句也該知道「滾」了。
然而那個日本人,停頓了兩秒之後,惡狠狠地補了一句:「滾犢子!」
這一句標準的苞米碴子味的東北話,哪裏是一個日本人的口音能說得出來的?他分明就是一個東北人啊!老頭兒一愣神,立馬就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兒了,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操,狗卵子在這冒充日本人!」

任何的解釋都是多餘的,都是蒼白無力的,都是徒勞無用的,再多的「八嘎呀路」也不好使了,因為他「滾犢子」了。他被集上所有憤怒的人群圍住了,一頓胖揍,文明棍被打折了,眼鏡也打碎了,禮帽也被打丟了,一身西裝更是破爛不堪沾滿了泥和雪的混合物。
「你姓啥?」
「姓張。」
「哪兒的人?」
「就是這兒的人。」
「家在哪?」
「江對面兒,過了江就是我的家。」
「這身行頭打哪兒來的?」
「攢了點錢,在哈爾濱買的。」
「為啥好好中國人不做,咋尋思出的主意,擱這兒裝日本人?」
「去年在奉天見過幾個日本人,看見他們這麼穿的,覺得……」
在人群一陣陣「滾犢子」的叫罵聲中,這位張先生一瘸一拐得走在江面上,灰溜溜的回去了。後來再也沒人見過他,起初還能作為茶餘飯後的笑料,時間久了在松江屯也就沒人記得他了。
可栓子卻一直記得他,對這個來自松江對岸的,穿著一身西裝、手持文明棍、戴著金絲眼鏡還頂著禮帽的形象印象深刻。後來,每到冬天東江冰封的時候,栓子都想就從江面上走過去,去東江對岸看一看。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董安簡介:一九九七年生於黑龍江,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文學士,香港科技大學中國文化文學碩士,現為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孔子學院研究助理。十六歲開始小說創作,曾獲青年文學獎、大學文學獎等獎項,作品散見陸港兩地文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