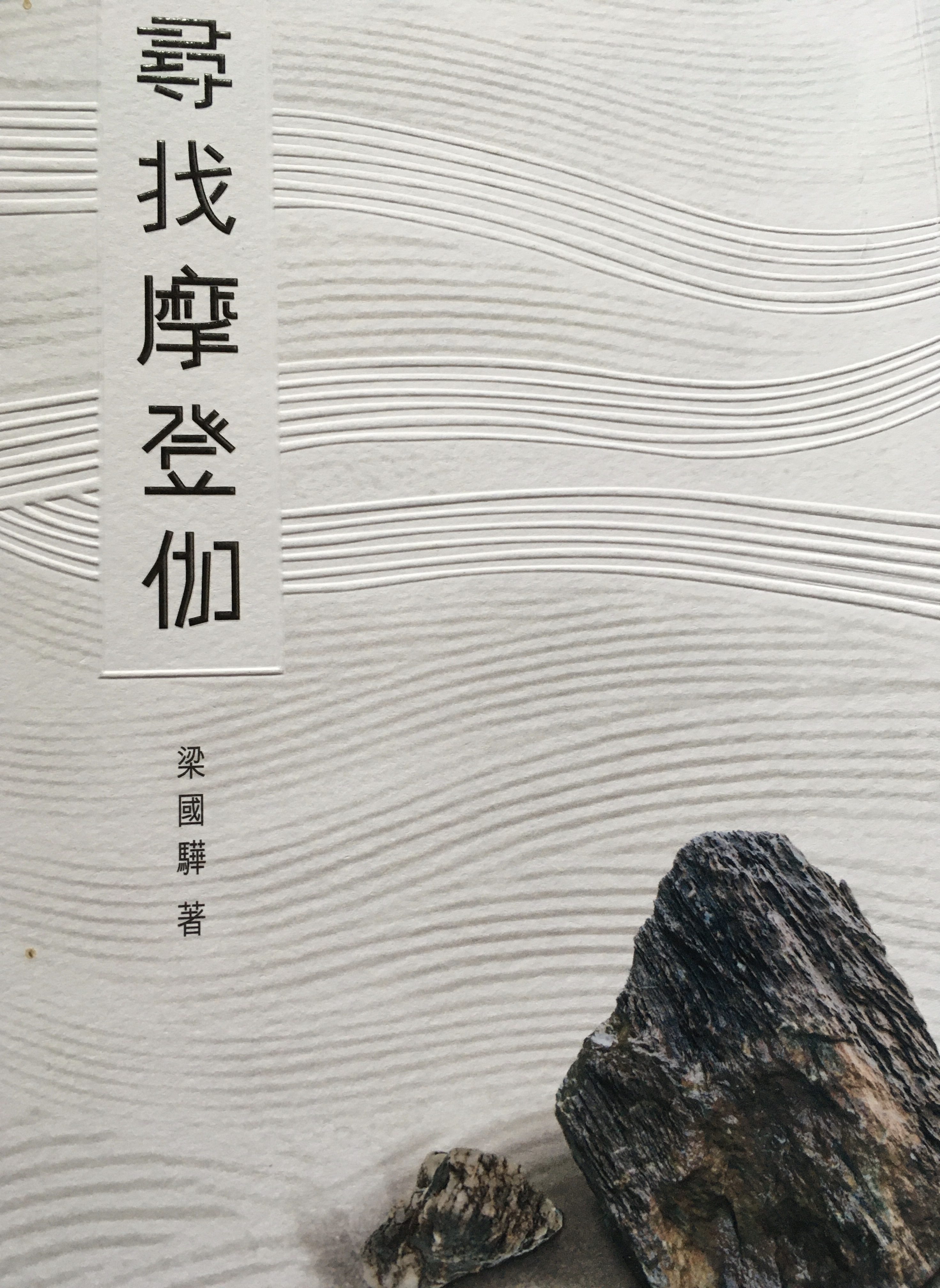陳慧雯

在曼徹斯特工作多年的兒子阿誠傳來婚訊,此次他專程回香港,邀請我過去參加婚禮。我們約在彼岸咖啡屋見。我照例七點到咖啡屋用餐,我是這家多年的老主顧。咖啡屋呈橢圓型,空間闊大,外圍是一圈名貴花木的花圃,幽香清絕。這裏環境浮華考究,裝潢奢華,充溢著濃郁的北美情調,室內常年瀰漫著深度烘焙的咖啡豆香,最牽動我的是,坐在窗口位可以望向碼頭,那兒稀稀落落地坐著幾個人在垂釣。或許那其中仍坐著我的琳達,我愛作此幻想。
「琳達,咱們的兒子終於要結婚了!」我由公事包掏出一個蛋型電子寵物機,低喃地對亡妻叨唸著。我比琳達大十幾歲,她十七歲已經跟了我,離開我至今已整整十五年。撫今追昔,我感慨萬端,多少前塵往事依然歷歷在目。我閉上眼睛,任憑思緒把我帶回那個年代。
二〇〇七年,公司處於創業階段,我經常開會加班忙得團團轉,阿誠在英國讀書,琳達總是投訴我沒時間陪她,顯得悶悶不樂。為了多陪伴嬌妻,我中午與她在公司共進午餐,之後,我繼續埋頭苦幹,琳達則會蜿蜒穿過街頭集市,獨自去附近的公園溜達。
那時,為了解悶,琳達開始飼養電子寵物,達到了機不離身的地步。因為飼養電子寵物,琳達還結交了一位閨蜜——碧翠絲,這同樣是溫柔曼妙的女子。我只見過她一面,是琳達帶她到我辦公室的。她們都三十出頭,身形相若,一樣的身高一樣的苗條,都有水蛇腰、細長四肢,都喜歡穿粉色及膝的連衣裙,同樣的秀髮披肩。我那時打趣說她們也許是失散的姊妹。這話充滿調侃意味,因為她們的臉區別甚大。琳達長著水靈靈的圓眼,直挺的古希臘雕像式的鼻樑,櫻桃朱脣,下巴內縮。而碧翠絲則不然,她眼睛細長,鼻子小巧稍顯扁塌,嘴脣單薄,額頭靠近髮際線處有一角硬幣大的凹陷疤痕。
琳達收藏了十二款不同時期的寵物機,每部外殼都用保鮮膜包裹著,如珍似寶地擺放在古董架上。她走後我不斷自我反省,思情無可排遣之際,我嘗試將它們裝上電池,親身體驗愛妻養電子寵物的樂趣。兒子阿誠於殯葬期間回港,始終緘默無言,回英國時他帶走了其中兩款,看得出,噩耗雷電般猝然而至差點擊垮了他。光陰飛逝,十多年彈指即過,我如今也對這些電子寵物關愛有加,它們寄託著我對亡妻的無限哀思。
記得在琳達溺水身亡後的那幾個月,我終日以淚洗面。她離開的第一個生日,我在公司樓下餐廳點了一份二人套餐,開了一支香檳,我與珠珠(妻子以前最寵愛的電子寵物)為假想中的她慶祝。為了進一步探索愛妻生前的活動軌跡,我挪著醉步踅出餐廳,捏著珠珠往公園走去。
這個公園地處車水馬龍的繁華鬧區中心,綠樹成蔭,芳草如氈,堪稱都市之綠洲,我之前居然從未陪愛妻來過。我邊走邊觀賞著種類繁多的樹木:烏口樹、黃槿、大葉合歡、牙香樹等,雀鳥聲此起彼伏,真是個散步的好去處。接下來的一幕讓我終身難忘,在觀景臺旁,我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紫羅蘭連衣裙隨風輕曳,腰間裙帶飄起——正是琳達素日最青睞的那條裙子,殘陽之光將她的麗影倒映在細碎的鵝卵石小徑上。不,我渾身打擺子似的顫抖起來:琳達!我的小寶貝兒啊!我赫然呆住了,酒也醒了!隨著她的身影緩緩轉來,我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呆若泥塑木雕!這不是琳達又是何人!「琳達!琳達!」我喉嚨發澀,生怕這一切會消失如夢幻泡影,用盡全力嘶啞地喊出!她驚疑地望向我,慌亂地抓起石凳上的手提包想跑,但是我上前一把拽住她的右手腕,雙膝抖顫幾乎要跪倒:「我的妻!小寶貝兒!琳達不要跑!」她鎮靜下來,不再試圖逃走,只是靜靜地說:「您認錯人了,先生。」這聲音似曾聽過,確實不是琳達的,可是我一時記不起。我的目光近距離貪婪地舔著這張熟悉的臉龐:圓眼直鼻,櫻桃小嘴,只是額頭添了一塊陳舊的疤痕。這世上,琳達真有雙胞胎姊妹麼?我的腦子一團漿糊,混沌一片。她終於在我鬆手的一霎那掙脱,倉皇逃離時,她掉了東西又附身拾起,是一個電子寵物機!

陰風冷冷地吹襲著我,送來各種草葉與泥土發酵的氣味,我同時還聞到濃烈的咬破自己舌尖的血腥味。我一陣暈眩緊閉雙眼,踉蹌了幾步下蹲,待我重新睜眼,四周異常冥謐,剛才發生的事情如同被風吹到現實的一團薄霧,像夢境般那麼失真。這個謎團困擾著我,使我失去了之後的安眠。直到三個月後,香港刑偵組的探員打給我,說琳達的遇溺不是意外,可能另有隱情——這才陸續驅散迷霧。原來,公園裏的那個女人便是碧翠絲,她與琳達搞在一起,被她的同居男友崔先生得知內情。這個妒火中燒的男子遷怒於琳達,在琳達夜間釣魚時推她落海,行兇過程被旅客無意中攝錄並揭發了出來。真相大白!我頹唐地將自己關在屋子,三天三夜不吃不眠。我接受不了最親愛的妻子原來一早已背叛了我。
二〇〇八年,初審判處被告終身監禁,上訴高院上訴庭獲判發還重審。二度初審維持原判,被告人再度上訴終審法院勝訴。二〇一四年,第三次審訊仍然維持謀殺罪有罪和終身監禁判決,之後,被告認罪沒有再上訴。
我最後一次見到碧翠絲是在法庭上,看著她仿若看到嬌妻重生,把我的心戳得鮮血淋漓。雖然妻子對我不忠,但我最終還是原諒了她,我不知道該如何看待她們之間的感情,這個女人為了所愛之人,大刀闊斧地整容,下輩子都以愛人的容貌生存於世。我很想衝上前斥責她,或者摔她一巴掌解氣,但是我什麼都沒做,渾身冰冷僵硬。
當我走出法庭大樓,看到對面街有同志會的成員拉起了寫著「一樣愛,勿歧視」的橫幅,歇斯底里地叫囂著口號,三五個警員正一邊說著對講機,一邊朝他們走去。我內心的悲涼無可名狀,雙腿乏力,眼前發黑,一個倒栽葱栽倒在街邊。等我甦醒後,我便深陷無邊的哀傷之境……
「戴先生,您的寵物餓了在叫您呢!」女侍應柔聲提醒我,將我由回憶喚回現實。我低頭一看,珠珠正噘著嘴對著屏幕吱吱呢,它的聲音嬌滴滴的,令人憐惜。
我邊吃天使蛋糕邊餵珠珠吃漢堡、喝珍珠奶茶,這麼多年來,由於我工作太忙經常將機器調成靜音,它無數次孤獨地死去、無數次升天,我亦固執地讓它重新復活了無數次。沒有親人相伴,我只與它一起吃晚餐。這家咖啡屋主要做寫字樓生意,中午門庭若市,晚上卻極缺人氣,四周的氛圍過於詭異,讓我恍惚間誤以為琳達又回到了我身邊,我幾乎可以感受到她在耳畔的呼吸,聽到她在喃喃央求:「老公,陪陪我!陪陪我!」

沉重的玻璃門被推開,高大的身軀挾著一陣風而來,是阿誠。他剛毅的身形線條是長期跑步鍛煉的結果。
「爹哋,我這次回來,也想問清楚媽咪當年溺水的情況。」 阿誠果然成熟了不少單刀直入。
「當時為了不影響你的情緒,我隱瞞了整個事件。你應該有所耳聞——你媽咪、她是被人故意推下海的。」說出這樣的事實對我們父子無疑是二次傷害。
「這人是誰,為什麼要這樣做?」阿誠的拳頭握緊了。
「我那時太忙,忽略了關心你媽咪。你媽咪背著我與碧翠絲阿姨走到了一起,碧翠絲的男友知道了真相懷恨在心,跟蹤你媽咪把她推下海,他自以為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卻被一位遊客無意間拍了錄像報了警。」
我取出泛黃的報紙,指出一小塊當時的新聞報道。阿誠認真地讀著,半個巴掌不到的新聞,他看了足有十分鐘。他展現出異常包容之態,甚至可以說不動聲色地放下報紙:「知道了爹哋,您要好好的,我只有您一位親人了!孩兒不孝,不能好好照顧您!」動情的話語讓我內心的堅冰世界轟然崩塌,我竭力咬著舌尖,強忍住在公眾場合痛哭的衝動,口腔瞬間充滿了血腥味,我抿緊了雙脣。他的眼光投射在寵物機上,忽然話鋒一轉,故作輕鬆道:「已經出了很多新版本了,您還玩最老舊的這款!我把媽咪的那兩款還給您!」他變魔術般攤開厚實的大手板,兩款寵物機躍然掌上,它們都穿著粉色毛線衫,甚是呆萌憨拙。「這些毛線衫是我織的。」他戲謔地抽動嘴角,我聽出了抑制不住的顫音。我依然坐著沒動,像被使了定身術。
他眼神閃動,錯開了與我的對視,似乎飄向遙遠的深處,喘了口粗氣,他繼續提高聲量講說,那模樣似乎置身傳銷現場:「我飼養著最新一代的寵物叫伴伴,在我的婚禮,所有嘉賓都將帶寵物機來一起聯網,我要為伴伴尋覓它心儀的伴侶,哪怕這個伴侶在天涯海角——這將是婚禮的重要環節!」他大手從挎包抽出一張信封,鄭重其事地放在雕花圓木桌上,手掌按在其上數秒又移開。咖啡屋憂傷的音樂在他臉龐流動,似乎將憂傷流進他體內的每根血管,又從他體內流回桌面,流至我的手與腳,流至我的五臟六腑。
我機械性地點了點頭。他臨走前瞥了我一眼,眼神就像他母親一樣幽怨,讓我打了個寒噤。暮靄從四面八方湧來,偌大的咖啡屋只有我一個顧客,我覺得自己就像閉鎖在寵物機裏的寵物,正向外窺視著主人。玻璃窗外,阿誠留給我一個挺直的背脊,隨他一同行走的同樣是挺直背脊的青年人,落拓不羈,他們肩並肩走遠,暮色吞噬了他們。
我亦挺直腰板,端起冷卻了的咖啡,就著泛滿口腔的血沫,一小口一小口地吞嚥著,如同一位帝王在品嚐瓊漿玉液。接著,我餵珠珠喝咖啡,今晚它注定陪我失眠。我的手繼續開啟信封,裏面有一張飛往曼徹斯特的機票。結婚請柬上燙金的字寫著:「婚禮邀請函:心之所向,素履以往。邀請您與您的電子寵物見證戴誠先生與宋河先生的婚禮。」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陳慧雯簡介: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文化發展研究會會長,香港文化藝術界聯會副理事長,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長,《香江文藝》雜誌編委,香港小說學會理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