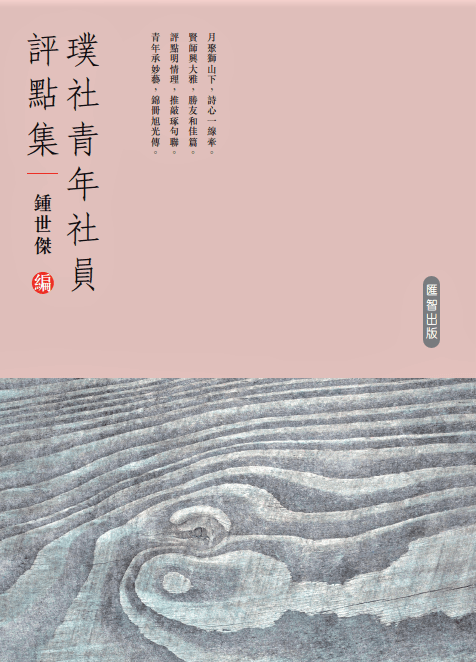林祁

櫻花開了,春天還在徘徊。(資料圖片)
櫻花開了,春天還在徘徊——彌生從海的那邊發來微詩,邀我同赴華文女作家協會的徵文。說「赴」,因為是「徵文」,以櫻花徵繳疫情。這場疫情不諦於一場世界大戰,看不見烽煙滾滾卻聞得到死亡的氣息。原以為能夠主宰宇宙呼天喚地的人類,碰到大麻煩了。區區櫻花何以抗爭?
今日上野依然有人戴著口罩去「花見」(日語賞櫻的意思),網波傳來他們平靜的微笑。隔空擁抱,寫一篇〈櫻花力〉吧。不過似有模仿《漢字力》之嫌。那麼以〈憤怒的櫻花〉應徵吧,這些日子有太多的疫情讓人操心,也有比災疫更為可怕的「頭腦發昏」令人憤怒。憤怒出詩人。詩餘落筆卻成了〈櫻花祭〉。「祭」在中文裏是祭祀的意思,日語則賦予它節日的熱鬧。我以為,「祭」便是中日櫻魂的關鍵字——哈,還是漢字力!
其實,還在一個月之前,未「徵」我已「文」。那天從東京返廈,我辭去所有的送別宴會,寂寥間於上野看到了第一樹櫻花——
從口罩抬起目光
驚艷今年第一樹櫻花
不聲不響就把春天騙來了
我可不敢對你抒情
上野,在你這裏
所有的物哀都開出花
沙揚娜拉,上野
我是有故鄉的人
手機拍的花比真的還美
我懂日式燈盞閃爍的漢字
山川異域 風月同天
不懂我為什麼在這裏
天飄著冷雨
櫻花都凍紅了
白口罩會變成雪花嗎
吟罷詩並未見雪飄,倒真希望有雪變口罩!昨晚廈大學友找我商議往日本快遞口罩,以回報當初日本捐贈口罩之舉。是呀,一個月之前,我還在東京街頭排隊,到處「搶」口罩往中國寄呢!一時洛陽紙貴。口罩雖輕,情義深重。這場災疫倒是激活了中日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如果說「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漢文有可能出自華人之口,而題在捐贈物資上並閃亮東京街頭的標語,無疑出自日人之手了。那「手」自古以來就善取中國貨,變為他家寶的,早就見怪不怪了。這不,舉世聞名的東方之美日本櫻花,不也是從中國移植來的嗎?
故,「知日」大家李長聲如此解說:「日本人本來是學中華尚梅花,後來崇尚武士道變成櫻花,看到櫻花落下,人人慨然生出赴死之心,如果還是喜歡梅花,恐怕大家只想隱居好好活下去了吧……」花道直通武士道,好一個「理解萬歲」。
他又說:「櫻花像潑婦,嘩地花了,又嘩地落了。」虧他想得出,櫻花像潑婦?我看日本人是絕對想不出來的,最多只會想到「淫婦」、「蕩婦」嘩嘩而已。雖然長聲兄的比喻鞭及女性,我卻要為他點讚,佩服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豪爽。
記得三十年前,我第一次被櫻花「嘩嘩」吵醒時,亦曾作詩,得以地從廢墟中搬來大詞「轟轟烈烈」以形容花開,有日本女詩人驚訝這種用語方式,曖昧地表示:喜歡用擬聲字並年年「花見」的日本人,卻是絕對想不出這種詞的。這回輪到我吃驚了,且把讚嘆當作批評,畢竟我是從那種語境來的,我終究逃不出那種大語境——
聽花在天地間喧鬧
我在一夜之間
喪失語言
但,櫻花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語言呢?
寫櫻花最為有名的當是留日前輩魯迅,他輕輕起筆:「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這段描寫引自上了中學課本的〈藤野先生〉,自然給「少年中國」留下了幾多憧憬。而後旅遊者每每引用,卻有意無意地忘卻下文:「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魯迅平時慣常拿辮子盤頭取笑,以至被取綽號「富士山」,想來其間頗有深意。辮子盤頭固然形似「富士山」,但「富士山」壓頂寓意著什麼?這才叫「百分之百的痛」!史載,中日甲午戰爭於一八九四年爆發,中國戰敗後深受刺痛,向東鄰日本學習蔚然成風。魯迅身在其中。從一張東京浙江同鄉會的老照片中(註),可以看出他當時還留有辮子,蓋在學生制服帽子底下。不知他寫〈阿Q正傳〉時是否還留著辮子?周作人曾解釋Q字就像是一個無特點的臉後面加一根小辮子,恰是魯迅用Q命名的用意。

一九○二年,魯迅與浙江同鄉會於東京合影。這張照片拍攝於「斷髮照」前,當時應該還留有辮子,蓋在學生制服帽子底下。(資料圖片)
今日看花者必定不留Q辮,但面對疫情來點「精神勝利法」卻不少見,甚至以繩子當辮子「將脖子扭幾扭」。日前,我給大學生們上網課講魯迅,就三不五時摸摸脖子,生怕被辮子纏上,反正釘釘視頻可以不露臉。還暗自慶幸,不被圍城封城,不用寫「萬箭穿心」的日記。嗚呼,這算不算阿Q國民性?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耶路撒冷文學獎」(二○○九年)時,發表了經典演講:「無論高牆多麼正確和雞蛋多麼錯誤,我也還是站在雞蛋一邊。正確不正確是由別人決定的,或是由時間和歷史決定的……我寫作的理由,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讓個人靈魂的尊嚴浮現出來,再將光線投在上面。經常投以光線,敲響警鐘,以免我們的靈魂被體制糾纏和貶損……」疫情尚未結束,作家何為?奧斯威辛之後,詩人何為?信手拈來的警句,卻是日本作家的。但,真正的作家是超越國界的,就像櫻花,中日的櫻花都開了。雖然櫻的花期很短,但從南九州的第一朵到北海道的最後一朵,要開上三個月,足足一個春天呢。
終於,我們聽到武大櫻花的聲音了——
三月的櫻花大道從未如此寂靜
想念畢業於此的李醫生
數字會清零,記憶不會
櫻花縱使瘋狂,卻是安靜的。總有一些事物不期然地喚醒我們的記憶。曾幾何時,我們在樹下讓櫻花飄進啤酒,再啜一口,爽!喊爽的北京作家,櫻花瓣在捲舌音裏顫出另樣的美。而今各「宅」一方,相忘於江湖;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人生若只如初見」,悲的是「故人心易變」,還只是悲人,而今「悲人」已變為「悲天」了。比天大的悲,何以詩文嘆之?
小引在網上紀念詩友時說,我們未曾謀面,一生只說過一句話:「春天好!」

我們聽到武大櫻花的聲音了。(資料圖片)
春天好就好在我們有櫻花。從第一樹到鋪天蓋地,櫻花總是爛漫得無拘無束,粉紅得如癡如醉,櫻花才不怕疫情呢。哪怕幸存最後的看花人,櫻花依然故我,開得自如,活得瀟灑。
「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要記得擦唇而過的櫻花,記得陪你看花的男人女人,恰是這些人組成你生命中溫暖的記憶,滋長出對抗病毒的免疫力,從而成為一個勇敢善良正直的人。也許當你和方方日記一起歷經「封城」之後,你重讀武大的櫻花已然不同於從前,你觀看上野的櫻花已不同於魯迅。當天空與櫻花一起醒來,你將與倖存者一起「向死而生」,靠光線,靠文字,或者靠一瓣溫暖的聲音……
註:一九○二年秋,浙江籍官費、自費留學生及在日本遊歷或僑居的浙籍人士一百零一人在東京組織浙江同鄉會。會上決定出版月刊雜誌《浙江潮》。魯迅加入了同鄉會。這張照片拍攝於「斷髮照」前,當時應該還留有辮子,蓋在學生制服帽子底下。
林祁簡介:
日本華僑。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日本華文女作家協會理事、日本華文筆會副會長。來往於中日之間,現為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教授、暨南大學兼職教授。
出版詩集:《唇邊》、《情結》、《裸詩》;散文:《心靈的回聲》、《歸來的陌生人》、《彷徨日本》、《踏過櫻花》、《莫名祁妙──林祁詩文集》,及《紀實長篇:莎莎物語》(獲日本新風舍非虛構文學獎第一名);論著:《風骨與物哀:二十世紀中日女性敘述比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