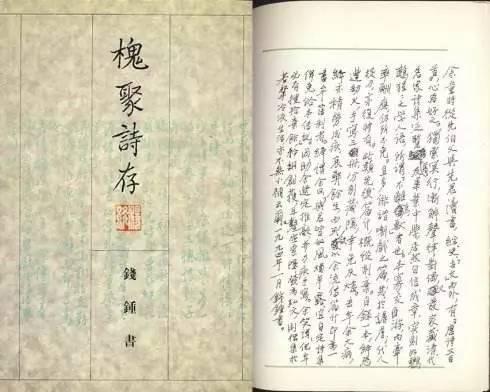白舒榮
元月三日,正準備電話問候曾老總,卻傳來他去世的消息。年前曾看到他在醫院奄奄歲晚的病狀,也見到他從醫院回家後的煥發,本想或許能參加他的百年壽誕,但病魔終究無情。沉痛悲傷之際,也慶幸不久前還曾直面聆聽過他對心心念念的世界華文文學事業的關切指導。
二○一四年三月初,我奔暨南大學參加即將於當年年底在廣州舉辦的「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籌備會,行前給曾老總電話,他說雙腿疼痛難行動。我決定到廣州後,利用會餘時間去他家拜訪看望。
認識曾敏之先生的時候,他是香港一家大報的老總,所以延續至今無論他的職務如何變化,我始終稱他為曾老總。出於慣性,也為親切。

到廣州當晚,聽王列耀教授說,曾老總要親自出席參加會議。果然,第二天上午,乘坐輪椅,杖策雙拐,神采奕奕的曾老總出現在文學院會議室。
看到曾老總由眾人攙扶起坐的艱難狀况,我很想對他說:「何必道路顛簸、親自出動,聽聽彙報,隨時可作具體指導啊。」
商討着「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籌備事宜,面對坐中的曾老總,我的思緒悠然游走進了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發展歷史。
中國世界華文文學發展道上的鬥士
回憶這段歷史,首先想到的便是曾老總。作為這個研究領域的創始者、指引者,始終不渝的參與者,無論壯年體健,還是暮年多病、或遭遇親人不幸的重創,他始終以頑強超人的毅力,傾注對世界華文文學事業不渝的深厚感情,站在一線指導前沿。
我和曾老總結緣於八十年代初,無論我在《當代》、還是主持《四海》雜誌,曾老總都曾對我的工作給予過巨大幫助。
另有有幾件事,也深刻留在我的腦海裏。
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夕,他和時任香港作家出版社社長的詩人犁青先生親自由香港到北京,聯繫洽談出版香港作家聯會的作家叢書,並出席了在釣魚台國賓館為叢書舉辦的隆重首發儀式。
曾老總胸懷博大,高瞻遠矚,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文壇,在香港回歸前曾積極籌劃成立世界華文作家聯會,希望以之促進中國海峽兩岸四地及海外華文作家之間的交流聯絡。雖種種原因蹉跎了他在香港作聯會長任內的這個宏大願望,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在他和繼任香港作家聯會會長彥火等作家的不懈努力下,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終於在二○○六年十二月三日於香港成立,他親自坐鎮擔任會長。
大陸的華文文學研究在他的指導和帶領下蓬勃開展,為了更有利於研究事業的推進和發展,他被推舉為「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籌備委員會」主任,為取得學會的准生證,他不顧高齡,多次奔波跋涉於香港與北京之間,親自到民政部面洽申請事宜。幾經周折,用了「八年抗戰」的時間,「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獲批成立。這時曾老總已年逾古稀,超過任職會長的年齡。他無怨無悔,不管職務如何,仍為這個學會和世界華文文學事業出力操心。在每兩年舉辦一次的「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總有他坐在主席台上的身影,總能聽他朗聲發表對這個領域建設和發展的誠摯鼓勵和展望。
「右手拿筆,左手拿梅花」
「右手拿筆,左手拿梅花」,這是曾老總的夫子自道。所謂「右手拿筆」即秉承中國知識分子「文以載道」的傳統,以筆報國;所謂「左手拿梅花」,即堅守做人的氣節和操守。
有如此深厚的文學積澱和愛國知識分子的情操熱誠,曾老總方得先聲奪人、高瞻遠矚,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開拓、並一路帶領,造就了如今華文文學研究事業的興旺繁榮。
回顧歷史,一幕幕往事湧上心頭。在世界華文文學發展道路上,我這個跟着曾老總走過來的人,對「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的召開,欣欣然成就感油然而生。
如今國家大力精簡會議,取消了不少例行活動,卻把從不在視野內的「世界華文文學大會」列入少量大型涉外活動的項目之一。
我突然明白,「首屆世界華文文學大會」的舉辦,對曾老總有多麼重大的意義。為之奮鬥半生,所開創的前所未有事業,終於得到國家的最高認可重視,籌備十一月大會,他哪能缺席!
遺憾的是,最終曾老總因病重未能親自參與大會,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學會舉辦的曾老總追思會上,同仁痛悼倒下的是我們心目中的參天大樹。
大樹傾倒,他開創的事業正在途中。
掩涕悲悼後,沿着他的路,發揚光大,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績,將是我們對他最好的紀念。
白舒榮簡介
作家、編審。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歷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代》雜誌編輯,世界華文文學雜誌社社長、執行主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編審,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理事,《文綜》文學季刊副總編輯等。上世紀五十年代年開始發表作品。八十年代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主要著作《白薇評傳》、《熱情的大麗花》、《十位女作家》、《自我完成自我挑戰——施叔青評傳》等,合著《中國現代女作家》、《尋美的旅人》等。主編、編選《世界華文文學精品庫》、《海外華文女作家新潮散文》、《海外女作家成名作賞析》、《海外華文作家文叢》等。另有未結集的散文、紀實、研究類作品數十萬字,刊於中國內地、港澳台、東南亞及美歐等地報紙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