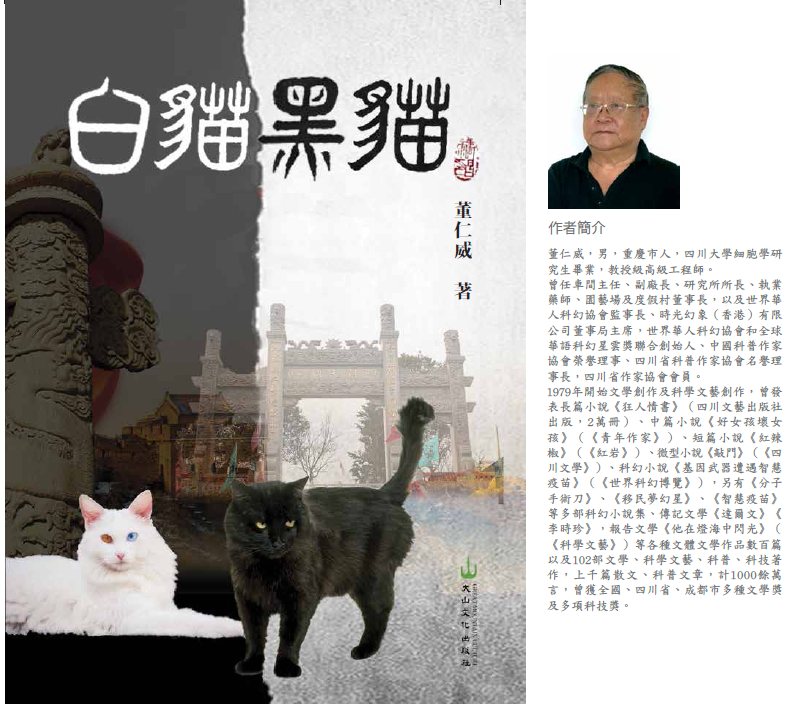胡少璋

我站在櫻花樹叢前,遠方飄來輕快柔和的樂曲,在不知不覺中,我也跟著節拍踏起歌來了。我一邊踏著歌,一邊觀賞著:櫻花樹之間都有著寬敞的距離,每棵樹的高低都十分相近,外形都像一個球體,最親近的兩個球體也只是像兩個圓形相切一樣,各棵樹的枝丫還沒有互相滲透、穿插。樹很年輕、健壯,可能是同時種植的。另外,人工管理以及修剪的功夫都很到家。看去,那一團團的粉紅色的圓球,十分誘人!
面前的櫻花樹雖然數量不是很多,樹上的花也不是開得很茂盛,沒有給人一種五彩斑斕的幻景,然而,它卻勾起了我的一連串美好的真實的回憶。
那是十年前,在廈門大學舉行的文學國際研討會上,我遇見了一位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因為我們寫了同題的論文,於是,雙方進行了深刻的切磋。在研討會即將結束時,這位美如櫻花的金小姐約我去東京「追」櫻花。
明麗動人、亭亭玉立的金小姐,原來是韓國女子。她的父親去日本講學不幸在空難中身亡,奇妙的是一位日本教授去韓國講學,卻遇見了金小姐的媽媽,他倆一見鍾情,隨即結婚,隨即又領著大小美人回到東京。
我到了東京,金小姐著一身和服與我見面,如今她已成為日本的「櫻花」了。因為,今天是她登上講堂教學的第一天,不能與我同「追」櫻花,即由她的父親代為陪同。
父女倆深深地向我鞠躬,表示感謝,因為我的論文對她的啟發,後來她又將自己的論文進行了修改,而獲得好評而晉升為講師。她的父親帶我去新宿御園觀賞那裏一千五百棵盛開的櫻花,又送我到日本最古老的上野公園去......
回到香港後,我寫了一篇〈東京追櫻花〉,該散文一發表即獲得好評,之後,又在海內外多個報刊上刊出。從此,我與櫻花結下了不解之緣,總想再觀賞一次櫻花。然而,身在澳洲又遇及新冠疫情,無法再前往日本去追櫻花。
當我與家居服務的鍾姑娘談起此事時,她即說悉尼就有櫻花,待盛開時,我領你去!

五月初的一天下午,陽光明媚,秋高雲淡,這是最佳的觀賞櫻花的日子。此刻,我所面對的櫻花不是在日本公園,它是在奧本植物園裏面。這個植物園,在悉尼西二十二公里的奧本市,它佔地十三公頃,於一九七七年開放。內有兩個湖泊,一座橋樑......。這個植物園內並設有野生動物園、鳥類養殖場、玫瑰花園、雨林園區和日本花園。
在這個植物園裏,孔雀、袋鼠及鴯鶓等舉目可見。這為該園增添了不少野趣。據聞,每年這裏均會舉行一個櫻花祭,讓人們感覺到「我」又到了日本,感受一下日本文化的渲染。櫻花啊,你象徵著生命的美麗和短暫。
當我要離開植物園時,又回望了在透過仿日本神社的紅色牌樓後面的櫻花叢,心裏有一種難以言狀的感覺,那是因為在異國感受著另一個異國的景物。櫻花啊,你的美麗令人傾倒、癡迷,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啊!
然而,剛才我看過的盛開的櫻花,此刻那粉紅色的花瓣已在微風中紛紛飄落。我舉目向上,面對著那像門框一樣的牌樓,啊,我突然想起:唐朝崔護的詩《題都城南莊》:「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後人從詩中提取四個字即「人面桃花」來形容女子的美。其實桃花美,櫻花更美,如果能將「人面桃花」改為「人面櫻花」那更能體現女子美到極致,美到驚艷的境地。
目前,日本櫻花已遍佈世界,有許多國家都建有櫻花公園。櫻花美麗、短暫,我想女生是這樣,男生不也是這樣的嗎?朋友別憂愁,只要當下你心情愉快、生活幸福就好!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胡少璋簡介:一九四一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六十年代畢業於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 一九八七年加入福建省作家協會,一九八九年定居香港,曾任《香港文學》雜誌編輯、《大公報》編輯、《統一報》總編輯及港英政府、香港特區政府藝術發展局審批員。歷任香港書評家協會創會會長。著有《胡也頻的生活與創作》、《胡也頻的少年時代》、《胡少璋雜文選》、《香港的風》、《香港的腦和手》等。曾在前蘇聯莫斯科大學出版社出版過由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教授馬特柯夫翻譯的兩本書。現定居澳大利亞。 一九九一年寫的《香港的風》獲《人民日報》等海內外「共愛中華」徵文比賽金牌獎,二Ο二一年六月在澳洲悉尼出版《胡少璋散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