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風
台灣著名作家、退休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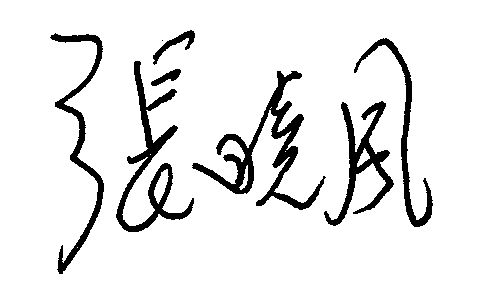
小時候,父母、老師好像都喜歡勉勵我們,他年長大了,要「做大事」,或是「做一番大事業」──記憶中似乎從來就沒有誰勉勵過我們要去「做小事」。
但,我這輩子好像都在「做小事」──而且,要命的是,我好像還挺愛做這些小事。
有個目盲的鄰居朋友,半夜兩點忽然打電話來。她一個人住,教鋼琴為生,跟一條老狗相依為命,我有時煮茶葉蛋會分送她幾個。她那天打電話來,泣不成聲:
「怎麼啦?怎麼啦?」
「我的狗狗……我的狗狗……剛才,走了……」
她一直哭,我一直聽,她的心情,我懂,她家不是死了老狗,而是死了「親人」,但一時也找不出什麼有意義的安慰之詞,只能胡亂說些「你不要難過了……」「牠也算安享天年了……」「我想牠臨走前,一定很希望看到你以後能快快樂樂地活著……」這麼說著,唯一的功能也許只是讓她知道,我在傾聽,她不是在對空氣說話。後來,也許她說累了:
「對不起,三更半夜,我忍不住……也沒有別人可說……牠就這樣走了……打擾你了……對不起……晚安。」
深夜,聽人哭,聽人傷悼她的老狗,這事,夠小了吧?只是,我覺得很好,在這五百萬人的大城裏,她獨獨撥了我的電話,她容我分擔她巨大的疼痛、驚恐和哀傷,這件事──比有人找我當什麼「國策顧問」要榮耀多了。
我願意做這種「小事」。
在這個地球上,從不缺「做大事的人」或「痴狂於想做大事的人」。古往今來,歷史是由他們導演的,但絕大多數的人,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以上的人──像我──是個做小事的人。
這會兒剛好是歲暮,做華人不錯,每年過兩個情人節,過兩個歲暮,兩個新年。歲暮對生意人來說是「盤點」日,我於是也想到要來盤點一下。我的錢很少,用不著費神。我的孫女只有三個,白痴也會數。那麼,我且來清點一下全球人口(咦?說得好像我是「地球」的「球長」似的),特別是在疫情之後。但,說到清點人口,天哪,在古時候,這可是全盛時期的帝王才敢想的事。是件要報名上冊、動員並串聯全國人力,拚上一、兩年才能做成的大事,而此刻,哈!只是「小事一樁」。我請助理幫忙,她五分鐘不到就查出來了,是七十九億多。我想想,七十九億是什麼意思呀?這數字太大,超乎我的想像力,我請她以「每秒鐘唸一個人的名字的速度」去唸這七十九億之人的名字(其實,有些人名字太長,一秒鐘是唸不完的),而這位「唸名之人」每天工作八小時(這八小時內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不抽煙、不打電話,週末或刮風下雨也照常執行任務),這樣下來,要多久才能唸完這七十九億人口的名字呢?答案也立刻揭曉,整數是七百五十三年。啊!我現在有點明白七十九億這茫茫無邊的意義了。古人說「芸芸眾生」,但「芸芸」二字有點太美,讓人忘了它那草芥或沙礫一般的卑微性和庶眾性。
七十九億,說來絕大多數都是「卑微庶眾」吧?如果以五人左右為一家計算,大地上有近十六億個家庭,如果這十六億個家庭各有屋頂和窗戶(有屋頂的人是幸福的,難民就沒有)──唉!那得多少抹布來擦餐桌?多少鍋子來煮麥片粥或大米粥?多少碗盤要洗?多少床單要換?多少窗子要擦?多少小狗、小貓或牛、羊、豬、雞、鴨要餵?多少花木要澆水?多少稼穡需要去辛勤照顧?多少車要開出門(包括貨車、小客車、摩托車、腳踏車、嬰兒車)?多少小孩要陪他做功課?多少老人要送去看病或為之送終……
這些都是「小事」,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就做著這些小事吧?而所謂「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多半不是靠「殺人」就是靠「逼人」來過日子。成功而不害人的人也有啦,但不多,像比爾蓋茲或張忠謀,或者,遠古之前的孔子、孟子……。
我還是喜歡做個「做小事的人」,但我又不免希望我做的是「好玩的小事」。什麼叫「好玩的小事」呢?茲舉數例如下:
有個同事,有點可愛,他成天嘮嘮叨叨,一進辦公室就向人報告他的婚事目前進行的節奏。後來又向大家詳述妻子懷孕、待產,並且終於生了長女……,我對他家的事不覺已瞭如指掌。不久,他的苦惱又來了,他的女兒命中缺水,他苦想一個有水的字(部分台灣居民常強調自己「不是中國人」,但在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迷信上,卻比任何地區的華人更中國,像「陳水扁」就是個好例子)。這同事又堅持名字最後一個字已經決定了是「秀」,我於是叫他用「泠」,「泠泠七絃上」,「泠」比其他水部的字要詩意多了,「泠」字讀來高昂清揚,出於唐詩名句,跟「秀」字的沉實讀音可以相輔相配。他立刻同意,後來那孩子也很成材。
去滿足那些為小孩求名字的父母的期望,我覺得是人間的「優等小事」。
另有一家的兒子則缺火,有火的字多半不怎麼雅,他又說那火字部的字必須十二劃,我於是說:
「叫他『斐然』吧!你不要看『然』字下面四點水,其實它下面是個『火』字。『然』的聲音也很好聽呢!」
他大為佩服,便欣然採納。
還有個朋友住在介乎台北市中心和「新店景點」之間的「景美區」。那地方的街名像兄弟排行似的,常用「景○街」,他住的那一條叫景仁街,他喜獲麟兒,我便勸他直接以「景仁」為名。「景」字本身是個好字眼,代表光明、美好。在古代,是一個可以選來作皇帝年號的字。「仁」也是個好字,幾乎包含了整個儒家思想的精華。小孩取這名,有點像從小就當了這條街的「街長」,他後來在美國做了律師。

這些是四十多年前的陽明醫學院的學生,多年後,他們的同學會在曉風舊居(今列景點,位在屏東,名叫「永勝五號」),請張老師(前排中,小黑板左方)「再為我們上一堂國文課」。(張曉風提供)
此處容我把話岔開,余光中教授曾跟我說,他教學生,還帶「售後服務」,那就是,常為學生證婚。而證完婚每每還有其「一貫作業」──為他們的新生兒取名字,啊!作「詩人的學生」真是賺到飽。
另外有個國樂團成立,他們有教會背景,想找個團名,我幫他們想了個「師曠」,師曠是春秋時代孟子、莊子都讚美的敏於音律的音樂家。而這名字,我私下想用「今解」(事實上也並無「古解」),將之詮釋為「師法曠野精神」。從宗教情懷來說,一切藝術雖也都有老師,但到了某個境界之後,便應該一空依傍,去站在無邊無際天風過耳絕無人煙的茫茫曠野中,像古先知摩西,去師法無限的自然和天機。
他們接受了這個名字。
另有個朋友,八十年代得風氣之先,跑去中國大陸做生意。她做什麼我有點說不清楚,似乎是為一些特定的有錢有勢的貴婦代購時髦的歐洲名牌衣服,她們全然不怕價高,她因而賺了不少。賺多了,她偶而跑回台北來,開了個自己喜歡的小店,很豪氣地不管賺不賺錢。小店面,只賣她搜羅來的小陶器,她請我幫她取個店名,結果我幫她把連中文帶英文都一起想好了。中文叫「立陶宛」(扣住「賣陶」的特質),英文則因為店小,便叫「little one」,兩個發音十分相近且好記,她為之驚艷。
除了給人起名,給社團起名,給店舖起名,我還給「活動」起名。
七十年代,有位在台北植物園區工作的朋友告訴我一件事。
唉,且讓我暫停一下,說說這台北植物園,這園在日本時代就已存在,且規劃得不錯。日本人曾把台灣高山上的神木搜刮一空,去讓京都或東京等大城的神社前有傲人的撐天大柱聳立,反正台灣是殖民地,不搜刮白不搜刮。當然,為砍伐且運送那些巨大沉重的神木下山,可想而知死了不少原住民。這些樹讓日本許多神社挺風光,讀者如去日本旅遊,不妨在重要神社前停留一下,看看地上有小牌子說明這神木的原產地是台灣。
台灣高山珍木遭日本毒手,這是千年也恢復不了的(神木的平均年齡高於三千歲)。但日本人卻在台北市規劃了一座植物園,有點像奪了我的一億家產,卻丟下一塊錢來還我。
不過,走過喧囂的市區,我還是忍不住有點喜歡這座植物園,特別是那片荷花池。每年夏天我都會給自己訂一個「荷花節」,那天,我會去池畔坐坐,對著荷花發獃發癡。
可是國民政府來了以後,大概覺得植物園既然那麼大,不妨「廢物」利用,於是便蓋了很多機關塞進去,包括小型博物館、科學館、廣播電台、小劇場,雖都不是什麼「壞玩意兒」,但原來站在那裏的不會說話的植物只好乖乖去死。
而我的朋友告訴我,由於這些機關廢水排除不當,荷花死了很多,而且,青蛙也死了,等到夏夜,居然聽不到蛙鳴。天哪!這怎麼對得起小朋友,憑什麼剝奪他們童年的顏色和聲音?
最近他們解決了污水問題,但青蛙一時也恢復不過來。
我輾轉找到一位日本學者,他當時正在中央研究院作台灣青蛙的研究。他聽我說及此事,答應給我三大鐵桶蝌蚪去放生,讓池塘的蛙量恢復。這放生可不是隨便可以去做的「好事」,必須事先弄清楚,以免蛙種不合,互相八字相剋,造成生態浩劫。好在此人是專家,可以信任。
於是,擇定吉日良辰,呼朋引伴,叫各家朋友「出小孩」,共襄盛舉。當天眾小將一一努力舀蝌蚪,往池塘中放,但我作為領軍,不免擔心,萬一有小孩把自己也跟蝌蚪一起「放下去了」,那可怎麼辦?

七十年代提倡愛護大環境,張曉風老師與小朋友一起到植物園去放三桶蝌蚪(原蝌蚪因故死亡),此行動題名為「預約一個有聲的夏夜」。前排蹲身執勺者為張曉風,爬在樹上的是亮軒的次子。(張曉風提供)
我給這活動取了個名字,叫「預約一個有聲的夏夜」,「預約」這個動詞當時只用在出版社待出新書的時候,「預約」會有很好的折扣,我把它轉換為對蛙鳴的期待。
當晚的電視和翌日的報紙都報導了這件事,都打出「預約一個有聲的夏夜」的名號。
後來,「預約○○」也就不斷有人套用。用就用吧,我最高興的是,那年夏天夜晚跑去植物園一聽,果真有一片聒耳的蛙鳴!
那三桶蝌蚪想來有的讓水鳥水鴨吃了,有的讓魚吃了,有的讓路過的飛鳥吃了,有的被池中水鱉水龜吃了,但無論如何,有一批活下來了。並且,鳴響整個長夏的每一個夜晚。
凡此種種,都是小事,我喜歡忙活著做這些拿不到半毛錢的小事。
小事萬歲!
(本篇稿酬請代為捐贈香港正生書院,他們為少年吸毒者戒毒,很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