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承志(內地作家)
張承志(內地作家)
我對五木寬之《看那匹蒼白的馬》的書評引起出版社注意、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譯文被發掘出來並以我書評充序在中國出版——此事的意義,惟在原作提出的思想終於得以在中國問世。但是,隨著發覺不僅讀者包括編者、甚至日本的讀者和編者都並不多麼在意這一思想,興奮便不得不冷卻下來。書卷之外時光流逝,一股悲哀漸漸變成了繼續發掘的決意。
我明白了:在這個腦殘時代,顯然讀者(不僅急功近利感覺粗糙的中國讀者,也包括「讀書之國」日本的讀者)愈是對重要的文字,就愈是不求甚解。
至今書評發表已有十年,那些「含義」若再不解說就真地湮沒了。趁這「不宜出行」的黃曆三月,我想作完這件功課。
寫之前先告誡自己:概括與凝練的中國古典散文筆法,尤其在這二十一世紀未必是好的寫法。哪怕一筆,只要不把話說透說白,讀者並不像你預想的那樣主動聯想。所以,放棄含蓄,文前點明:我要說的「含義」有三:關於馬的毛色隱喻的糾纏、「他本質上是個短篇小說作家」的意味、那匹威脅世界與我們的怪馬是誰。
一
原著書名《蒼ざめた馬を見よ》,我的書評自譯書題為《看那匹蒼白的馬》,中譯本譯名為《看那匹灰色的馬》。沒有哪個對與不對,這些譯名都差不多。它確實與聖經中象徵死亡的一匹白馬關聯,但那匹馬在影射誰、它在當今世界的「含義」才更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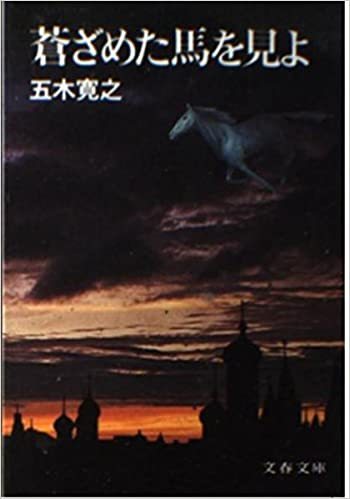
五木寬之《看那匹蒼白的馬》。(資料圖片)
先是在《讀書》雜誌的讀者留言中,有人議論說書評沒必要扯到那麼多「蒙古話中馬的顏色」。後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對著我的「蒼白」和小說譯者的「灰白」想二者擇一,他搬來香港的聖經學者引經據典,當然認為《聖經》的記載就是謎底。
而我是牧民出身,先於聖經獲得的教育是蒙古牧人的知識。我用遊牧民族對馬的稱呼及馬的顏色含義裏的「不潔」,以民間術語來加強那匹馬給人的不祥感覺。
編輯似懂非懂,於是中譯本特加了一頁講述這個譯題始末。我很願意把序言題目改得與正文一致,但保留了序文中的自譯段落。或該提及:我對引文的自譯與小說正文之間存在譯筆的微妙不同——我沒改動它,是想藉它表達我對原作思想的理解。
書評裏講到了蒙古牧民描述馬的兩種顏色。原因是我深知談及馬之顏色,唯牧人才是真正的權威。所以如「撒了」(saral)和「薄了」(būrul),它們的含義都並非「白」卻常用于白馬,因為牧民的「白色」(查幹/čagān)是概念的,針對馬使用時,它是理想的純白而不是現實中的斑駁雜色。我說「那是一種不純的白,編字典的蒙古人居然用『污白色』來表達」,我想強調的是它「給人的視野和心裏留下的不悅感覺。」
但我終於明白了,世界秩序已把人改造得讀法全變,所謂讀解、潛讀、吟味、會意、參悟——已經是舊時代的回憶。奢談什麼類近的語言心理乃是讀解的條件,對我這樣的作家,這才是真的難關。
到了去年底(二○一八年十二月),在我應日本的河合塾(高考預備校)為應屆考生編輯的「我挑選的這一冊」約稿推薦讀物時,選了五木寬之這一本。我用日文把舊書評改成千字文,講到「包括我們在內的人們一直被洗腦卻並沒有意識到,習慣了拒絕呼吸新鮮空氣」的現象,我抱著幻想,對異國的高中生建議說:
「不願被社會潮流沖走的你,更適合異色的讀物。所謂讀書——或許正是發現真實之旅的出發。」
(社会の流れに流されたくない君は、異色の読物にふさわしい。読むことあるいは、真実へ発見の旅立つ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
不想囉嗦沒完,和合塾的編輯也是執著於聖經裏的那匹馬,不願接受遊牧民族的顏色觀。我煩了,不再解釋。隨他們印吧,反正我能留住自己的原稿,將來的文集裏添幾篇外文作品也不錯——只是其中的意味使我禁不住思索:他們為什麼總強調流行觀念而不願捉摸原作的警告,他們的腦子怎麼一圈也不轉,難道他們的眼前沒有掠過一匹不詳、惡意、污髒的馬麼?
二
關於「讀」的感慨之外,真正引起我長久思索的,不是上述的聖經故事與牧民觀念而是下面一段:
「……雖然也能使人感到超越種族響徹人心的痛切,但那與昔日給他以撕咬般刺激的米氏,總之並不一樣。或許,他甚至想,這個作家本質上只是一名短篇作家?也未可知。」
這裏藏著五木寬之的直覺。與「短篇作家」對立的,是被吹捧為「俄羅斯文學空前僅有的」長篇巨制。所以它也同時暗示了長篇小說的定義。這是兩種作品,甚至是兩類文學。這種觀點沒有被深入解釋,但使我一瞥開眼。

日本作家五木寬之。(資料圖片)
這是一種文學觀點,或者說,是一種文學學術觀點。它當然沒有被文學評論家提出過。這裏存在著對短篇作家與長篇進行兩類區分的,遠不止於篇幅技巧即形式、而是從本質上所作的判斷。
《看那匹蒼白的馬》裏的「短篇作家」判斷所依據的,是由於「過早看夠了不應該看到的」東西而抵達的「乾渴的虛無主義」、是使小說失去安穩感的「黑暗裂縫般的虛無感」。他沒有引伸至其他主題。但他指出了「短篇作家」是一種「與煽情主義處於對立之另一極」的作家。他指出社會熱捧的長篇「搭乘著庸俗的商業宣傳一路成為快賣榜首」,給他帶來一種「生理的厭惡感覺。」這些話不能不引起讀書人的聯想與思考,因為他們已經被牢牢吸引。
「短篇作家」是什麼?
無疑這是一個文學理論題目。也許它還超出了文學的桎梏,觸碰了漫長的思想史領域。
不消說文學變化無窮。
無疑短篇小說也罷散文也好都自由不羈,不服從概念的規定。但思想的含義更從不依仗篇幅的拉長,思想的意義只在於真與假,以及表達它的語言力量。何止篇幅,包括形式都從來不是問題,文學的生命是魅力與發現。我不再多發揮了——文學本身是多義曖昧的,心有靈犀自會體會。只是,五木寬之一語點破的「短篇作家」,給了我們判斷文學質地的某種標誌。
在造假時代討論它當然不合時宜。不過,代代更迭的人潮裏會有新人湧現。他們不是只瀏覽六十字微博的網蟲,而是新一代古典意義的讀書人。他們會參與和吟味,早晚刷新腐朽的文學理論。
順便說,書評裏我的一句話必須刪除:「按中國流的小說劃法就在小中篇與長短篇之間」——「小中篇」一詞是我學作小說時從文學界沾染的一個庸俗提法,它表現了對「短篇」本質的缺乏認識。
也許可以說說相對的另一極,即長篇小說?我們常看到長篇小說雖然充滿不節制的渲染,但其實輕薄者多。較多的現象是,它們顧全了故事的平衡,但篇幅未必與內含的思想平衡。而且,即便優異的秀作,也缺乏古典的洗練。
表述的急迫,不允許拉長篇幅。所以古典都是短篇,古典長篇名著半數是綜合民間話本甚至源於外國(若《西遊記》)。而所謂短篇隨筆或小說,即便採輯社會風物傳奇,也常常旨在文以載道。總之命筆乃為一件事或一種思路的點破,有時是由於它感悟了什麼有話要說。
它說到底就是「言論」,不過假文學以磨拭思想。它本是一己述懷,後來才流傳朋友。它身在異類,乃屬「五蠹之民」。比起娛樂,它更是辭藻的「惜身」之作。自然它多是短章,不作拖遝,愈是有意味的描述,就愈不顧平衡周到。它與媚眾及商業之間,幾乎天生缺少維繫。至於長篇,則是伴隨白話漸次成為書面語才興起的。其間世事滄桑,到了印刷垃圾時代,常見長篇作家愈寫愈快水兌得愈來愈稀。似乎長篇教人學壞——或該說:它們距離中國古典出神入化的簡煉傳統,已經太遠了。
中國古典為觀察世界提供了極高的標準。從這樣的文學觀眺望,凡懷著真知灼見的作品,確實文字無須太長。我猜五木寛之或有類似感觸,因為他面對一個世界陰謀的巨制,不是從政治背景而是從作家品質進行甄別,他甚至這樣措辭:這個作家本質上只是一名短篇作家。
三
最後一個有趣現象是:不僅是在中國,包括在作品的故鄉日本,讀者們直至今天並不理睬作家警告過的那匹不祥的、污白色的馬。自負的日本文學評論家們沒有討論那匹馬是誰或是什麼,讀者人人都知道這位作家有名,但並不細究他的思路。
更不消說我小小書評二次呼籲的話語。一點都沒有錯,人們持續地接受洗腦,絲毫不覺得難受。
短篇小說包括散文(順便說,散文與短篇小說並無質的區別)追求的古典與洗練,在這個愚蠢的世紀裏也許純屬作繭自縛?雖然比起長篇,它們也許進行著更廣闊的戰鬥。
那「以自由這一觀念為釣餌給世界設置了巨大陷阱的、堪稱藝術的惡意」,如一代代病毒的變異,尤其經過加入洗腦工程的知識分子操作,繁殖膨脹,向著人類最後的良知攻擊。
魔鬼騎著那匹馬跑遍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除了遊牧民族之外,沒有人發覺:那顏色並非如宣傳的潔白。
草就於二○一九年春三月,霾中
(書評《看那匹蒼白的馬》刊於二○一四年三期《讀書》,《看那匹灰色的馬》二○一七年九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以此書評為中譯版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