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秀蓮
靈異這回事,信者言之鑿鑿,不信者視為穿鑿附會。世事難解,幽玄偶爾一閃,以不可思議的形式,以難以置信的表達,靈異驟臨,乍然造訪,向人間親友來個靈犀一點,完了心事,便倏忽而去,只因陽間未許徘徊。我自小已聽聞一些靈異經驗,自己則從未經歷,不意在日前,終於遇上了,遇上了……當下我呆立在打印機前,震驚不已,泫然悲泣。
四月十二日我坐在太古城蘇浙匯的角落,等候譚福基校長來午飯,上回他做東,今次還鍾之宴。
譚校長一九六八年英華畢業,入港大中文系,年輕時已與同道創辦《詩風》、《詩網絡》,篳路藍縷,充滿理想。晚年重投舊詩懷抱,詩人詞客,庾信文章,尤精七律,詞則境界高遠,對聯自是得心應手。在Facebook讀過他的詩詞古文,内心一顫,他只年長半輩,學問才氣竟然比我高了十級。身為散文創作人,我絕不輕易這樣讚賞行家,然而人家根基盤虬,筆法空靈,我不得不俯首稱美。

譚福基校長。(作者提供)
在餐館久候半小時,怎麼仍不見那踏實的步履呢?我開始有點不安,不會有事吧,他從北角坐地鐵來,不太可能有交通意外的,電話響了良久,終獲接聽。譚太太說校長在凌晨時分中風,情況嚴重,此刻在瑪麗醫院,動過手術,醫生說蘇醒無望了。
天呀!怎可能發生這種事?分明詩興濃郁,文心滿溢,如星星燦爛於夜空。奈何人間好物不堅牢,翌晨他永別文苑了。那麼,星星隕落,墮在何處?
他退休後,花了六年光陰來研究姜夔,去年出版了《蝴蝶一生花裏--八百年前姜夔情詞探隱》,識見不凡,創前人之未創。我特別寫了一篇推介〈徘徊《蝴蝶一生花裏》〉,所謂「修辭立其誠」,推介發自真誠,讚美出於由衷,絕無捧場之意。此書無論質量分量,都超越無數博士論文,這水平足以在大學開設一學期專家詞了,難怪中央圖書館請他明年演講關於姜夔情詞的研究。好書不能寂寞,才人理應名揚。
.jpg?x-oss-process=image/interlace,1/quality,Q_100#)
譚福基著作《蝴蝶一生花裏──八百年前姜夔情詞探隱》。(資料圖片)
後來我又寫了〈空姐煎炸奉坊鄰〉,回應他的七律:「昔日翺翔千萬里,今朝煎炸奉坊鄰。生涯必備薪與水,小店猶煩苦與辛。路險未容多俊選,心寬自力少憂貧。人間不絕滄桑客,我亦滄桑寓一塵。」文字相交,互相鼓勵。
剛剛擺下飯局,誰料得到世事無常,翌日就動筆寫悼文〈蝴蝶花裏水仙操--悼詩人譚福基〉。品性敦厚且才華橫溢的詩人詞客,靈感尚有無數,雄心最為勃發,竟猝然辭世,真是「長使英雄淚滿襟」!我問星星,為何為何?星星默然無語。
胡燕青是校長五十年的詩友,鄒志誠是校長情同骨肉的師弟,我是新知,三人在喪禮上中並排而坐,蓋棺那刻,我們仨抱著痛哭。禮儀告畢,我目送披著白色祭袍的神父,袍角輕飄,領著白色靈柩步出靈堂。靈柩給輪子推動,似輕又重,載著淚影,婆娑而去。
喪禮過後,我為自己第七本書初次校對時,在〈徘徊《蝴蝶一生花裏》〉那篇文章附錄後記:「詩人譚福基於二○二一年四月十三日因中風永別詩壇,重讀此文,倍添傷痛。」
再次校對時又把全書列印,怎料打印機忽然卡紙。關上電源,移出碳粉盒子,小心翼翼把卡住那張紙拉出來。那張紙,狀態完全不似卡紙。紙抽出來,四周端正,沒有起角。摺紋一摺又一摺,如手風琴,間距均勻,摺與摺的距離不及半寸,十分細緻。從左到右,從上到下,寸寸都摺得清楚玲瓏。我再仔細看看,天呀,正是〈徘徊《蝴蝶一生花裏》〉最後一頁,印上追思後記那頁!當下我呆立在打印機前,震驚不已,泫然悲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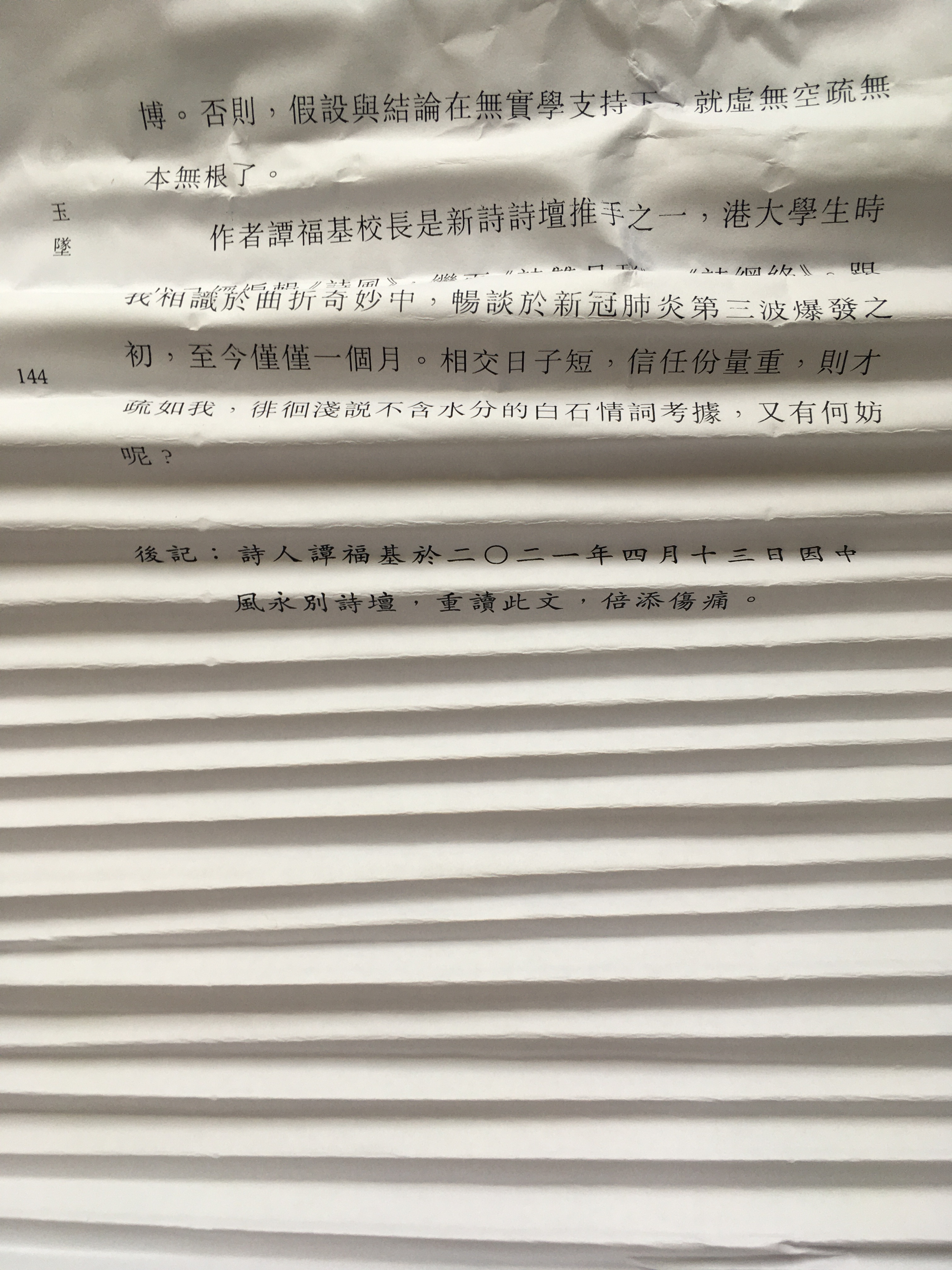
摺紋一摺又一摺,如手風琴,間距均勻,摺與摺的距離不及半寸,十分細緻。(作者提供)
一疊全新影印紙,整齊擺放入槽位,按常理不會卡紙的。再者,給卡住的紙,又怎會有這種如手風琴的摺痕?全書有一百六十四頁,為什麼不遲不早,偏偏就是這頁卡住?我把摺痕摩娑,薄薄而摺痕橫列的紙張起起伏伏,幽異如密碼。朋友認為是校長來謝我這知音,給他提醒,我忙抹去眼淚,立刻從書架取出《蝴蝶一生花裏》,把書立在打印機上,三鞠躬還禮。
星語難解,幽微隱祕,終於會心而頓悟了。手風琴低迴欲語,不以驚慄報信,而以紙墨寄意。「誰見幽人獨往來?縹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不就是詩人譚福基的身影嗎?
二○二一年五月
黃秀蓮簡介: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師承余光中 ;曾任中文大學圖書館任白珍藏展──「九十風華帝女花」策展人 。著有散文集《灑淚暗牽袍》、《歲月如煙》、《此生或不虛度》、《風雨蕭瑟上學路》、《翠篷紅衫人力車》、《生時不負樹中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