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定銘
侶倫的散文集有《紅茶》(香港島上社,一九三五年)、《無名草》(香港虹運出版社,一九五○年)、《侶倫隨筆》(香港太平洋圖書公司,一九五二年)、《落花》(香港星榮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和《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年)等五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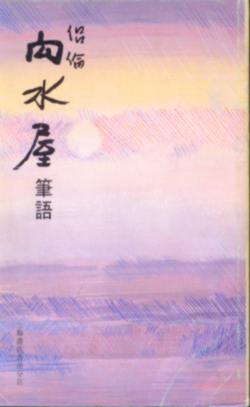
侶倫的散文集《向水屋筆語》。(資料圖片)
此外他還有本很多人都誤以為是散文集的《紫色的感情》(香港星榮出版社,一九五三年)。我幾經辛苦找到這本六十年前出版,並已絕版多年的原書,細心一讀,發現八萬多字的《紫色的感情》,表面上是由五十八封書信組成,如果單看目錄,把本書誤以為是散文集一點不奇,其實書前有〈序曲〉,交代了故事發生的始末,再讀了書信的內容,你一定不會稱《紫色的感情》是散文集,一定明白到作者的心意:用五十八封信來組成一個長篇!
〈序曲〉中說:作者在一個生辰宴會裏認識了一位愛文藝的S小姐,她給他說了一個「朋友」的故事:
一個女孩子主動地和她仰慕的作家薛嘉靈通起信來,原先只是虛榮心作祟,後來卻不自覺陷入了情網。而作家也同樣愛上了她,不能自拔。她冷靜下來後,怕這段紙上的愛情不會持久,終有幻滅的一天。於是揮慧劍斬情絲,和現實生活中的另一男士結婚,到外地生活。同時把作家給她的信轉給本書的作者。
S小姐離開後不久,作家薛嘉靈即因長期憂鬱症病逝!
侶倫寫《紫色的感情》,是經過精心策劃和慎密構思的,全書就是薛嘉靈寫給S小姐的五十八封信,而不刊S小姐給他的信,這在故事裏留下了很大的空間:S小姐說了些甚麼,會使薛嘉靈這樣神魂顛倒?增加了讀者的無限想像……,這種以單方面表達故事的寫作手法,在一九五三年應該不多見。
侶倫擅長編電影劇本,五十八封信就是五十八個場景,作家的個人獨白,有無限發揮延伸的潛力,落到一流的導演手裏,必然會演化成高水平的藝術作品。
這樣的一個傷感故事,怎麼會變成了「散文集」!
侶倫散文的種類大致分:寫個人感情和生活的(《紅茶》、《無名草》和《落花》)、閱讀筆記和隨想的(《侶倫隨筆》和《落花》)及史料性的(《向水屋筆語》)三大類。
《向水屋筆語》是他散文中最重要的作品,侶倫在〈前記〉中說:
在這方面著筆的時候,我無意為一些人所謂的「香港是文化沙漠」這一觀念作辯正;我只是憑自己的記憶,把所知的一些人與事記下來,說明這塊「沙漠」也曾經出現過一些水草。但這可不是「史料」,而只是一點點瑣碎的憶語。
侶倫在這裏所說的「這方面」,就是書中第一輯的《文壇憶語》,輯中十多篇文章,記的就是他一九二○至四○年代,在香港所接觸到的人和事。
侶倫是一九二六年涉足文壇的,在香港文化圈子內活動超過六十年,是見多識廣的老前輩,與他同代的文化人,只有平可寫過〈誤闖文壇憶述〉(11),但內容僅限於他自己活動的小圈子,質和量都遠遜於侶倫的《文壇憶語》。
此中〈香港新文化滋長期瑣憶〉談早期的書店、報紙副刊、《伴侶》、《字紙簏》、《激流》和《紅豆》等期刊,侶倫都參與其事或寫稿,資料詳盡,過來人的親述與一般憑資料寫成的記述截然不同;〈寂寞地來去的人〉、〈島上的一群〉、〈《島上草》胎死腹中〉、〈關於《時代風景》〉……中,很多資料都只有他知道,很多還是他未寫這些文章前從來未有人提及的。侶倫在〈前記〉中說「但這可不是『史料』」這句,真是可圈可點,這應該是第一手史料,是編寫香港新文學史的一份珍貴文獻!
侶倫不擅辭令且沉默寡言,我曾與他同桌參加晚宴,整晚近三小時,說不足五句話,但他在散文中卻是滔滔不絕,而且不忌諱談私事,全是一個「真」字,這可以在《紅茶》和《無名草》中得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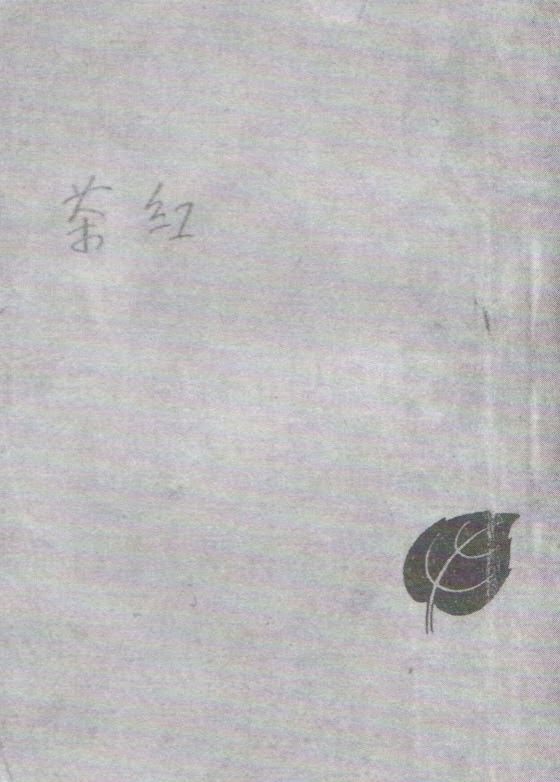
侶倫的第一本書《紅茶》。(資料圖片)
《紅茶》是侶倫的第一本書,分《殘絃小曲之什》和《紅茶篇》上下兩輯,共收十六篇作品。侶倫在〈前記〉中說「這裏面的每一篇文章,在動機寫的時候以至寫好,都不過是企圖抒發自己心中的鬱結;最高的目的,也只在給自己一種適意的滿足」。正因為這種純真,散文才不會矯揉造作,才會有感情,才能叫讀者感動!
侶倫的妹夫江河(一九一六-二○○六)也是本港著名的作家,還有筆名紫莉、金刀和魯柏。他以筆名魯柏在五百字專欄──《雜碎》(12)的一篇〈林風與林鳳〉中,談到侶倫與郭林鳳(葉靈鳳的離婚妻子)一段情誼時曾說「郭林鳳這個人在他(指侶倫)的生命中的確是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在感情上,侶倫付出比林鳳多……」,並指出侶倫的處女作《紅茶》中,有很多篇都是寫林鳳的。在《紅茶》出版近二十年後,侶倫把書中近十篇充滿情意的散文重寫,全收進《落花》中,可見他對那段情念念不忘。或許,這就是侶倫所說「心中的鬱結」吧!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攻陷香港之時,侶倫是住在九龍城「向水屋」(13)的,他目睹平民百姓在日軍的淫威欺壓下忍氣吞聲,過著亡國奴的生活,生命隨時被結束……。他終於忍不住,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逃到東江上游的紫金縣避難。在平靜的鄉間歲月中,他一邊在小學裏教書,一邊默默地筆耕。這時候有朋友來信,說要在曲江辦報邀他撰稿,他便隨寫隨寄,寫了一大批揭發日軍暴行的文章,以備將來組成《香港淪陷回憶錄》出版。可惜朋友的報紙辦不成,他幾經辛苦討回來的稿件,僅剩下零星的散頁,《香港淪陷回憶錄》便出版無望了。 在紫金隱居三年多,侶倫勝利後回到香港,向水屋已被夷平,他撫平了傷痛,在生活穩定以後,便整理這幾年的散稿出版了《無名草》。
《無名草》雖然書分《無名草》、《火與淚》和《生死線》三輯,其實只是兩類文章:《火與淚》和《生死線》收〈難忘的記憶〉、〈孤城的末夜〉、〈淪陷〉、〈橫禍〉、〈人性以外〉……等十篇,正是索回來《香港淪陷回憶錄》的散稿,這裏有淪陷前文人焚書燒信的恐慌;誤闖禁區,生死繫於一線的驚嚇;為了未得允許而購買香煙,迅間身首異處;搭公巴全車被捉去「剝光豬」搜身……,日軍的種種暴行,讓我們未經戰亂的後生小子,以為在讀《天方夜譚》!

侶倫散文集《無名草》。(資料圖片)
《無名草》一輯中也收十篇文章,是他戰後生活的點滴,此中〈故居〉、〈舊地〉、〈書二題〉和〈我的日記〉數篇,感慨尤深。和平後回到香港,他到九龍城去,緬懷昔日的生活片斷,時空轉移了,故居景物和人事當然已不再了。文人多是感情豐富的動物,記憶中的無助,忍痛焚燬寫了十三年的二十本日記,那種傷痛是不能用文字表達的,侶倫說:「我愛惜我的日記,比較在『舐犢情深』這觀念下愛惜自己的作品還要深切。因為後者是用思想去寫,而前者是用生命去寫的」(14)。試想想:那些記載了個人「生命的成長,思想的變遷,青春的哀樂」的文字,要在一瞬間化成灰燼,執筆要描述那種哀痛時,誰能不手震,誰能不痛心疾首!
寫《無名草》時侶倫已三十多歲,較青少年時代出版的《紅茶》,無論是思想上,寫作手法上和文筆,都有長足的進步,生活的歷程,是作家筆鋒最好的磨練。
《紅茶》、《無名草》和《向水屋筆語》是侶倫散文的極品,可惜《侶倫卷》字數有限,我們只能選出最精彩的收在這裏,想一窺全豹,就得訪尋原書了!
侶倫以小說寫得最好,但他一九二六年以《睡獅集》初涉文壇卻是以新詩起步的。幾十年後他在〈想起一個除夕〉(15)中強調「我不會寫詩」,這句大概不是自謙之詞,他的十多本著述中沒有一本是詩集,可見他的新詩的確寫得不多。編《侶倫卷》時很想收齊他各類文學創作,可惜盡了力,遺憾只能搜尋得〈訊病〉、〈歸航〉、〈流亡的除夕〉、〈九月的夢〉、〈忘題〉和〈哀敬〉。
〈哀敬〉有個副題──〈送蕭紅女士遷葬〉,送蕭紅骨灰回國,是香港文化界一九五○年代的大事。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香港文化界數十人送蕭紅骨灰上火車,與蕭紅素不相識的侶倫參加了是次盛會,送同齡人骨灰的事,深深打動了侶倫的心坎,回程時他寫下了悼念蕭紅的詩句:
著作等身算得什麼呢?
如果那只是一帙白紙。
蕭紅沒有等身的著作,
然而她寫下的每一頁都不是白紙。(16)
侶倫回去以後,把這四句詩演化成七組四十二行的〈哀敬〉,發表在《大公報》上。一九八八年侶倫猝逝後,《八方》的〈侶倫先生紀念特輯〉上,就選刊了〈哀敬〉以作紀念,因為那是侶倫最關心的事──「他寫下的每一頁都不是白紙」!
此中特別要提的是〈流亡的除夕〉。這首詩寫於一九四二年,那是香港淪陷後的第二年,侶倫穿過封鎖線,逃到東江上游的小鎮,滯留在那兒從事教育工作,過著「異鄉飄泊,孤立無助」的生活。他在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九年,寫了回憶性質的散文〈想起一個除夕〉,就用〈流亡的除夕〉作引子,說「這幾行句子,卻記錄了我當時的情景和心境。多年來也不曾忘記。因為這是我有生以來所經歷過的一個最不愉快的除夕」(17)。
〈流亡的除夕〉只有分成四組的十二行:
除夕,
給雨封住了。
如在空間劃上五線譜。
異鄉,
有徹骨的寒冷,
和流亡的淒涼味。
室內病妻的呻吟,
屋外的爆竹聲遠聲近,
混合於五線譜之中。
壁上,
被冷落的生豬肉,
也滴著淚了。
詩是情景交融的結晶:在淒冷的寒夜中,由雨聲、爆竹聲、呻吟聲合奏的五線譜;異鄉流亡的淒酸,與本地人的新年歡樂氣氛,成了強烈的對比……深深地刺入詩人的心坎,難怪他畢生難忘!〈流亡的除夕〉是一首出色的小詩!
──二○一四年十月
(11)平可的〈誤闖文壇述憶〉見《香港文學》1985年1至7期。
(12)魯柏的五百字專欄《雜碎》剪報,是貼在侶倫親筆簽贈江河的《都市曲》上的,〈林風與林鳳〉約寫於一九八九年。
(13)侶倫1930年發表散文〈向水屋〉,並把自己的居所定名「向水屋」。
(14)見〈我的日記〉,《無名草》(香港虹運出版社,1950)頁25。
(15)〈想起一個除夕〉,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205。
(16)見〈關於蕭紅骨灰遷葬〉,載《向水屋筆語》(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101。
(17)同(15)。
(本文轉載自許定銘編《侶倫卷》,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十二月初版)
許定銘簡介:常用的筆名有陶俊、苗痕、午言、向河等,一九四七年生的廣東電白人,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的愛書人,從事寫作近六十年,早年埋首於新詩、散文及小說的創作,近二十年專注於「書話」的評介,其內容以中國現代文學及香港新文學的研究為主,旁及台灣及南洋方面的作家和作品。
有關書話的著述,已出版的有:《醉書閑話》、《書人書事》、《醉書室談書論人》、《醉書隨筆》、《愛書人手記》、《醉書札記》等十多種。他從事教育工作40年,開書店20年,畢生與書結緣:買、賣、藏、編、讀、寫、教、出版,八種書事集於一身,花甲以後自號「醉書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