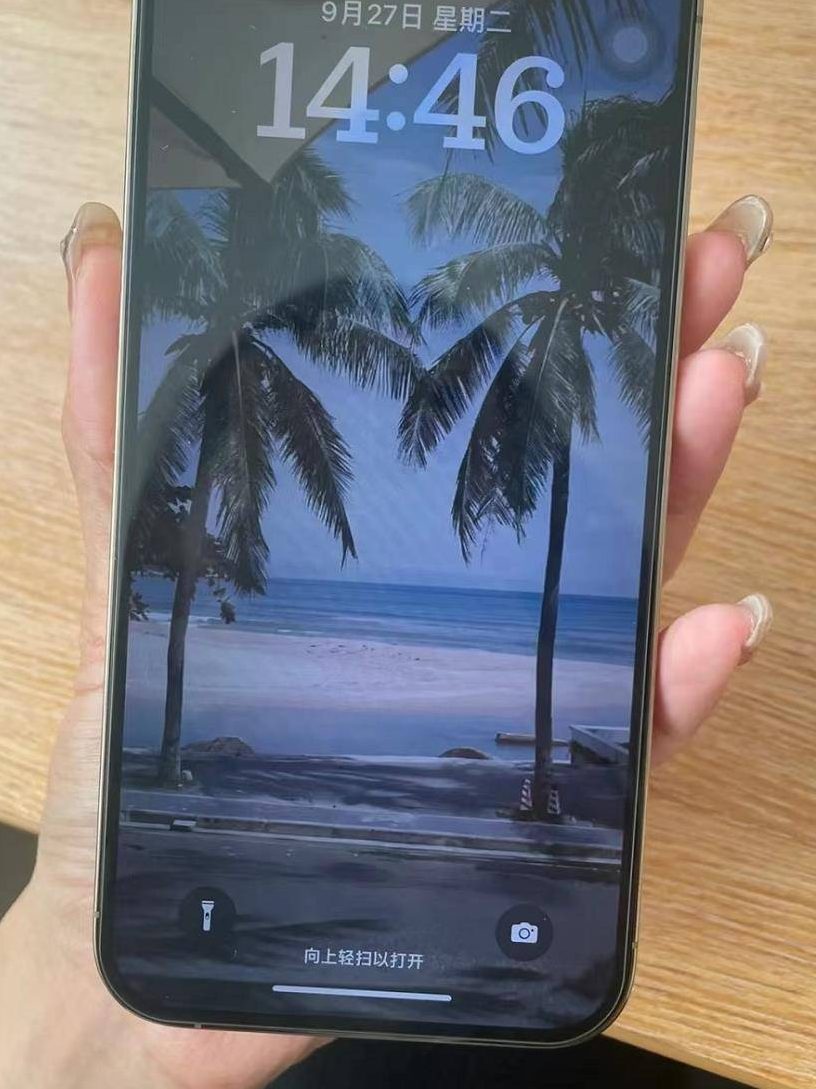淵 懿

維度二: 示眾的材料
溫柔敦厚、善良勤勞、堅韌頑強是與「國民性」批判相對的另一個書寫面向,也是蕭紅對魯迅「國民性」書寫的拓展和延伸。當我們把關注《呼蘭河傳》的視角,從看客的群像轉移到示眾的材料,也就是某一個體身上,會看到蕭紅所觀察和書寫的底層民眾在艱難生存環境面前,除了對烙印在身體內的國民劣根性進行批判,更多的是以平視,甚至與人物進行互動的姿態書寫「國民性」的溫情和積極面向,「我覺得自己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要悲憫我咧;悲憫只能從上到下,不能從下到上,也不能施之於同輩之間。我的人物比我高」。
既然本文提出蕭紅對「國民性」書寫積極面向的開掘,那麼便有一個問題需要釐清:為甚麼蕭紅在《呼蘭河傳》前五章所書寫的「國民性」與魯迅如出一轍,是延續對國民劣根性進行無情鞭撻和深刻批判,而最後兩章,卻對「國民性」的書寫卻在批判中逐漸轉向了溫情和積極面向呢?蕭紅的生前好友蔣錫金在一篇〈蕭紅和她的《呼蘭河傳》〉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這部小說「大約開始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讀了她寫的部分原稿……讀了第一章,又讀了第二章的開頭幾段」。通過查閱蕭紅生平年譜可知,當時的蕭紅剛從上海撤離到武漢,就已經開始著手創作《呼蘭河傳》。而《呼蘭河傳》的最後完稿時間是一九四○年一月,當時已身處香港異鄉的蕭紅重疾纏身,後因庸醫誤診,導致病情雪上加霜。雖然蕭紅初到香港便以其在文學創作的成就和知名度而很快被香港文藝界熱情接納,但總體來說,身處香港的蕭紅是寂寞的。與曾經共患難的蕭軍分離,又和一個並不怎麼合意的端木蕻良結合,此時的蕭紅與武漢時期的心境大相徑庭。《呼蘭河傳》最後的章節便是在對家鄉無限懷念和深情回望中完成的。正如她在《呼蘭河傳》的結尾中鄉愁滿滿地寫道:「以上我所寫的並沒有甚麼幽美的故事,只因他們充滿幼年的回憶,忘卻不了,難以忘卻」,葛浩文亦認為《呼蘭河傳》「是背井離鄉者思鄉情緒下的產物」。出門在外漂泊的遊子,在逆境中難以忘懷,揮之不去的便是對故鄉的深情回望和懷念,作為呼蘭河兒女的蕭紅,她不希望自己的悲劇重演,也不願再看到從呼蘭河出走的「娜拉」終究以悲劇收場。她希望自己的家鄉在馮歪嘴子、王大姑娘這樣堅強的生命和韌性的力的推動下能夠與幾千年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進行正面撞擊,給這個愛之恨之的家鄉帶來真正轉變。《呼蘭河傳》最後一章描寫馮歪嘴子的孩子:「大的孩子會拉著小驢到井邊飲水了,小的會笑了,會拍手了,會搖頭了」,如此正面且積極地對孩子描寫,在蕭紅以往的作品中是很少見到的,這其中便蘊含著蕭紅對新生命所寄予的無限期望,這一點也可以從蕭紅同時期完成的《北中國》和《小城三月》中看出端倪。《北中國》所抒發的無疑是蕭紅悲涼的家國情懷,不過還要注意當時發生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蕭紅的弟弟張秀珂就在新四軍隊伍。弟弟張秀珂是蕭紅衝出家門後,唯一書信往來的親人,自上海一別音信全無,這一突發事件對於身在異鄉孤單寂寞的蕭紅來說,更加激起了她的思念之情。而在《小城三月》中,善良美麗的「翠姨」在與讀書人的短暫接觸中不僅呼吸到自由氣息,也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真愛,最終因無法獲得自由的愛和幸福,用生命的隕落向傳統宗法社會表達她無奈但堅定的抗爭,而《小城三月》文中「我」的「家」是富裕開明的,冷酷無情的父親也變得頗有人情味,「翠姨」雖然懵懂懦弱,但也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反抗之心,這樣的書寫在蕭紅過去的作品中亦是不曾見到的。葛浩文在《蕭紅傳》中引述其好友與蕭紅的談話中提及未完成的《馬伯樂》第三部,蕭紅說:「我很遺憾,還沒有把那憂傷的馬伯樂,提出一個光明的交代」。從以上分析看出,這一時期的蕭紅作品,作者在主觀上希望構建出一個光明和抗爭的結尾。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出蕭紅在《呼蘭河傳》中的「國民性」溫情、積極面向的書寫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此時此景的水到渠成。
以上對蕭紅《呼蘭河傳》小說文本從「國民性」的批判到溫情和積極面向書寫的轉向,也僅是從獲取的相關資料和文本解讀做出的分析,亦未必是絕對定論,在此作為一種分析呈現。
一、啼笑皆非的有二伯
阿Q這個底層人物的形象隨著魯迅《阿Q正傳》於一九二一年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而走入讀者心中。阿Q之所以能在極短時間眾人皆知家喻戶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阿Q如呼蘭河城永遠不能填平的大泥坑,折射出潛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小我,擊中了每一個中國人的軟肋。
《呼蘭河傳》中的人物或多或少,或隱或現地投射著阿Q的不散魂靈,蕭紅對骨子裏透著和阿Q一樣「被人打了就是被兒子打了」的人物描寫和塑造,並不是對魯迅筆下阿Q的簡單複製和模仿。與魯迅振臂吶喊的辛辣尖銳諷刺批判不同,蕭紅筆下的「國民性」書寫除了無情批判,還多了幾分人性的「美」和「善」的觀察,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喜歡被對方稱呼自己為「有二掌櫃」的——有二伯。可以說有二伯既是圍觀的看客,又是示眾的材料,他的身上除了「國民」劣根性的可恨可悲,還有發自本性的自尊廉恥和被關心尊重的人性訴求。
有二伯是「我」這個地主家一個地位十分低下的長工,他唯一的財產就是一個髒兮兮的枕頭和一牀破爛被褥。孩子們向他扔石頭,我家的老廚子也不拿正眼瞧他,比他小三十多歲的父親會把做了錯事的他打得頭破血流,總之沒有人看得起他,也沒有人在意他的內心感受。
有二伯身上和呼蘭河的眾看客一樣,深深烙印著對生命冷漠的「國民」劣根性。當他參加完團圓媳婦的葬禮後,他毫無悲痛之感,滿腦子回味的是「酒菜真不錯……雞蛋湯打得也熱乎」。至於團圓媳婦的死和自己沒有任何關係,也不會產生任何同情和憐憫,酒足飯飽便心满意足,因為在他心中「人死不如一隻雞」。
阿Q雖說混得不怎麼樣,晚上也還有個土谷祠落腳,有二伯卻連個固定睡覺的地方也沒有,只好今天住粉房,明天在小豬官的炕頭梢上湊活一晚。然而,貌似對甚麼都可以接受,對甚麼都不在乎的有二伯對別人如何稱呼自己卻是十分在意。只要聽到有人叫自己的乳名「有子」,便「氣得像老母雞似的,把眼睛都氣紅了」,一聽見「有二爺」、「有二東家」、「有二掌櫃的」,便笑逐顏開,這和與趙秀才同姓便沾沾自喜的阿Q有異曲同工之妙。
然而,蕭紅對有二伯的人物刻畫並未到此為止,而是往前推進一步。正在儲藏室翻箱倒櫃的「我」與有二伯不期而遇,被撞破的有二伯沒有擺出一副不認賬的姿態找理由搪塞,而是臉紅冒汗,嘴唇顫抖,這是因為他的心底仍然留存自尊自愛和廉恥之心。「我」沒有揭發他,他也沒有告我的狀,我們不僅因此達成了保密協議,還建立了良好的跨越年齡的「友誼」。孔乙己滿嘴的竊書不算偷,但最終因為偷竊被打斷了雙腿,有二伯卻因偷竊和「我」這個小主人拉近了彼此的關係。後來有二伯偷竊銅酒壺、洗澡盆等等,都被老廚子當做飯後茶餘的笑料。蕭紅沒有忘記在文中對有二伯的「偷竊」行為進行淡化處理,比如:有的東西是老廚子偷的、有的是我偷偷拿取玩的、有的忘記放在哪裏了,大家都習慣地賴在有二伯身上。
有二伯雖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個被嘲笑,被戲弄的小人物,但是與筆下人物平起平坐的作者蕭紅,用女性的細緻和生命體驗,觀察到有二伯作為一個人也有其可愛之處:他有時也疼愛「我」這個小姪女,帶著「我」去公園走走。除此之外,有二伯還有被尊重和被關心的需要。當有東西吃的時候,必定要問問他吃不吃,否則就要生很大的氣。其實,真的給他送過去,他便客氣起來,「你二伯不吃這個,你們拿去吃吧」,有二伯只是需要這樣一個被問候,被關心的感覺。就如有二伯一個人的時候,會和天空的雀子說話,也會和大黃狗談天,這其實是孤獨寂寞的有二伯在找尋一個傾訴的對象罷了。有二伯還常常提起日俄戰爭時期,自己一個人冒著被砍頭的危險給老東家看家護院,不外乎就是告訴大家,自己沒功勞也有苦勞,但這似乎沒有引起東家的額外關顧,於是心情不爽利的時候有二伯不是鬧上吊就是鬧跳井,可總是虛驚一場,白嚇唬人,他所要爭取的不過是對他的重視和基本尊重。
蕭紅對有二伯這個底層小人物的溫情關照,是蕭紅對所繼承的「國民性」書寫的突破和豐富。蕭紅寫作的時代大背景,已經不是魯迅的清末明初,如果還用極端的「國民性」批判塑造筆下人物,顯然有點不合時宜。有二伯這個人物的如此鋪排,也是蕭紅把呼蘭河這個生她養她的故園已經構建為自己最為惦念的精神家園,她不想讓她的精神家園總是充滿負面戾氣的灰暗色調。
還有一點就是有二伯的抱怨和滿腹牢騷:「你們家裏沒好東西,盡是些耗子,從上到下,都是良心長在肋條上」,有文論將這些行為解讀為有二伯身上的反抗精神,本文認為這樣的分析顯得牽強,如果有二伯真有反抗,至多也是對自身命運不公的反抗,陳世澄則認為:「有二伯和阿Q一樣,都對統治階級有過反抗,但卻都是消極的反抗」。
如果說有二伯的抗爭與我們所理解的對封建統治的反抗似乎還有距離,也顯得牽強,那麼《呼蘭河傳》的最後一章所推出的兩個人物——王大姑娘和馮歪嘴子便是用生命和行動在向整個封建道統體制進行的真正抗爭。
二、向死而生的執念
1、衝破禮教的王大姑娘
《生死場》中的金枝是自願嫁給同村男子成業的,但金枝的婚姻與其說是衝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如說是首先被男子婉轉的口笛吸引,接著不諳世事的金枝又稀里糊塗偷吃禁果未婚先孕,最後沒有任何退路的金枝不得已踏進了男方的家門。「管他媽的,活該願意不願意,反正是幹啦」。從這句成業的混話中便知道這個稀里糊塗走出家門的「娜拉」,不可能獲得她心中想要的幸福生活。
魯迅筆下敢於衝破封建枷鎖的「娜拉」出走之後有三條路:墮落、回家、餓死,因為娜拉終究無法解決經濟獨立的問題。其實,反抗家族包辦婚姻,義無反顧衝出家門的蕭紅,在半生艱難跋涉中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為錢而困。
《生死場》是蕭紅創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金枝自然是蕭紅小說塑造的第一個敢於走出家門的「娜拉」,這位沒有任何經濟自主能力的「娜拉」,最終沒有跳出魯迅對出走娜拉所給出的路徑。然而,經歷了離婚、再婚,從異鄉再到異鄉的蕭紅,從《呼蘭河傳》中再次出走的「娜拉」,卻是完全不同的結局。
《呼蘭河傳》中的「娜拉」——王大姑娘還沒有嫁人的時候整個院子的街坊鄰居個個都誇她長得漂亮有福相,「這姑娘將來是個興家立業的好手」,然而當她的婚姻大事沒有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規矩去做,而是私下自作主張嫁給了呼蘭河門不當戶不對開磨坊賣切糕的馮歪嘴子。於是,曾經聲音響亮悅耳、辮子水滑油亮,雙眼神采奕奕,人見人誇,美麗得像一棵「大葵花」的王大姑娘在看客眼中便完全變了樣:說話聲音出奇的大,長得也不秀氣,力氣還比男人大,連誰都敢欺負的有二伯也一臉嫌棄地說:「長的是一身窮骨頭窮肉,那穿綢穿緞的她不去看,她看上了個灰禿禿的磨官」。王大姑娘曾經有多少優點,如今便有多少缺點。街坊鄰居們對她曾經有多少讚美,如今便有多少惡毒的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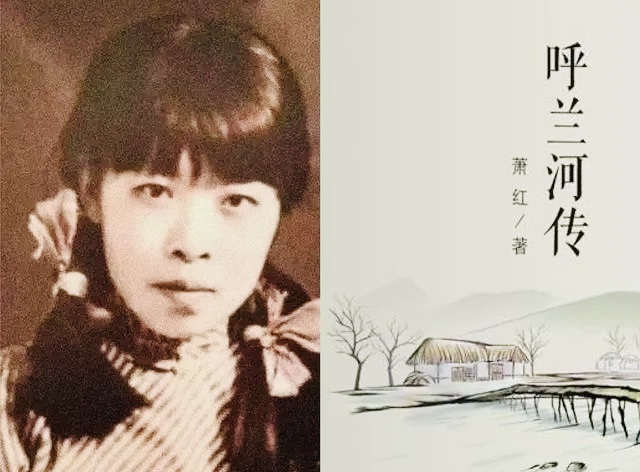
王大姑娘衝破千年的封建禮教,選擇了自由戀愛的馮歪嘴子,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家徒四壁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更重要的是她實現了婚姻的自我做主,她的內心充盈著幸福。然而,呼蘭河民眾在千年沿襲的傳統文化中按部就班的生活著,將每個人都規矩在封建傳統的強大羽翼之下,如今,卻被一個王大姑娘捅了個大窟窿。王大姑娘如此大逆不道,壞了祖宗規矩,呼蘭河那些本無惡意但被封建倫理道德世代荼毒的鄉民是絕不能接受的,更讓這些看客不能原諒的是王大姑娘居然未婚先孕,這簡直就是對封建禮法的褻瀆。
王大姑娘躺在炕沿上的瓦盆都能凍裂的碾房坐月子。然而,她帶到這個世界的新生命不僅沒有得到祝福,反而迎來掌柜太太的破口大罵:「破了風水了,我這碾磨房,豈是你那不乾不淨的野老婆住的地方 」,掌櫃太太罵完覺得還不夠解氣,又把蓋在剛出生孩子身上的麵口袋拿下來。接下來的日子,「全院子的人給王大姑娘做論的做論,做傳的做傳,還有給做日記的」。王大姑娘的笑聲消失了,一盆火似的臉變得清瘦了,也白了許多。在楊老太太、周三奶奶們的風言風語中,在呼蘭河鄉親鄰居的蔑視和詆毀中,王大姑娘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蒼白,一吋一吋地矮下去,最終王大姑娘在難產和閒言碎語的圍剿中悄然離開了這個世界。
《呼蘭河傳》有兩個媳婦死亡,一個是被迫成為團圓媳婦,從笑到哭再到無聲的死亡,一個是將幸福和微笑藏在心底,在流言蜚語中選擇沉默,最終因個人能力無法抗拒的外力離開了這個世界。這樣兩個通過「被動」和「主動」結婚,最後「被動」和「主動」死亡的建構,深刻揭露了呼蘭河民眾對鬼神無知崇拜和對鮮活生命逝去的麻木冷漠。
王大姑娘這樣一個生活在偏僻小城的弱小女子,沒有受過任何教育,更談不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然而她卻大膽地做出了與大眾內心完全相悖的決定,她是在以微薄之力向整個腐朽封建道統進行抗爭。也許這樣如蚍蜉撼樹的抗爭近乎無意義,但王大姑娘敢於衝破封建枷鎖的勇氣和精神,便是蕭紅對「娜拉」這個形象所賦予的新的內涵。
《呼蘭河傳》中,蕭紅對小團圓媳婦和王大姑娘這樣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對「國民性」書寫的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補充。一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的女性傳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因此自古以來的女子發聲,基本是藉助男性作家得以實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成長起來的知名女性作家有冰心、丁玲、盧隱、蘇青、石評梅和張愛玲等,但真正繼承魯迅進行國民靈魂改造的女性作家亦是鳳毛麟角,從這個角度分析,蕭紅的創作價值和意義仍然有繼續開掘和探索的空間;二是在同時期女作家中,蕭紅的命運和情感經歷是最為悲慘和坎坷的,當作家將自我體驗投射到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苦難,便不是以往男性視角下的隔靴搔癢,而是力透紙背,深入骨髓。特別是那些殘害團圓媳婦和王大姑娘的看客們,居多就是女性自己,這更是對千年封建禮教殺人於無形的控訴;三是通過一個沒有反抗婚姻的小團圓媳婦結局,和一個敢於和命運抗爭,突破循規蹈矩的陋習,選擇自主婚姻的王大姑娘所形成的鮮明對照,讓依舊被封建道統所束縛的廣大女性看到,只有放下沉重的精神枷鎖,突破封建宗法禮教的千年牢籠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內心自由和幸福,路就在每一個人的腳下,這也是對魯迅所言「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的回應。
2、我不要「香爐」和「燭台」
魯迅《故鄉》中的少年閏土曾經是「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長大成人後,那個曾經手捏鋼叉月下捉猹、雪中設伏捕捉鳥雀,以及心裏裝著無窮無盡稀奇事的閏土早已蕩然無存。「先前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頭上是一頂破氈帽……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卻又粗又笨而且裂開,像是松樹皮了」。再次見到闊別多年的魯迅,寡言少語的閏土只能在憨厚的笑臉中勉強擠出兩個字——老爺。生活景況苦楚無奈,彷彿石像般的閏土最終選擇了「香爐」和「燭台」,這也意味著他將沒有希望的未來寄託於更加虛無的宗教。
蕭紅所構建和閏土一樣窮苦的馮歪嘴子卻在艱難和困苦的生活面前拒絕低頭,他雖是悲慘,但通過自食其力獨自頑強扛起生活重擔。他與王大姑娘通過自由戀愛結合在一起,還生了個兒子。雖然王大姑娘在生第二個孩子時難產而死,但馮歪嘴子頂住來自八方的閒言碎語將兩個孩子拉扯成人,彰顯了生命的頑強。
馮歪嘴子是一個典型的窮苦人,但整天都是樂呵呵的,還待人和善,充滿愛心,對還是小孩子的「我」,也是愛心滿滿,送「我」黏糕吃是常有的事。勤勞質樸,對未來充滿信心的馮歪嘴子一年四季在打梆子、拉磨的忙碌中度過。
突然有一天,馮歪嘴子的炕上不僅有了個女人,女人的被窩裏還有個孩子。在這個夫權至上,充斥著大男子主義,男人打女人是天經地義的呼蘭河城,馮歪嘴子卻非常難得的懂得疼愛自己的老婆。他從不讓王大姐幹任何粗重活兒,有點小積蓄便買來雞蛋給她補身子,一日三餐粗茶淡飯,他們是快樂和幸福的。
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私定終生給這個生活單調無趣的小城平添了難得的談資,畢竟小團圓媳婦死了有些日子,看客們也寂寞了一段時間。如今,王大姑娘的醜事一出,真是又可以熱鬧開心一番了。
儘管馮歪嘴子告訴祖父自己成家了,但是這個跨越封建道統的家,是無法獲得呼蘭河鄉民認可的。所激發的只是楊老太太、周三奶奶們超乎尋常說三道四的想像力。等著看笑話的好事者更是整夜守在馮歪嘴子窗口,為的就是探聽最新消息,「好作為第二天宣傳的材料」。有人看見他家炕頭有一段繩子,就傳他要上吊。馮歪嘴子買來一把切菜刀,就放出他要自殺的消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馮歪嘴子既沒有上吊,也沒有自殺。面對掌櫃太太大罵「你沒有臉,你若有臉你還能把個野老婆弄到大面上來……你趕快給我滾蛋」,頑強的馮歪嘴子沒有被這些流言蜚語和諷刺挖苦所擊倒,沒有因此而消沉,向生活低頭,向命運屈服,如閏土般拜倒在「香爐」和「燭台」所構建的神靈腳下,而是直面所有壓力,默默扛起生活重擔,迎著庸眾的冷言冷語堅韌向前。
王大姐不幸在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因難產而喪命,那些原本就見不得馮歪嘴子過好日子的看客一邊忙著四處打聽最新動態,一邊幸災樂禍地猜測著馮歪嘴子的末日何時到來。這反而更加激發出馮歪嘴子潛藏在脛骨之下的精神和力,更加頑強地面對生活的殘酷。他照常起早貪黑地磨粘米、賣黏糕,「他在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們都用絕望的眼光來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經處在了怎樣的一種艱難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經完了。他沒有想過」,正如矛盾所言,「馮歪嘴子『像最低級的植物似的,只要極少的水分,土壤,陽光——甚至沒有陽光,就能夠生存了』」。這個以馮歪嘴子和他的兩個鮮活的孩子所散發的生命張力所構建的「國民性」正向積極書寫。
馮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封建思想瀰漫的呼蘭河這樣的偏遠小城,能夠突破世俗眼光,透過自由戀愛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即使在命運不測的災難面前也能夠樂觀頑強面對,用原始生命的力積極生活下去,這是他用生命的韌性對現實和封建腐朽制度的反抗。
結 語
本文在這一節主要分析討論的是「《呼蘭河傳》『國民性』兩個維度」中的「示眾材料」,也就是個體的「被看」。具體是從小說文本中的「有二伯」、「王大姑娘」和「馮歪嘴子」三個底層人物切入,分析蕭紅在繼承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同時,通過獨特女性視角和日常生活敘述,對底層螻蟻般民眾身上所散發的溫情、堅韌和頑強的國民性所進行的關照。
愛慕虛榮,人性未泯:作者對有二伯這個懦弱自卑的小人物除了批判,更多的是充滿悲憫和同情之心。看到有二伯偷竊而不說破,有二伯大哭大鬧不外乎只是想獲得別人對自己的小小關心。他性情古怪,對現實不滿,但又缺乏改變現實的勇氣和信心,唯有將氣撒在沒有生命的小石頭小磚塊身上,這與阿Q「兒子打老子」的精神勝利法和欺負更加弱小的尼姑有本質區別。特別是有二伯小偷小摸被發現後的面紅耳赤,以及被尊重的人性基本需求,都是蕭紅對這個底層人物溫情書寫的體現。
衝破禮教,敢於自主:一個沒有任何文化知識的王大姑娘,卻和「娜拉」一樣走出家門,衝破封建牢籠,打破媒妁之言,自主嫁給誰也瞧不上,賣切糕的馮歪嘴子,這是對封建體制的最有力衝擊。雖然這種個體衝擊的實際作用未必能掀起多大風浪,但是在那些楊老太太、周三奶奶們閒言碎語的傳播中,這種敢於追求內心自由和幸福的行為給那些和她一樣的女子做出了榜樣,這對閉塞落後的農村來說,沒有比這可以起到更加直接和深刻的影響。
樂觀向上,頑強堅韌:面對生活的困境,馮歪嘴子表現出勤勞善良,勤儉節約,樂觀向上的品性。面對命運不公和亡妻的不幸,他沒有向生活低頭,而是激發出本能的生命韌性和不屈的反抗精神。馮歪嘴子所表現出的人性自我覺醒,是蕭紅在繼承魯迅「國民性」批判的同時,對「國民性」積極面向書寫的拓展和延伸,讓廣大底層民眾在這樣的書寫中,真正看到這個民族的未來和希望所在。
落後保守、愚昧冷漠、麻木自私是上世紀二十年代舊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真實圖景。呼蘭河這個偏僻小城如一面鏡子照射出普羅民眾的百態人生,也折射出舊中國的「國民靈魂」。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呼蘭河傳》成書於一九四○年,當時中國時代大背景是抗日戰爭壓倒一切,由左派控制的文藝戰線所創作的主旋律,都在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鼓與呼,同是左派陣營的蕭紅遠在香港所創作的《呼蘭河傳》是一個異數,也是蕭紅於無聲處對中國現代文學在特殊創作時期炸響的一聲驚雷。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一文中,對覺醒出走「娜拉」的未來充滿悲觀,認為「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蕭紅用文字構建的「力」宣告,她這個出走的「娜拉」,即使身體倒下去,精神依然挺立。
已進入數字化地球村的當下,面對無處不在無縫不鑽的數字黑科技,「國民性」書寫和研究不僅沒有落伍反而更加彰顯其重要性。不同的是,那些曾經圍觀的看客如今紛紛躲在幕後,重塑為一個個幸災樂禍,殺人不眨眼的「鍵盤俠」,用子虛烏有的惡意揣測,用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煽動,用身敗名裂千夫所指的狂歡共同建構「網暴」和「以暴止暴」的現代無聊麻木冷血看客形象,將一個個用流量和所謂正義推上風口浪尖的「被看者」送上猙獰的絞刑架。正如王科、牟維珍所言:「這才是寫出中國人民生的堅強、死的掙扎的蕭紅,猛烈鞭撻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蕭紅,深刻揭露民族痼疾、國民根性的蕭紅」。
參考書目
一、衣俊卿 、春良、李曙光等編:《蕭紅全集》,黑龍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二、葛浩文:《蕭紅傳》,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三、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五年。
四、季紅真:《蕭紅全傳 呼蘭河的女兒》,北京:現代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淵懿簡介:本名袁疆才。西北邊陲呼喊著跌落人間,隴上人家馬不停蹄野蠻生長。當下,垂釣香江,文字覓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