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
回台灣和家人過年,返回香港時,因為新冠肺炎的影響,機場十分冷清,來的路上搭乘捷運,整節車廂只有我一個人,通關快速,我戴著口罩,依防疫專家的提醒洗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機上乘客不多,除非是偕伴同行的旅客,每個人的座位都保持著相當的距離,異常安靜,連咳嗽聲都小心翼翼地不曾聽聞。因為航班減少的緣故吧,飛機準時起飛並準時降落赤鱲角機場,這麼多年,是我第一次置身人煙如此稀落的香港國際機場,原本的繁忙匆促是此時寂寥的上一頁,約莫也是下一頁,現下的安靜是其中一小段換頁的空檔,但是身陷其中的人心裏雖然明白,卻依然不免擔憂焦慮。

新冠肺炎的影響,機場十分冷清。(資料圖片)
曾聽香港朋友說,香港多老鷹因為港口多老鼠,為老鷹提供了足夠的食物,果然港邊常見老鷹盤桓,十幾年前香港港口貨運量曾是全世界第一位,如今先後被新加坡和上海超越,但是依然擁有驚人的數量,所以鼠患猖獗,有其現實因素,即使老鷹多,依然無法阻止老鼠從港口區進入住宅區安下身來。一八九四年,香港因鼠疫橫行致使三分之一的人慌慌撤離,《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記載病例死亡總數是二五五二人,然而這一數據是在東華醫院或「醫船」(隔離船)上由港英政府確認的死亡數,許多人認為沒有經當局確認、統計的鼠疫患者和死亡病例要遠遠多於二五五二人。更令人憂懼的是此後三十年間,鼠疫幾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現,兩萬多人因此死亡。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她名叫蝴蝶》中便描寫過這一場鼠疫,小說裏黃得雲依母親交代外出抓藥,結果被人口販子綁架至香港畢打碼頭,本欲賣為婢女,偏偏遇上遊行示威反對蓄婢,人口販子於是將把她賣到水坑口大寨當妓女。一八九四年端午時節鼠疫發生,人心惶惶,恐懼鼠疫又不得不到疫區執行任務的亞當尋求肉體短暫的慰藉,因此遇到黃得雲。
香港鼠疫嚴重時,來自福建漳州與泉州的商人大多攜家人返回老家,有報導稱,「港中太平山現已圍住,擬將屋宇改造,並展闊街道」,港英殖民政府因太平山疫情嚴重,欲以「屋宇改造」為名,把「舊太平山」改造成「新太平山」,令在港華人恐慌和仇恨的情緒升高,施叔青的小說中火燒太平山疫區的前一天,亞當僱轎子將得雲接至跑馬地的成合坊的唐樓安頓,但是中秋過後,當鼠疫逐漸趨緩,亞當意識到自己終究希望伴在身邊的是一位白種女性,因為疫情開展的一段纏綿情與慾自然也未能圓滿告終。

香港鼠疫嚴重時, 來自福建漳州與泉州的商人大多攜家人返回老家。(資料圖片)
提到與瘟疫相關的作品,許多人會想到加繆的小說《鼠疫》,《鼠疫》中里厄醫生離開診所,在樓梯間第一次發現死老鼠時,預示著阿赫蘭這座城市即將陷入傳染病的恐慌。隨著疫情愈演愈烈,被封了的城裏上演著生離死別,有人設法出逃,但也有加繆書中描寫一直堅持在第一線的里厄大夫,以及參與防疫志願隊的醫生護士們;有推諉卸責的政客,也有努力營救城市的政治家;有加入志願義工的外地記者,也有發國難財的商人。人的身份不同,但是當瘟疫盛行,社會地位在病毒面前其實是沒有區別的,區別的產生是來自每個人不同的選擇。原來時代地域不同,當傳染病出現人性還是相同的,不可預知的疫情發展下不同抉擇,匯聚在小說字裏行間,讓讀者看見了人性的各種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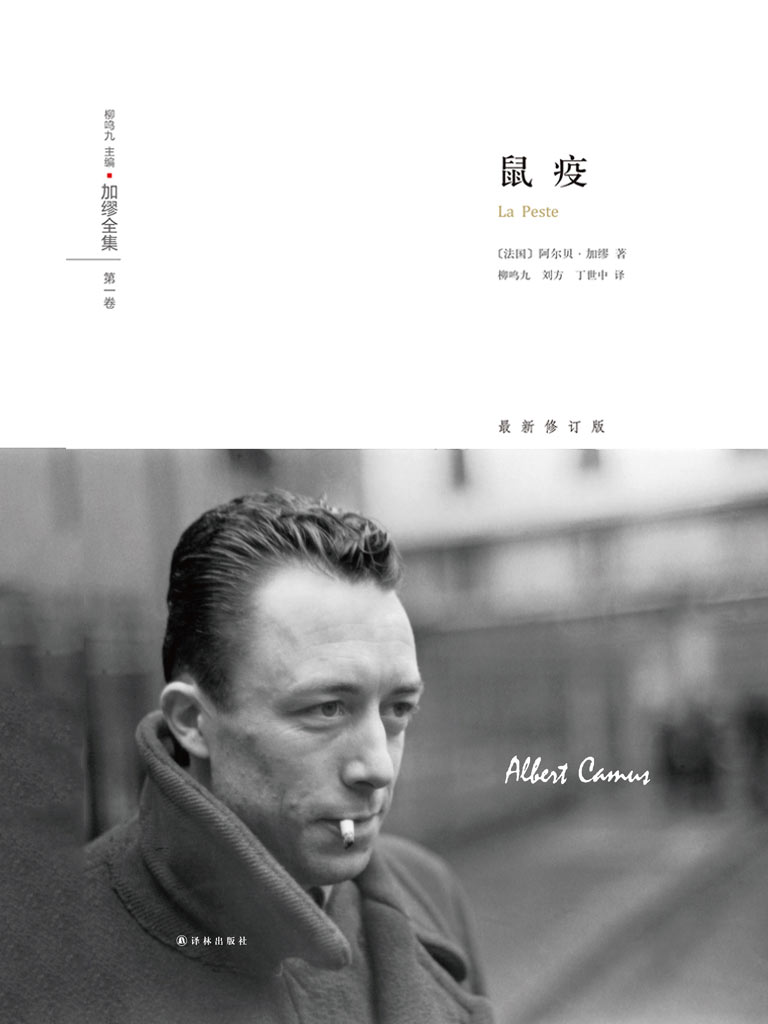
加繆小說《鼠疫》。(資料圖片)
人類歷史上,鼠疫第一次大暴發是在西元五四二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是歐洲中世紀有名的「黑死病」,第三次是十九世紀末從中國雲南開始,最終影響全球,施叔青筆下的鼠疫便是這場傳染病中的一環。遲子建的《白雪烏鴉》寫的則是其後發生在哈爾濱的鼠疫事件,一九一○年十月中國東北滿洲里發生鼠疫,十一月傳至哈爾濱,疫情如決堤般蔓延,東北平原之外,還波及了河北、山東。和新冠肺炎蔓延影響下同樣的出現了兩個關鍵詞:口罩和封城,《白雪烏鴉》裏寫道:「女人們接著做口罩去了。她們每做好一隻,就往紙箱丟一隻,像放飛雪白的鴿子。只是這些鴿子都折了翅似的,飛不起來。」飛不起來的折翅透露出絕望,佩戴口罩,是當時看來可行的防疫方法,可是口罩數量不足,小說裏傅百川便利用他的綢緞莊,在原有的縫紉機之外,又添置兩台大量加工口罩,傅家甸兩萬多人一周之內幾乎人人都有口罩了。但是這還不足以阻絕疫情,於是軍隊將傅家甸封了起來,封城後的傅家甸被劃分為四個區,以居民佩戴臂章顏色區分為:白、紅、黃、藍四色,分到紅色證章的人最高興,他們覺得紅色喜氣;領到黃色的人,因為黃象徵富貴也感快慰;拿到藍色的人擔心這是天空的顏色,是否預示著自己快要升天了?而白色是喪葬時用的,就更不吉利了。面對不可掌控的傳染病,人們的無奈無知無力益發凸顯,人為的顏色區隔也成為恐懼中的徵兆,猶如為什麼這個人感染了那個人沒,為什麼這個人痊癒了那個人卻病故了的疑問。

大排長龍買口罩。(資料圖片)
離台前,香港的新聞報導便看見為買口罩排起的長長人龍,台灣則實施所謂口罩實名制。回想春節後,一開始官員說防疫一定要勤洗手和戴口罩,台灣的口罩庫存數量足夠。接下來很快就發現其實根本不夠,又改口無症狀的人不必戴口罩,但是接著傳出有無症狀的新冠肺炎患者在不自知的情況下往人群散播病毒,人人自危結果使得醫療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口罩都不夠用。我想起十幾年前的SARS,當時許悔之曾經在二二四期的《聯合文學》中寫道:「這是一個口罩變成禮品的年代,這是一個未知而憂懼的年代,這是人與人距離最遠的年代……有一天,當我們回過頭來看今日的一切,會發現,我們每個人都坐了牢,不管是『居家隔離』的牢,還是心牢;所有人性純善與醜惡的質素和行為,都在SARS這樣的臨界情境下,一覽無遺。」當時許悔之稱SARS將是人類在廿一世紀的集體創傷,那一期的聯文還特別企畫「從圍城中飛出去──SARS年代看文學裡的『疫病』」專輯,如今的新冠肺炎是否又是另一次集體創傷,而二十一世紀才過了五分之一,重複發生的疫情讓我們學到了什麼?
二月七日蘋果日報上張曼娟也在她的專欄中提及當年的SARS:「在搶口罩的風暴中,我想起了當年的SARS。那時在大學教書,每天進入校園都量體溫,而後在身上黏一張有色貼紙,表示自己是安全無虞的。除了吃飯、喝水,口罩都不取下來。哪怕是戴著口罩,與人交談時也要保持安全距離。」會不會人與人本就該維持著距離,不論我們是否意識到病毒就在身邊潛伏。
韓麗珠二月二十六日《自由副刊》上刊載的〈遺忘〉中寫著:「自然療法的醫生說,肺炎的心理原因,是壓抑的話語無法表達,因為肺是掌管吸入和呼出氧氣的器官。而從SARS至武漢肺炎,就像一種未完全康復的舊病捲土重來,當年人們還沒有學會的,生活的方式、和土地與動物的關係、社群的關係以及脆弱的醫療系統,現在再次碰到相同的命題……」韓麗珠甚至認為要是人類在這一場病毒中滅絕,那麼就讓別的物種承繼地球。這樣的說法看在某些人眼裏或許嚴厲了些,但地球的確從來都不是人類所獨有,人類卻妄自想佔領掌控一切。
《聯合報》上看到研究疫病與人權的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劉紹華在中研院舉行「從中國的『後帝國』語境看疾病的隱喻與防疫:從麻風病談起」演講中談到新冠肺炎,她說台灣起初普遍稱該病為「武漢肺炎」,但這稱呼有污名化嫌疑並非好現象。她說,國際上並不是使用「武漢肺炎」,英文資料開始因為未有正式病名,曾以「Wuhan Virus」或「China Virus」稱此病毒,在世界衛生組織發現有污名化問題後,很快不再使用。劉紹華說,世衛組織將此疾病命名為「COVID-19」後,台灣許多地方包括官方也未正名。武漢肺炎只是一個名詞嗎?對部分人而言應該不只吧,即使瘟疫危急,意識形態依然作祟。
馬家輝則在二月十六日《明報》的專欄中指出了另一個觀察方向:「肺炎肆虐,百業蕭條,網絡企業的進帳卻暴漲急升,騰訊自是箇中代表。人人隔離,個個閉關,無一不變成『宅男宅女』,最方便的娛樂當然是打機睇戲之類,皆在網上進行,你的危,他的機,網絡巨子理應比其他人捐獻更多的善款和物資……」看到這,突然想起進入二十一世紀時千禧蟲也曾引起憂慮,而可以避開人與人直接接觸的網絡,何嘗沒有病毒感染問題,早在半個世紀前大衛傑洛德的科幻小說When H.A.R.L.I.E. was One中就描述了一個叫「病毒」的程式以及與之對戰的叫「抗體」的程式。一場疫疾,引發各種不同的觀察角度,多年前,武漢作家池莉曾寫過過一部中篇小說《霍亂之亂》,小說裡描寫武漢爆發霍亂疫情,醫護人員和市民何面對突發傳染疾病的故事,小說開頭這樣寫:「霍亂發生的那一天沒有一點預兆。天氣非常悶熱,閃電在遙遠的雲層裏跳動,有走暴的跡象。在我們這個城市,夏天走暴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池莉年輕時在湖北農村當知青,返城後從醫學專科到醫學院學習,同時就讀中文系,畢業後曾在武漢鋼鐵廠衛生署擔任過醫生,對於她的作品,我印象最深的是《生活秀》裏吉慶街賣鴨脖的來雙揚,以及《煩惱人生》裏分不到房遭老婆抱怨的印家厚,她的作品記錄了武漢三十年來的變遷,而其中唯一涉及醫學的就《霍亂之亂》,她在題記中寫道:「人類盡可以忽視流行病,但流行病不會忽視人類,我們欺騙自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或者說,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災難面前的表現都是相似的。我們希望文學作品可以長遠並廣泛傳播人性,感染讀者,情感上的感染,而不是病毒的感染,同時也希望人間的傳染病即使沒法完全杜絕,卻不至造成人們彼此隔離。
楊明簡介:現任珠海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散文及小說集《情味香港》、《酸甜江南》、《路過的味道》、《松鼠的記憶》、《別人的愛情怎麼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