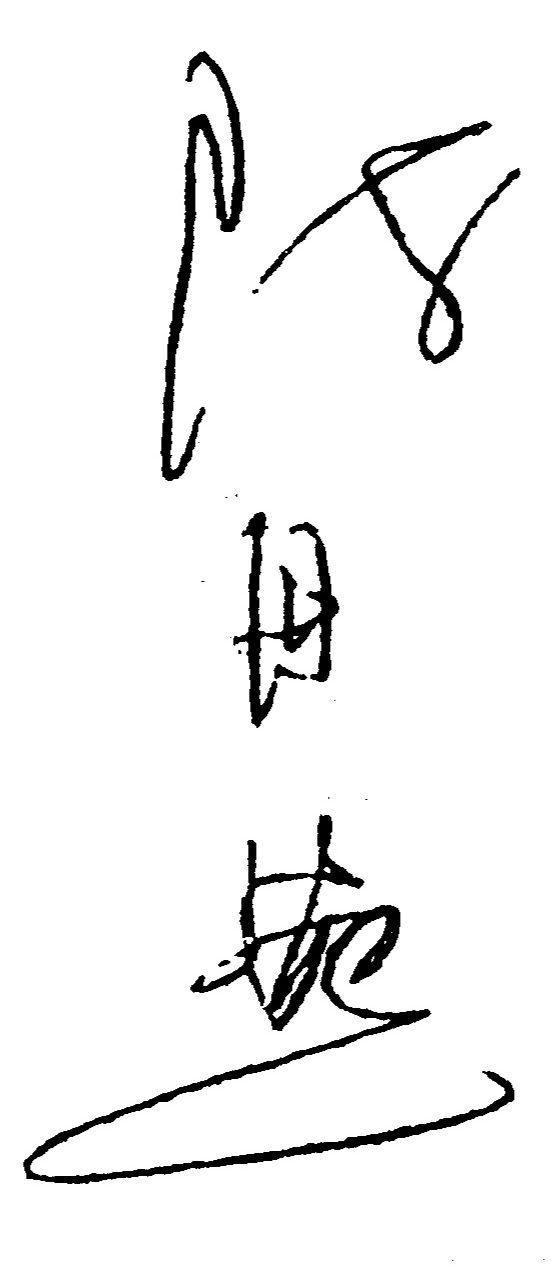 陳丹燕 上海著名作家
陳丹燕 上海著名作家
(一)燭台上的枯山水
在盧瓦河畔的奧維爾小鎮,從一八九○年夏天梵高度過生命中最後兩個月的小旅館門前出發,路過褐色窗欞的窗子,窗裏垂著白色細棉線鈎織成的花邊,古老的女紅。
拐上向上彎曲綿延的台階,路過梵高當年畫《奧維爾鄉村街道》是擱畫架的位置,畫家多比尼家的院牆下。如今那處豎了塊牌子,印著梵高的這張畫。在梵高眼裏,兩個穿白衣裙的女人向坡上走去,前頭還走著兩個穿黑衣服的女人。畫裏坡上的房子和樹,如今都還在。走上坡去,慢慢就看到有岔路的教堂了,它在三月末的雨中濕漉漉的,保留著梵高畫它時的姿勢。如今這幅著名的畫被印成小小的印刷品,謙卑地釘在教堂一角牆上,這叫我想起在愛琴海邊以弗所城外的瑪麗教堂廢墟正面的牆上,教皇釘上的一個小小十字架。

雨中一切都安靜,教堂裏沒有人,黃銅十字架上的耶穌瘦得出奇,不是通常教堂裏的樣子。但它放在梵高畫過的教堂裏,似乎就很妥帖。為梵高點燃了一支蠟燭,舉著四下一望,還是放在聖母像前的燭台前最心安理得。
聖母案前燭架上插燭的沙盤,被什麼人悉心清乾淨了,耙梳成了一小塊日本禪寺裏的枯山水。我獻給梵高的燭光照亮著這一小塊另一個人獻上的枯山水,寧靜悠遠的沙石世界,還有兩粒小小的白石頭,錯落地放在清燭油的小孔旁。一定是某人做到一半,特意到外面小廣場地上拾來的。
它讓我想起出嫁前的最後一個夏天,在自己房間裏讀歐文.斯通的《渴望生活》時的安靜。陽台門開著,一九八三年初秋的微風穿過有十字繡的床單吹進來,掃在玻璃台板上的厚厚的傳記上。那時我不記得這個小鎮的地名:盧瓦河畔的奧維爾。斯通描寫過的這條路,待三十年後,這個春天走在雨裏,他的描寫已經成了一小團模糊的影子。
我想枯山水出自一個日本人之手,也許感念梵高對日本畫的喜愛,也許對梵高的生活有著與靜觀一處枯山水一樣的心得。書上寫到梵高愛浮世繪,我那時還遺憾地想過,梵高一定沒看過宋徽宗畫的夢中大白鳥。我們這些東方人,遠游到法國小鎮上來,心甘情願被雨淋得濕漉漉的,就為自己幽暗記憶中的一個畫家。沙礫般微小而沉默,一根頂著火苗的蠟燭,一小塊犁出波浪的細沙,這是專心致志的致敬,即使是遲到一百幾十年,仍乾乾淨淨地完成。

我心中漸漸升起了一種奇靜的幸福感,帶著哀傷。這致敬真是遲到,比起畢加索,甚至莫奈生前享受到的榮譽來說。但卻更晶瑩純淨,毫無現世之利。作為一個欣賞者,我為自己的愛如此單純卻不朽感到幸福,也為愛得太遲,終於沒能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而不免要哀傷。
(二)杏花千朵萬朵
教堂後面有一條路,濕漉漉的小路。
這時突然看到一棵開滿白花的杏樹,那麼熟悉的,梵高式的扭曲,伸展,有渾然天成的優雅與和煦,正是我心中的梵高。
第一次看到這些杏花,是幾年前在初冬雨夜中的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地球北面的低地,下午四點一過,就墮入倫勃朗式的黝黯之中。沉沉雨夜裏,在博物館裏看到一株杏樹,白花盛放在淺藍色的天空下,溫存天真。原來它在這裏呀,就開在梵高墓地的旁邊,梵高麥田的對面。
想起自己年輕時代,總著迷於梵高引項長嘯的生命力,著迷他那扭曲盤旋的世界,橄欖樹銀色發亮的枝丫,絲柏的樹梢,星光,總是分叉起伏的小路和向日葵狹長的花瓣。但當我遠離青春之後,忽然在阿姆斯特丹看到這棵杏樹,白花盛放在充滿春季柔和水汽的淡淡藍天下,這才終於越過年輕時對熾烈向日葵的傾倒,為這滿枝真純打動,忽然才懂得了梵高在激烈中對世界無瑕的拳拳愛意。一個人心靈的果實,能在我年輕時打動我一次,在我不年輕時打動我第二次,對我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時刻。
阿姆斯特丹畫布上的杏樹在藍天下散發出來的愛意與溫存,奧維爾的這株杏樹在雨中新鮮得好像洗過澡的嬰兒,我現在會說,這才是梵高。
布滿雨窪的村路旁邊有條白漆斑駁的木板椅子,我遲疑著要不要坐上去。我想這是梵高路過時坐過的椅子,他在樹蔭下歇腳,聽正午時分有岔路的教堂那裏,鐘敲了十二響,有家的人該回去吃午飯了。這時他看到開花的杏樹,他心裏噢地叫了聲。沒人等他回家吃午飯,於是他就開始畫這棵杏樹了。我猜想著梵高遇見杏花時候的情形,一邊慢慢路過那條被雨打濕的椅子走向麥田。
村路上遺留著一種芬芳與和煦,那是梵高被標誌般的濃烈顔色掩蓋住的心靈柔軟純真之處散發出來的氣息。
(三)麥田裏驚濤駭浪
這就是最後兩個月裏梵高總是來畫畫的麥田。杏樹在泥濘小路旁望著它,守著它,一百幾十年。
三月底杏花開放時,麥田裏的小麥剛剛灌漿,還是一團青綠,看上去好像一隻正在烤熟中的圓麵包,又軟又香。下著雨,很安靜,遠處一動不動的大樹,在梵高的畫中它們是些黑呼呼的陰影。但是此刻沒有烏鴉,也沒有烏雲。
梵高總是沿著台階走上來,帶著一個畫架,一小箱顔料,一小瓶松香,還有一把槍。走過小教堂,經過一棵杏樹,然後他就看見這片麥田了。赤子般的翠綠和濕潤,寧靜地起伏著,要是他想要畫的是這樣的赤子心意,大概能多活一個孤獨的夏季。但是他不是。
沿著岔路向麥田中央望去,那裏有一塊小牌子,上面印著飛滿烏鴉的麥田,梵高的畫。這是梵高的麥田,畫上是金黃色的,像汪洋大海般起伏著的,烏雲密布的,烏鴉被他的槍聲驚起後,呱呱叫著在麥田上盤旋。

他一向喜歡畫麥田,從阿爾到奧維爾,一向都這樣。開始他畫裏的麥田還平整,絲柏點綴著遠方。後來,天上有了翻卷的烏雲,田裏有了粗大的雨點,最後是一群群盤旋不去的烏鴉。他需要成群的黑點點,所以當烏鴉埋伏在田野裏時,他就打槍驚起牠們,逼牠們飛。他畫出那些不安。七月末的麥田裏有驚濤駭浪,黃色意味著某種無法阻止的成熟。他老是坐在深處畫畫,好像是想在自己始終喜歡的地方表達心中劇烈的不安。
有人說他最後在這裏開槍自殺,有人說他因為酗酒而走火,有人說也許是他在村裏的兩個少年朋友玩槍走的火。總之,悲劇發生就在麥田裏,好像宿命。
梵高帶著流血的傷口,原路退回到坡下的小旅館裏,死在自己咖啡館對街的房間裏。
那聲槍響已經過去一百多年,這片麥田還保留著梵高遇見它時的樣子,一種植物聚集之處無聲的安慰與蠱惑。麥子聚集的大地看上去樸實,而且生命力旺盛,它令我相信梵高走上坡來畫它,一次又一次,因為它有自己獨特但毫不自知的美,他在這裏找到和阿爾麥田同樣的感受。也許因為它和他心意相通,他們在麥田寂靜的深處赤誠相見。
我向麥田深處眺望,青青麥好似顛簸的大洋。《麥田鴉群》的小牌子好像大海中沉船的碎片一樣。當麥子變黃後,那裏就會變成令人迷醉的漩渦了吧。金黃的顔色會令人害怕吧。大概不祥的,並不是漂浮在空中的烏鴉,而是在大地上起伏,並長出岔開小路的麥田。
我想起好多年前的晚上,讀到梵高來這裏畫畫,躺在灼熱的麥田裏,他的故事嚇得我雙腳冰凉,那時我已經決定自己這一生,要做成一個純粹的作家。
(四)常春藤棉被
奧維爾村的墓地在杏樹和麥田旁邊,墓園的圍牆外豎著梵高畫的麥田之雨,他斜靠在這面牆上畫畫時,一定沒想到自己很快就會躺在牆裏面。
墓園小小的,被雨淋得透濕。墓碑大多是簡單的一塊小石碑,或者小十字架,幾乎沒什麼高大的樹,也沒有通常老墓園的浪漫。要是梵高遺稿裏的一幅鄉村墓地,畫的就是這裏,那麼,如今這裏變化不大。
即使這麼小,一時也找不到梵高的墓。應該是梵高家的墓,文森特和提奧。哥哥死後,弟弟陷入沮喪,半年後也去世了,過來與哥哥埋在一起。照顧了梵高臨終的加歇醫生,又照顧他們兄弟的墳墓,書上提到過,加歇醫生在他們墳上種了一條法國鄉下最樸素的常春藤,去掉些荒凉。
書上說,他們的墳墓靠在墓園牆邊。
然後,看到一座被常春藤厚厚覆蓋的墳墓,在一個不知名畫家的墓旁邊。青石小墓碑上刻著文森特和提奧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墳上的泥土被常春藤層層環繞著,無它。只是加歇醫生種下的常春藤如今長得像一床棉被那樣寬大,厚而柔軟地蓋滿在墳上,使兩座並排的墳塋顯得異常沉穩寧靜。

雨點悄無聲息地將常春藤澆灌得又乾淨,又葱蘢,就像所有在墳土上長出來的植物一樣,特別茂盛,卻又特別靜穆,彷彿它的根是深深追隨死者而去,在地下纏繞他們,吸取他們,不讓他們消逝。因此它的葉子有一種特別的光澤,好像燭光照亮的眼珠裏閃動的微光一樣。
想起梵高,他是世上那種所有極少卻極珍貴的人。這個人會像無瑕之玉那樣,晶瑩剔透地愛世界;這個人能經歷赤誠的,劇烈的人生痛苦,也從未喪失過赤子心懷;這個人一生都有自己手足肯生死相依,直到死去,埋骨異鄉,他們也要肩並肩躺在一起;這個人死去一百多年了,當年自己醫生在墳上種下的常春藤仍舊好好地活著,代替早已離世而去的醫生,維護著墳墓那天真的樸素。如果是宿命的念頭,就會說,正因為他擁有的太珍貴,所以他不能得到更多的了。因此這個人生前無人喝彩;這個人一生無法開一次個人畫展;這個人沒有家,沒有孩子,沒有朋友,必定要孤零零地過完一生。
在墓園外,他當年畫畫的地方都還保留著他心靈的氣息,他的視線,他的角度。他面對的自然,也都還保留著他眼睛裏的樣子,人們三三兩兩,從千里萬里之外趕來,只為靜靜地與他待上一會,看看他眼睛注視過的世界。這些人似乎是被上帝召喚來此,向梵高奉上他曾渴望的愛與敬意。
梵高死得慘烈,但他在這個被常春藤覆蓋的墳墓裏,一定會得到安息。這些梵高天長地久擁有的,也是他同時代那些畫家難以擁有的吧,比如畢加索。
(五)空蕩蕩的淺褐色牆壁
如今奧維爾仍舊是個小鎮,一下雨就空了,貓都不在街上走。在梵高當年住過的旅館街對面,咖啡館裏也沒什麼人吃東西。這間咖啡館裏有個不大的舞台,舞台上方還有些花裏胡哨的彩紙懸著,周末也許有人在古色古香的舞台上唱香頌,跳康康舞,和梵高在這裏的時候一樣。
梵高在奧維爾時很想在咖啡館裏開個小畫展,但提奧沒來得及做,或者說沒能力做。後來,梵高成了世界上價格最高的畫家,小小一幅在奧維爾畫架上誕生的畫,曾經寂寞地靠在小房間門後,散發著松香水刺鼻氣味的麥田,在藝術品拍賣會上定能賣出不可思議的高價。這些本來只想在村鎮上展出一次的畫因此流散到世界各地。一幅麥田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裏,另一幅麥田在波士頓博物館裏,還有一幅麥田在巴黎的奧塞美術館裏,甚至有一幅在紐約博物館裏。如今這世界的各個角落,圍繞著他的畫,有數不清的監視探頭日夜嗡嗡作響地工作著,因為覬覦它們的人實在太多。

如今奧維爾小鎮希望能完成梵高的遺願,在梵高喜歡的咖啡館裏舉辦一次梵高畫展,把當年靠在街對面樓上房間門後的那些小小油畫從世界各地的藏家與博物館借回來,在咖啡館裏展覽一次。但是最終,因為無法承擔巨額的租借和安保費用而作罷。這次,仍舊因為費用太貴而失敗了。即使今天,金錢仍舊是困擾梵高畫展的原因。
要說宿命,這就是梵高的宿命,咖啡館淺褐色的牆壁永遠為他空著,而他永遠被錢困擾。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