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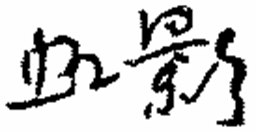
作家、編劇、詩人、美食家
河的女兒
《饑餓的女兒》在英美出版時叫《河的女兒》(Daughter of the River),當初把書名直譯成Daughter of Hungry,出版社營銷部認為是非洲的難民,讀者會嚇壞,他們取了好多書名,問我意見時,我說那些名字都不太適合,最好叫《河的女兒》,他們同意了。
這本在長江邊的女孩的成長的書,在歐美及歐洲受到高度重視,幾乎所有的報紙都整版介紹評價,甚至冰島也有這本書的讀者群。這本書無敵先於外文版在台灣爾雅出版社出版,一再加印,在二○○○年才在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讀者喜愛度遠超過國外,國內讀者是真懂。記得在重慶解放碑新華書店簽名售書時,萬人空巷,好多讀者說,你寫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

做一個作家,除了欣慰,還求什麼。
女性主義
沒有誰說男作家是一個男性主義作家。因為他們就是男權,整個社會的主流者。
女性主義被他們稱為女性主義,是明目張膽的欺負:你們是女性主義者,你們是二等人。
好多男性談到女人時,皆有一個居高臨下的態度。我的小說《K──英國情人》初稿成了後,交給我英國文學經紀人。他一向權威,看了後說,你一個中國女作家怎麼可以寫我們的精英圈子布魯斯布瑞,怎麼能寫好二戰?
他拒絕代理這本書版權。
這是性別歧視,也是種族歧視,他不相信,一個中國女性作家可以寫這種類型的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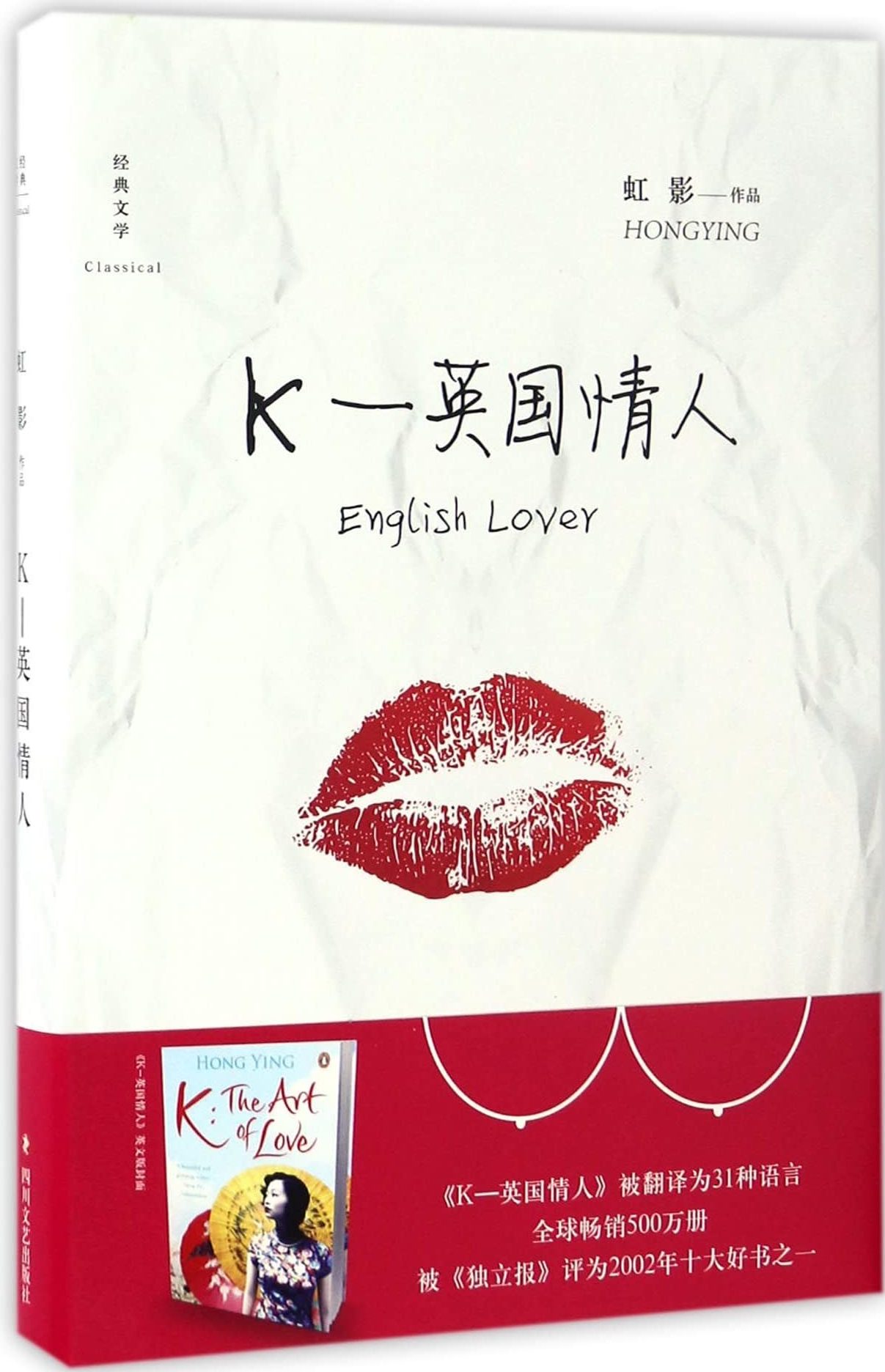
事實證明,他看走眼了。這本小說寫了戰爭,不亞於男性作家,寫英國精英圈子,讓身居其中的人驚嘆。之後這本書經過好多年許多曲折,最後在國外出版,翻成三十種語言,並獲得意大利羅馬文學獎。這個英國經紀人經常在世界很多地方的書店和機場看到這本書,很想知道他的心情,有一回在法蘭克福書展與他迎面相遇,他祝賀我當母親,而隻字不提那書。
「因為我長得太高了。」
我應是後女性主義者,相對早年的我,比較寬容、理解男性,而不是用敵視的姿態對待他們。我烹調佔領廚房,成為一家之靈魂,我是我女兒最好的母親,我寫作,也不再單純地製造一場男女之戰,而是去找根源,我也用口紅和旗袍,面容溫和,的確我不是男人想的那樣青面獠牙的妖魔。
北大教授戴錦華曾用一句話回答她何以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者,她說:「因為我長得太高了。」
我呢,我是身材太矮,所以,我看得見最低處的真相。
女權與代價
法國大革命的婦女領袖奧倫比.德.古日的《女權宣言》,說得一清二白:「婦女生來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權利。」
兩年後她就被過去的男性同黨推上了斷頭台。
為什麼寫作?
每個寫作者都有原因,寫作時都有秘密。
我簡單回答,就是為了讓讀者買了我的書,看一個好故事。
複雜回答,就是為了存在,為了醫治我受傷的心。
關於這個問題,我分地點和時間不同,有不同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是誠心誠意。
寫作時,我不用語言而用情節提出問題,能否感覺到有問題,看每個人的慧根。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我用人的命運來設置我的問題,用生和死,生死相契,悲歡離合。
我的寫作跟言情小說不同,故事並不只是讓人哭泣,不只是感動,更是惶惑。
惺惺相惜
我寫過幾個已故女作家的東西,像蕭紅,包括張愛玲、蘇青。她們是我喜歡的前輩。
她們與同時代的女作家不一樣,就是她們為自己而活。
她們遇到的男人卻有些相似,不忠誠,見異思遷,始亂終棄。
她們出生的背景影響一生,張愛玲名公名媛後代,家世顯赫,少時沒家庭溫暖;蕭紅從呼蘭小鎮跑出來,和所有男人的關係越弄越糟,最後三十一歲命喪香港;蘇青個人生活也好不到哪裏,與男人的關係也是強弓之弩。
但是她們活得精彩,活得有歌有泣,愛得有血有肉。蕭紅愛過的男人,至少史家已經不否認的還有好幾個,最後是比她年輕七歲,當時才二十多的駱賓基,她崇仰魯迅,而魯迅對她幾乎越出了父女式情感,從她紀念魯迅的幾篇文字,從當時人的回憶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場最秘密也最驚天動地的戀情,呼之欲出。張愛玲與胡蘭成據說是行過跪拜之禮的,胡蘭成那時在上海灘炙手可熱,是青幫流氓頭子吳四寶的軍師,她也糊塗跟著。此後胡蘭成已經不知道換了幾任妻子,甚至打發懷上自己孩子的女人找她解決問題,她還當掉細軟給了這孕婦。最後胡蘭成寫信到香港,要求張愛玲介紹他進CIA做特工,才把張愛玲嚇出一身汗,從此不再通音訊。張愛玲一下萎謝了,嫁給一個電影劇作家賴雅。張愛玲愛賴雅嗎?只是為了在美國不孤寂生存下去?
蕭紅的愛,是愚蠢的:一見鍾情赴湯蹈火,一言不合,拍手走路。張愛玲的愛,是算計的,人情通達,有所靠有所得。張愛玲僅是在過孤芳自賞日子而已。兩人都是紅顏薄命?不,蕭紅愛得熱烈,始終充滿激情,命短而不薄,張愛玲做人矯情,性格孤傲,長壽而不幸。
海明威及道德
海明威一向以風流倜儻著稱。
英國詩人布魯克斯一次大戰時去世,人說這麼美的男子,我們現在時興的話「帥哥」,怎麼可以死在戰爭裏?
美女太多,好作家卻太少。
最大的問題是人沒有道德底線,不講信譽,不管下一筆生意,不要回頭客。
作家想想自己的信譽,政客、商人、評論家,我們每個人,都想想信譽,這個世界哪有不付出代價就能空中攬月?
使命
為不能發出聲音的生活在最下層的女性寫作,講她們的故事,這是我寫作的使命。
我每次站在長江邊上,看船看江上的鳥,看天空的雲,都會跟一個人相關,那就是我的母親。母親就是生活在最下層的一個女性,她從忠縣鄉下逃婚來到重慶,一生波瀾起伏,相信好人好報,愛人比恨人強,原諒勝過報怨,在一九六二年,她寧肯背對一切,把我生下來,並用一種超常規的方式養育我,讓我野蠻生長。
我母親反叛的血液流淌到我身上,足以解釋我所有的生活和寫作。

弱勢
一個女性,她一出生,就明白自己處於弱勢,尤其在中國如此強大男權思想體系中,一個女性如果寫作,說到底是一種反抗的姿態。
作為女性,我關心女性本身、女性的成長、女性的婚姻和不公平的命運。
在娘胎裏,母親擁有我的那一瞬間,就是對這個世界叛逆和不順從。
女人的美
小時,很羡慕那種戴眼鏡的女人,她們有知識,有學問,透露出別樣的光芒。
有一回學校組織看教育片,在電影院,開映前,有一個女人戴著眼鏡從廁所門口走出來,有一個男孩子沒看見,對撞過去,那女人身體斜了斜,沒有生氣,反而伸出手去扶起男孩,然後伸直背,朝男孩一笑。那笑真美,那氣度讓人欽服。
好多年,我都記得那場面。
我是愛美者,只要是美的,我都會屈服。美像一場不經意的煙火,節氣過了就過了,不會再來,再來的是另一種節氣,節氣年年有,但同樣的煙火不再。我害怕失去美,也害怕女人不再美,尤瑟納爾不是美女型的女人,常年帶同一口箱子到處旅行寫作,她的眼睛有一種少見的篤定,對我而言是美的。杜拉斯酗酒成性,一副年老色衰的模樣,惹我疼愛,她是美的。伍爾芙衣袋裝著石頭走下河,讓最後一口氣飄浮在水面上,那種毅然決然,是美的。阿赫瑪托娃稱手持木笛的繆斯,美麗會一直相隨。

虹影。(作者提供)
真實與虛構
生活的真實故事,有多少可以用來於抒寫,有多少可以裁掉,有多少可以虛構?這本書作家要表達的只是記載有過的生活,令人痛心不已的往事,或不止於此,觸及那種內心深深孤獨的冰山。
這看似簡單,卻是在考驗你的寫作技能和選擇的思想立場。
我寫《饑餓的女兒》,可以寫幾百萬字,把有過的生活真實記錄下來。但我在大腦裏進行了大浪淘沙,我也運用了虛構:在母親的子宮,我想像我呆在那兒,一遍遍聽到她的哭泣,並品嘗她的淚水。
這種想像,給我力量。讓我在成稿後,再次下手,砍掉枝蔓,使《饑餓的女兒》這棵樹於時間的風暴中更堅韌。
我信有
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我都信。我信有,不會信無。
你不能夠怪罪生活,你不能夠怪罪命運。一個人只要虔誠,始終愛人,相信這個世界始終是善的,那麼你總會看到美好的事物。
很多人什麼都不相信,這樣的人其實是一個窮人。
二十歲前很盲知,收音機裏念聖經時,每一個字能背下來,那種信是一種盲目的信,同樣,那時的叛逆是一種盲目的叛逆,那時的憤怒也是盲目的憤怒。
內心感受什麼,就寫什麼
上小學時,同學大都是工人階級家庭出身,有一個同學,父母都是老師,不時會帶革命小說來看。心裏羡慕她,她說小時候母親總在她床邊讀書。
我的父母並不支持女孩子讀書,每到交學費三元錢時,我都得哭,才能得到。
家窮,電費貴,我做學業,也只能到院外路燈下。
我沒有好的先決條件,卻愛書,愛故事,愛聽神神怪怪的事。一到夏天,是我的節日,因為盛夏,房外空地,潑了涼水,太陽下山,會涼快,人們會搬小板凳出來乘涼,會有人擺龍門陣,說的都是陳年的鬼故事,也有人自動讀外國小說。我總是第一個坐在那兒。
聽多了那樣的故事,腦子裏自然裝滿了這樣的東西。輪到寫作文,從小學到初中,我寫得怪怪的,總被老師批評,思想有問題,被打最低分。有一次寫批林批孔的文章,別人去抄報紙,唯有我會寫孔子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他居然說「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還有「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他不是女人生下來的嗎?老師在我的句子下面打了好幾把紅X。
上高一時,語文老師生病了,請了一個老教師代課,她讀到我的一篇作文,一篇課文讀後感。寫毛主席的一個警衛員,通過他述說領袖多麼偉大與辛苦。我寫這個警衛員的觀察,通過他的眼睛觀察到主席的細微表情,寫得很具體,包括主席窗前的油燈。代課老師在班上讀了這篇作文,說,你讀到了什麼,內心感受到什麼,就寫了什麼,打滿分。
我非常感動。第一次有老師欣賞我。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