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榮 訪問及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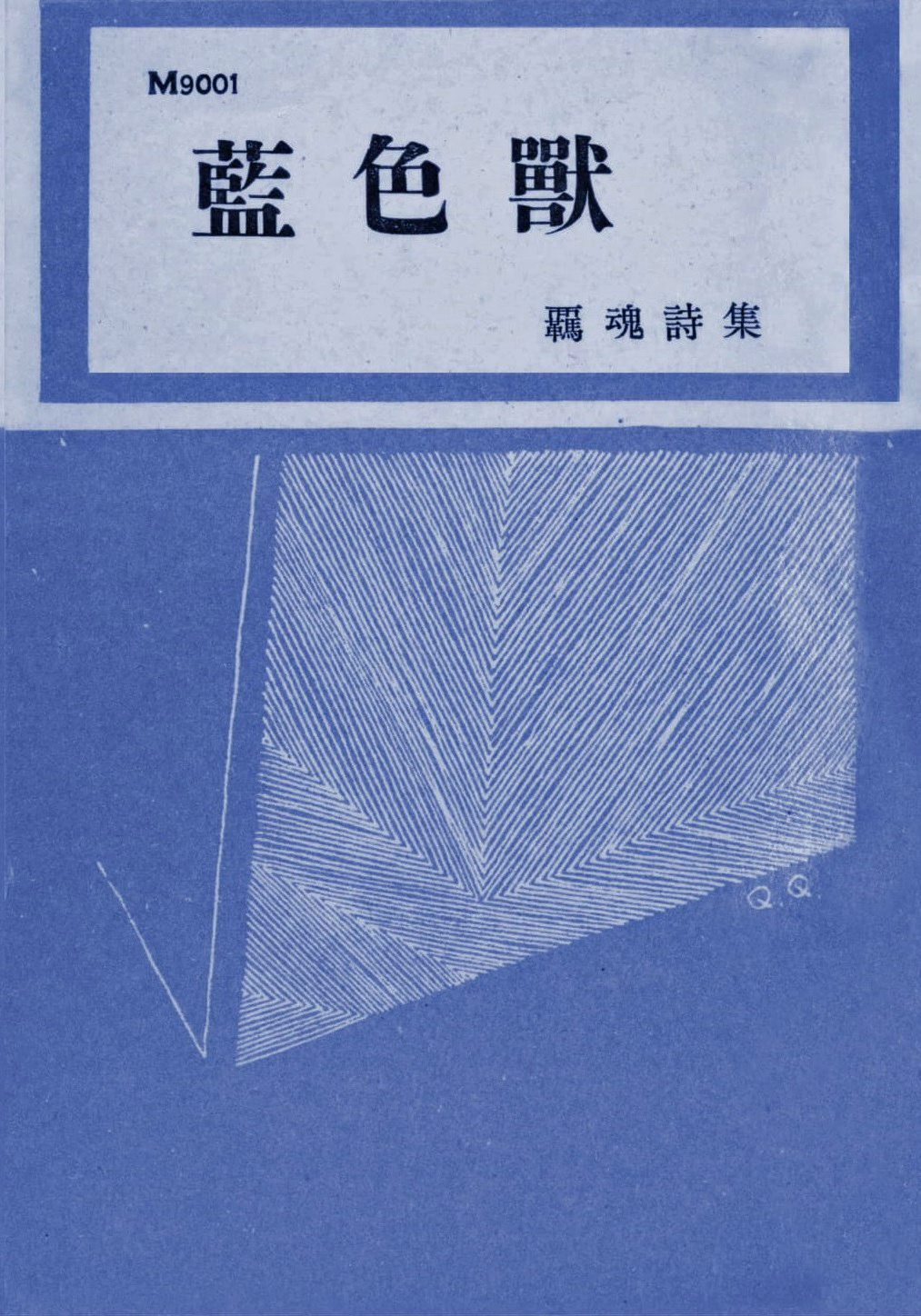
前言:羈魂先生,原名胡國賢。一九四六年生於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文學碩士。六、七十年代香港「文社」與「詩社」運動中堅,曾創辦《藍馬季》、《詩風》、《詩雙月刊》、《詩網絡》。詩作曾入選中、港、台、澳洲、韓國、馬來西亞及羅馬尼亞等地選集,歷任「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雙年獎」評判。編著有詩集《藍色獸》、《三面》、《折戟》、《趁風未起時》、《山仍匍匐》、《我恐怕黎明前便睡去》、《回力鏢》;詩文集《戮象》、《這一個晌午》;詩評論集《每周一詩》、《足跡•剪影•回聲》;詩選《香港近五十年新詩創作選》及粵劇《孔子之周遊列國》等。這篇專訪裏,羈魂不僅會細述自己新詩創作的歷程,還會點評中、港、台三地的新詩名家。
問:李浩榮
羈:羈魂
一、影響與交往
問:〈藍色獸〉是您早期(一九六五年)的詩作,詩中交織著瘋狂、熱血、黑暗,與您日後的創作基調截然不同。詩裏對「瘋婦」的描寫,甚有李金髮〈棄婦〉的味道。請問李金髮與象徵主義詩派對您早期創作有沒有影響呢?
羈:其實,小學時我較喜愛古典文學,中學辦文秀文社後才多接觸新文學。《戮象》(一九六四年)中收錄的三首新詩,正是那段時期的作品,風格較接近新月浪漫派。至於〈藍色獸〉,則是我加入藍馬現代文學社後創作的,極富現代文學色彩。進入港大中文系,重投古典氤氲中,我竟一度嘗試創作一些以「古典為貌,現代為神」的「實驗新詩」。《藍色獸》詩集裏不少數行小詩,正是這方面的成果。
說到〈藍色獸〉中「瘋婦」、「血」、「雪崩」等意象,與其說來自李金髮,倒不如說來自洛夫。事實上,不少論者都認為,〈藍色獸〉深受洛夫《石室之死亡》的影響。這點我也同意。
問:當時您是怎麼讀到李金髮、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新詩呢?也請談談您對這些詩人的看法。
羈:加入藍馬後,通過許定銘,認識一些文友。他們積極蒐集,甚至翻印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新文學書籍。我主要是藉此讀到大量那段時期的新詩集。(七十年代初,我曾一度加入「鳳凰出版社」,協助蒐羅和翻印那些絕版書呢!)後來大陸逐漸開放,書籍恢復發行,這些翻印工作才無以為繼。
相對新月派,我較接受卞之琳與何其芳等三、四十年代作家,尤其他們能融匯古典於現代之中。至於李金髮、戴望舒等,則傾向西方象徵主義,尚有一些值得欣賞之處。戴望舒在香港創作的一些新詩,對我後來以香港本土為題材的創作,有一定影響,尤其心態方面。要知道,他只是旅居於此的內地人,也能寫出對香港的情懷。我是生斯長斯的香港人,當然更應書寫吾土吾民。

羈魂先生,原名胡國賢。
問:創作早期,您有接觸西方的現代詩嗎?
羈:我在皇仁讀中學,英文科需要閱讀不少英文名著,因而也曾讀過莎士比亞,以至雪萊、拜倫、華茲華斯等西方詩人的作品。我十九歲寫〈水仙〉相信正由此啟發。加入藍馬後,更讀了不少現代主義的作品,尤其是存在主義的。艾略特的〈荒原〉、卡繆的《異鄉人》,常是大家談話之資。坦白說,那時候我仍未讀透的,卻大膽地把一堆未全然消化的東西,直接放入〈藍色獸〉等詩作中。那代西方現代詩人中,我較明白也較喜歡的是龐德,也許是他的短詩,近似唐人絕句吧!
問:您讀香港大學時,老師有鼓勵學生創作和推廣現當代文學嗎?
羈:當時的港大課程沒有現當代文學,更沒有這方面的推廣;只有極少數老師如張曼儀,於課餘辦新詩班。我本來也想報讀,但為張老師婉拒。她笑說,你是羈魂,不需參與這課程了。原來她早已知道我發表過不少詩作。
問:那時候的作品多在甚麼地方發表?
羈:新詩多發表於《中國學生周報》的〈詩之頁〉,散文則在《星島日報》的〈青年園地〉(原為〈學生園地〉)。當時,〈青年園地〉 的編輯是胡輝光,文社的稿投去,他一般會盡量刊出,以示鼓勵。至於〈詩之頁〉,說起來,也有一段文學因緣。雖然〈藍色獸〉不是我第一首在《中國學生周報》上發表的新詩,但詩稿寄出後不久,竟第一次收到〈詩之頁〉編輯 (後來才知悉就是蔡炎培)的來信,更一連兩封。(早前我已把這兩封信捐給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館藏。) 蔡炎培喜歡改動別人的詩,〈藍色獸〉見報的版本,也經他改動過,當時我有些不悅。他又喜歡以馬評的方式評詩。〈藍色獸〉首節刊出時,他便在詩旁加了一節風趣幽默的按語:「經過殯儀館化妝之下,是否較生鬼呢?」
問:你一九六九年寫的〈沏〉詩,模擬茶樓對話的情境,讀來頗有余光中〈五陵少年〉的色彩。詩中用了劉伶、陶令、黃鶴樓等典故,也令人想到余光中新古典主義的詩風。請問您對余光中的新古典主義有何評價?也請談談您與余光中的交往。
羈:我讀過余光中〈五陵少年〉,但〈沏〉跟〈五陵少年〉並沒有任何關連。〈沏〉是寫我上粵式茶樓的經驗。少時,家住深水埗唐樓,環境嘈雜,很難安心讀書。由於家母愛「飲夜茶」,而黃昏時段,茶客寥落,我便隨她到那裏,順便做功課、溫習。光顧久了,跟茶樓的伙記甚至茶客都混熟了。當時的茶樓,品流複雜,有賣藥的,有看相的,也有不少外省人;他們講話我不大聽懂,只覺有趣。升上大學後,便很想寫一首詩,抒述少時上茶樓這難得的體驗。但,該怎麼寫呢?那時候,適值胡金銓的《龍門客棧》首映;看後,我覺得大可借用戲中古代酒寮的氣氛,只是要把場景與粵式茶樓糅合起來。於是,〈沏〉中的人物便帶著武林的味道,「挑挑撻撻」,飲茶亦如飲酒一般。〈沏〉裏,我還刻意加上廣東話,如「開嚟有找」,藉以加強詩中市井氣息和本土色彩。余光中可不會這樣寫吧!曾有朋友批評這句廣東話破壞了整首詩語調;我卻認為,若真的換成書面語,市井和本土的感覺便出不來了。
我寫〈沏〉時,文學界還沒有「新古典主義」這觀念。若說這詩裏有「新古典主義」的味道,那也是羈魂式,而非余光中式或任何人的。對於「新古典主義」,我並不反感,卻不會刻意標榜。如果題材需要多一點古典氣韻,那自然就會多用典故;但若是現代或現實題材,那就需要多用現代漢語甚或口語了。〈沏〉就是試圖糅合古典與口語。寫新詩的人,我認為必須要有古典根底,但怎麼把古典與現代融合起來,那得看個人功力。洛夫早年主張扔棄古典,後期還不是回歸傳統?所以,標榜古典與揚棄古典,同樣沒有意義。當年讀余光中《蓮的聯想》感覺一般,甚至覺得我也可以達至這樣的水準。反而,他後來寫的〈公無渡河〉等詩,我覺得很好,寫偷渡的慘況,而能融匯古今詞藻、語調、節奏,實屬難得。再後期的〈母難日〉、〈抱孫〉等家庭題材也很感人,能將古典學養與生活經驗完美地結合。
一九六九年,我首次見到余光中先生。那該是余光中初次訪港。我和很多本地文友一同拜訪他,好像是吳萱人牽頭的,出席者還有古兆申、康潔薇等。到了七十年代,余光中應聘來中大教書,正值我們編刊《詩風》,便請他供稿,他差不多每期都來稿支持。我有幸能率先讀到他當年在香港寫的新詩,並一路見證他風格的轉變;而自己,也不自覺地慢慢轉變過來。
問:六十年代末,您的三首新詩〈碎〉、〈牆〉、〈失〉充滿了暴烈的美學,觸目盡是「乍裂」、「成灰」、「滴血」等意象,甚有洛夫的色彩。洛夫的詩風對您的創作有甚麼影響呢?〈蛇羹〉是您給洛夫的贈詩,也請談談您與洛夫的交往。
羈:台灣五、六十年代好幾位詩人的詩我都欣賞,但多是蜻蜓點水式地淺嘗;唯有洛夫,卻令我沉迷不已。無可否認,我詩裏「乍裂」、「成灰」、「滴血」等意象,確是深受洛夫影響。以前,我讀卞之琳的詩,感到意象唯美,氣氛哀怨,卻沒有那種衝擊和衝動。但,洛夫不同:「祇偶然昂首向鄰居的甬道,我便怔住」,《石室之死亡》開首已不同凡響。洛夫的詩,儘管我未必可以每句解釋得來,卻隱約感受到他的心境,體會到他的情緒變化。他的意象可謂雜亂無章,而我正正喜歡他這一點。如「驀然回首/遠處站著一個望墳而笑的嬰兒」,「望墳」、「笑」、「嬰兒」三個毫不相關的意象,卻可以如此聯繫起來。又如「如果你推倒所有的石柱淒然而去/伊的眼淚就再找不到挑釁的對象」。推倒所有石柱,可以理解為推翻傳統,但也可有其他解說呢!這正是洛夫,以至中國詩的妙處:放在不同處境下,可以有不一樣的解讀。洛夫早期強調「自動語言」,說寫作不是由作者本人控制,而是意念借作者之手而出。我自己寫作時,也曾有「自動語言」的情況,有時候,意象會不由自主地跳落紙上。然而,當修改時,我會重新審視這些意象,是否用得恰當。如果連自己也感受不到意義,便會把它刪去。

我最喜歡洛夫《石室之死亡》,後來他的詩風變了,變得有跡可尋。例如《魔歌》時期作品,集子裏有些意象,也許洛夫自己也未能消化過來,其中〈長恨歌〉我最接受不了。反而他晚年寫《漂木》,詩風得到淨化,只是略嫌冗長。此外,我也喜歡他的禪詩,〈金龍禪寺〉更是我常用作教材的作品。還有他的〈寄鞋〉,由縫補鞋底寫到鄉愁,奇特的意象與感情巧妙地結合,正是洛夫的看家本領。
我承認。〈藍色獸〉主要是模仿或脫胎自洛夫,但〈碎〉、〈牆〉、〈失〉這三首詩,卻是企圖擺脫洛夫,向古典靠攏的嘗試。這三首詩以文革為題材,是六十年代末,香港少有講述中國問題的詩作。用洛夫的意象,加上古典節奏去寫文革,可謂絕配,能供發揮的空間很大。
至於〈蛇羹〉則寫於一九八八年。當時洛夫訪港,香港文友宴請他吃蛇羹。當洛夫吃得津津有味時,問起碗中物是甚麼。我告訴他是蛇,他立時面色大變,但接著還是開懷地吃。我捕捉住洛夫這番的變化,以蛇褪變的意象,寫成〈蛇羹〉。那場宴會,座中還有顧城夫婦。
問:提起顧城,您對內地朦朧詩派有何評價?
羈:顧城性格很酷,當時只是問一句,答一句。他看來很依賴太太謝燁,不時問太太,帽子戴好了沒有。顧城某些詩,我覺得還不錯;但是,當你了解他的性格和生平後,便明白他為甚麼會這樣,那種感覺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編《詩風》時,顧城已主動投稿過來。當年讀到他的詩,覺得蠻不錯就刊出了。顧城為甚麼會投稿給《詩風》,我也不大了了,可能是跟編輯王偉明有關。偉明人脈廣,跟內地不少詩人也有聯繫。楊煉也有新詩在《詩風》刊登,那是我們邀稿的。綜觀當年朦朧詩人,北島名氣最盛,但《詩風》同仁最欣賞的還是楊煉。楊煉的新詩其實不算朦朧,字裏行間更充滿火氣。說起來,朦朧詩出現之初,我覺得那不就是《藍色獸》時期我輩的風格麼?但我們當時這樣寫,並沒有獲得兩岸重視,可見香港詩壇一直為兩岸忽略。也許是時代因素吧!由於香港過去是殖民管治,在他們眼中,文化根基不夠紮實。可惜,時至今日,這觀念依然沒有改變,令人唏噓。
問:後來,您寫家庭題材的詩作,真切動人,完全擺脫了洛夫的色彩,為甚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呢?
羈:《藍色獸》出版後,一些文友批評我的詩,如七寶樓台,拆下來卻不成片段。我不服氣,決心去寫現實一點的題材。那時候,女兒出生,我對生活有了不一樣的感覺,便嘗試捕捉這種感覺。詩集《三面》的同題詩〈三面〉,就是寫給與我同月誕生的女兒嘉文。女兒出生後,需要放入玻璃罩內吸氧氣。我每天放學都跑到醫院探望她。見到第三面,她終於可以離開玻璃罩了,心內感觸萬分,就把那三次見面寫成〈三面〉這首詩。《三面》與《藍色獸》的出版不過幾年之差,風格卻已截然不同。
問:讀您寫於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詩作,頗多佛道的意識與詞彙,如「未鑿的混沌」(〈三面〉) 、「如來天地」(〈看山,雨中〉) 、「因緣苦集」(〈惡緣〉) 。佛道兩家的思想對您的人生有甚麼影響嗎?
羈:我在港大曾修讀中國哲學課程,對佛道稍有涉獵。此外,有一段時期,我頗喜歡周夢蝶的新詩,多少也影響我的用詞。反而後來,我對佛道思想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卻不敢再多用這些詞彙。因為我得考慮是否用得恰當,一旦猶豫,便不敢落筆了。我嚮往莊子的逍遙,但自問仍未達到那樣境界。
九十年代中,我移民澳洲前,內心也經歷一番掙扎。那時我未屆五十歲,還熱愛教學。我曾自問能否真的放棄教學工作?最後雖然選擇移民,始終是個很艱難的決定,而兩年後我也終於回流。目前,我已退休十多年,初期還在港大及教院兼課,現在則主要寫粵劇、舊詩等。(我第一本古典詩集將於七月初出版,而第三齣粵劇作品則將於九月底首演。) 我想,我應是個頗為入世儒家式的人,閒不下來。
問:關於周夢蝶的詩,您有何評價?除了余光中和洛夫,他們那一代的台灣大詩人,您還有喜歡的嗎?
羈:周夢蝶的整體風格我都喜歡。他的〈樹〉,尤得我心。我最鍾情其中兩句,「等光與影都成為果子時,/你便怦然憶起昨日了。」「光與影」好似是抽象的,但成為「果子」,卻是具體可見的。「昨日」也好像是抽象的,但藉著成熟的果子,回望往昔的歲月,一切便又變得清晰可見了。這兩句詩是從生活的體驗裏提煉出來的。印象中,我曾在台北拜訪過周夢蝶一次。他為人較沉默,不太跟人閒聊。
台灣詩人中,我較欣賞的,還有鄭愁予。鄭愁予來港時,《詩雙月刊》曾訪問過他,更帶過他遊車河呢!至於瘂弦,跟我距離較遠,他對也斯的影響相對大些。而楊牧也曾為《詩風》當徵詩比賽評審;他為人內斂,跟我們的聯絡不太多。楊牧的詩,有時鑽得太深,有時則拉得太鬆;反而,他葉珊時期的作品較易理解。不過,印象最深的卻是他的敘事詩〈吳鳳〉,可惜較少人提及。
問:〈遇〉是寫給綠原的詩作,為甚麼會有這首作品呢?綠原與七月詩派的新詩,您喜歡嗎?
羈:我和綠原見面是在一九八五年。當時《詩風》雖停刊,但跟內地不少詩人仍有聯繫。那年綠原來港,便指明要跟《詩風》同人見面。我記得是在灣仔一家酒樓聚餐。飯後,他在街上攥住我的手腕,鼓勵我一番。風,從海傍吹來,我忽然有一種世事茫茫的感覺。畢竟,我們是不同世代的人:他是經歷過歷史動盪的老人,而我當時還值壯年,且生活於太平盛世的香港。那畫面,那觸摸,那風吹的感覺,至今仍歷歷在目。那趟見面,綠原給我一種很真誠的感覺。綠原的詩有一兩首,我很喜歡,但整體對我的影響,比不上卞之琳和何其芳。七月詩派另一詩人艾青,我卻不喜歡。艾青的名詩,如〈雪落在中國的大地上〉、〈大堰河是我的母親〉,我先天就有一種反感。同樣的主題,何其芳的〈古城〉,意象運用遠比他好。
問:〈給國彬〉、〈戲贈康夫〉、〈拐彎與攀梯〉三首詩,是分別寫給黃國彬、康夫、也斯的作品,請談談您與這三位詩人的交往,和對他們詩作的評價。特別是也斯,他的詩風明朗,強調本土題材,反對新古典主義,您有何看法呢?
羈:三人中,我最早認識和合作的是也斯。中學時期已認識他,因為同是文秀文社成員。當年,通過一位社員介紹他入社。也斯大概在《星島日報》讀過我們的作品,覺得不錯,才願意加入吧!文社另一位成員吳煦斌,當時是《中國學生周報》港島通訊員。有一回,我在那兒出席會議,她主動上前自我介紹;我見大家談得頗投契,便邀請她入社。她還帶了一位同學加入。吳煦斌與也斯就是在文秀文社結識的。那時候,大家在創作路上尚處於摸索階段,並沒有強調甚麼門派。不過,從也斯翻譯的作品看到,他中學時期已傾心西方文學,而我則較傾向古典。也斯很少在《星島日報》發表作品,主要投稿給《中國學生周報》。當時,他應已醉心現代文學創作,但從不標榜。所以,許定銘成立藍馬文社,提倡現代文學,竟沒有向他招手,反而把我吸納進去,很奇怪。我跟也斯雖然因文學結緣,卻很少談論彼此的詩,也許是性格、詩觀不同吧!和而不同,各自發展。可惜,始終再沒有直接合作的機會。
黃國彬與我雖同在皇仁書院唸書,卻低我兩屆。當年皇仁也有很多文社,黃國彬參加了秋風社,社員全是同校同學。我雖然知道他是人才,但不好意思挖角,彼此於中學時期屬點頭之交,沒有甚麼聯絡。直至我研究院畢業,他也本科畢業,一起出來社會做事時,他才找上我,合辦《詩風》。黃國彬的詩風深受余光中影響,不少我也極為欣賞。當年會考課程曾選了他的〈聽陳蕾士的琴箏〉作範文,我覺得這選擇間接地害了他。
康夫跟何福仁在一九七六年《詩風》改版時一同加入。當時,我剛重回《詩風》,與他們共事過一段日子,也很愉快。可惜,他們很快便離開,主因是詩觀跟某些編委不合。他們在《詩風》只編了一期雜誌,就是改版後的第一期。不過,我和他們後來還保持聯繫,有時更相約喝茶聊天。康夫和何福仁辦《羅盤》時,也有向我約稿。
問:聽說,您是香港最早翻譯特朗斯特羅默的人,請談談這經歷。
羈:我也想不到會成為香港,以至華文詩壇中,第一個翻譯特朗斯特羅默的人。記得當年為了慶祝《詩風》一百期,同人異想天開,要出版特輯,邀請世界各地著名詩人惠稿,由我們翻譯成中文。我們先擬定邀請名單,再跟世界各地文學組織或領事館聯絡,託他們代為轉達邀請。誰料反應極為踴躍,各地詩人紛紛來稿支持,其中數位後來更奪得諾貝爾文學獎呢!當稿件收齊後,我們便分配翻譯的工作,每人大概要翻譯數首。當年,特朗斯特羅默的知名度還不太高,他好像是由瑞典領事館推介來的。我們編輯也沒有人懂瑞典文,幸而特朗斯特羅默很有心,來稿附上了英譯。我讀到他〈軌道〉的英譯,十分喜歡,覺得似中國近體絕詩,便主動提出由我翻譯。我用「月明星稀」翻譯了其中的詩句,讓古典氣息更形濃烈。

二、語言與形式
問:您新詩的語言甚為精煉,不乏四字句,如「千仞不樹」(〈失〉)、「星渡窮途」、「獸囚三面」(〈折戟三篇〉);另外,您也會直接運用文言字詞入詩,如〈陶將軍俑〉中的「汝」和「兮」。以文言的句法和詞彙寫新詩,您認為有甚麼好處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羈:我的詩風貌較多。若某一類詩需要用上文言字詞,才能帶出其中的古典韻味,我並不介意採用,〈陶將軍俑〉便是其中例子。當年,秦俑首次來港展出,參觀後不期有感而賦。當中的思古幽情,我覺得非用文言字詞不足以展現,所以才有「拄劍無劍」、「挽弓無弓」等較文言的句子。〈折戟三篇〉中的「地茂館」也有涉及康夫。康夫那時候剛出版詩集《窮途》,而他又喜愛寫小明星,所以我便有「星渡窮途」之句;至於「獸囚三面」則用了我的詩集作典,獸指《藍色獸》,三面指《三面》。「獸囚三面」表面好像引用「商湯禱天」典故,其實是說我的《三面》時期,已沒有《藍色獸》時的野性色彩了。這樣的寫法,純粹過癮,讀者也許需要注釋才能理解。
用文言句法,切忌濫用,尤其陳腔濫調。「拄劍無劍」、「挽弓無弓」、「執戈無戈」,那都是我參觀秦俑展覽時的真實所見。如其中一名秦俑擺著拉弓的姿勢,但手上的弓早已不存了,確實是「挽弓無弓」。另外,運用文言句法,也要視乎那首詩的風格,須得要呈現古典韻味時才用。
問:您除了是詩人,也是粵劇的作者,曾寫過《孔子之周遊列國》。〈粵劇〉一詩裏,您更用了粵劇的分場及工尺譜來寫詩。粵劇對您寫詩可有甚麼啟發?
羈:我自小喜歡粵劇,一直希望寫一首以此為題材的新詩,因而寫了〈粵劇〉這首詩,把粵劇「唱、做、唸、打」的概念融匯詩中,藉以寄寓對人性的一些看法。如寫臉譜的變換,「昨日帝王 明天走卒/如今是花臉大喉掛鬚的/哪一朝將相?」寄寓人性的瞬息萬變,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自己?
用辭方面,戲曲對我的詩也有一定影響。例如:「罷罷罷」等三疊歎詞,正是套用粵曲連聲感歎的做法。題材方面,我寫〈荊軻〉、〈華山記〉等作品,亦是從粵劇吸取靈感。〈華山記〉便用了粵劇《寶蓮燈》的典故。
問:您新詩的感歎修辭,常常將歎詞置於句子的中間,如「寢食難安啊坐立不寧」〈膽頌〉;另外,長短句的大量使用,以及拆字修辭,如「杯已狼囊不起晚騷的離/盤已藉植不起早雕的花」〈折戟三篇〉,都令人想到余光中常用的修辭技法。余光中的修辭技法對您有沒有啟發呢?還是這些修辭的技巧是由古典詩直接轉化而來的呢?
羈:這種寫法,其實主要受《楚辭》影響,非來自余光中。由於白話詩不太好使用「兮」字,我便試用白話文常見的感歎詞代替。為了避用標點把句子隔開,破壞節奏感,那就只好用感歎詞,把上下兩句接駁起來。這種句法,頻繁出現於我中後期的詩作,早期則較少見。
至於「杯已狼囊不起晚騷的離」則是寫蔡炎培的,而「盤已藉植不起早雕的花」卻是寫戴天,分別融入蔡炎培《離騷》和戴天《花雕》的詩題。這兩句其實也玩諧音字,「狼」與「囊」,「藉」與「植」。蔡炎培早期的短詩,我很喜歡的。而戴天寫中國的詩,對我的古典書寫,頗有啟發。他的長詩〈蛇〉,不乏佳句,但略嫌冗長,有堆砌的毛病。長詩難工,適宜用作敘事,所以我較少嘗試。
問:您的新詩也不乏以古典詩的特殊形式創作,如〈十月的選擇〉和〈荔枝〉等詩。古典詩這些特殊的創作方式,套用在新詩上,您期望會有甚麼效果與發展?
羈:洛夫也寫過不少藏頭詩。古典文學更有一系列的雜體詩,如隱題(藏頭)詩、神智詩、盤中詩、雙聲疊韻詩等,我偶爾亦會嘗試這些技法。〈荔枝〉這首詩是以正方形,由外而內的形式排列,近似古詩的「盤中詩」;加上詩題的諧音,合在一起,便成了「方勵之」。這是一首獻給方勵之的詩。至於〈十月的選擇〉屬「隱題詩」。由於我和女兒同於十月出生,而兩岸慶典也在十月,因而引發「十月的選擇」的感觸和思考。中國文人愛以這些特殊的創作形式,帶出當中寓意。新詩借用這些手法,得看看是否必要,而不是為寫而寫,徒具形式。
(訪稿經受訪者修訂)
(本文圖片皆由訪問者提供)
李浩榮簡介:香港作家聯會理事、《香港作家》網絡版策劃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