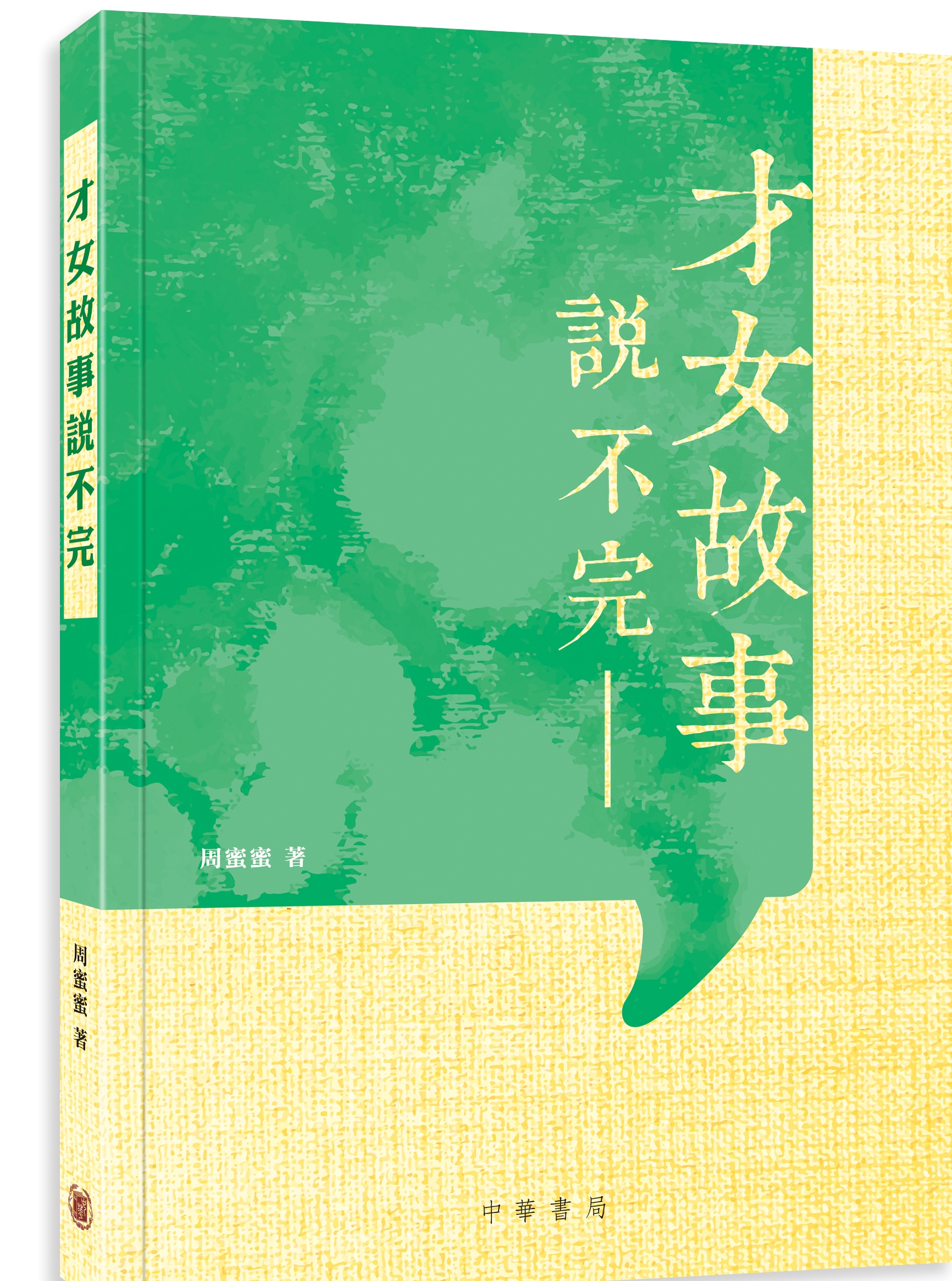淵懿
出生於封建地主家庭,九歲喪母,終究無法忍受和面對專橫父親、冷漠繼母的蕭紅決絕地選擇離家出走,終其一生都在貧困和坎坷中顛沛流離,跌宕起伏。十年文學生涯,創作百萬文字,被譽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一九三五年第一次以筆名蕭紅發表中篇小說——《生死場》,從此登上文壇。
《生死場》共十七章,前十章描寫愚昧保守的東北鄉民忙著生死的日常,第十一章到十七章講述「九一八」事變後,村民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的悲慘生活和漸漸覺醒的反抗意識。正因為這部作品的內容有兩個不同的面向,因此問世以來的研究也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蕭紅於一九三四年完成《生死場》寫作,第二年魯迅以《奴隸叢書》的形式出版發行。魯迅在小說序言中寫道:「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添了不少明麗和新鮮」(衣俊卿、潘春良、李曙光等編著:《蕭紅全集一》,頁四一),胡風在〈讀後記〉中寫道:「這些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們就悲壯的站上了神聖的民族戰爭底前線。蟻子似的為死而生的他們現在是巨人似的為生而死了」(《蕭紅全集一》,頁一三三)。正是有了這樣兩位文學巨匠對文本的定調,因此《生死場》自面世以來便被「抗日」和「革命」的主題所傳播和解讀。第二個時期:八十年代初掀起的改革開放打破橫亙在中西方之間的塊壘,中國社會從政治到經濟民生等多個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那些曾經登上舞台的許多現當代文學作品漸次退出讀者視野,而蕭紅創作的包括《生死場》在內的作品,不僅沒有被歷史的長河淹沒,反而日漸受到讀者熱捧,因此單一從「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的層面詮釋這部作品,雖然有其合理性,但顯然不足以闡釋其作品的豐富內涵,於是,研究者藉助西方文學思潮湧入,從多維度重新開掘和審視《生死場》的內涵和外延。

蕭紅《生死場》共十七章,前十章描寫愚昧保守的東北鄉民忙著生死的日常,第十一章到十七章講述「九一八」事變後,村民們在日寇鐵蹄蹂躪下的悲慘生活和漸漸覺醒的反抗意識。(資料圖片)
通過查閱近二十年有關《生死場》的研究文論,發現研究者主要從作品的敘事結構、風俗文化、鄉土意識、悲劇意識、人道主義特別是女性主義等諸多角度以及蕭紅與同時代的魯迅、丁玲、關露、沈從文、蕭軍等作家進行橫向對比的面向進行研究,前人豐碩而多元的研究成果對本論文的撰寫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引、借鑑和參考作用。本人通過細讀文本認為,蕭紅《生死場》這部作品通過散板式的生活場景拼貼,不僅刻畫了以抗日背景下東北人民在艱難困苦環境中的生死日常,還通過文本構建了一個個令人窒息的女性死亡圖景:無論是不足月的幼女、走入婚姻的少婦,還是正在求學的女生以及頭髮花白的老婦,都在以不同方式淒慘地走向死亡。胡風在《生死場》〈讀後記〉中也寫道:「糊糊塗塗的生殖,亂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動在自然的暴君和兩隻腳的暴君的威力下面。」(《蕭紅全集一》,頁一三二)基於以上考量,本人期試圖站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以女性「死亡」書寫為切入,運用不同研究方法,將蕭紅通過自身生命體驗和經歷,對男權社會下女性生的堅強、死的掙扎以及向死而生的死亡圖景逐層進行分析梳理,從而讓讀者更為深刻解讀蕭紅《生死場》中所書寫的女性生存的巨大苦難以及對男權社會的無情鞭撻和控訴。
女性與五種「死亡」
「兩隻蝴蝶飛戲著閃過麻面婆,她用濕的手把飛著的蝴蝶打下來,一個落到盆中溺死!」(《蕭紅全集一》,頁四四),隨著《生死場》中這個具有女性意象的美麗蝴蝶死亡,蕭紅以最直觀也是最殘忍的筆觸,向我們構建了一個個瀰漫著死亡氣息的「生死」場域。
一、幼女之「死」
第一章《麥場》開篇,王婆的幼女就不小心跌在鐵犁上橫死,如同小狗給車碾軋死了,「她的小手顫顫著,血在冒著氣從鼻子流出,從嘴裏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斷了」((《蕭紅全集一》,頁四十八),然而身為母親的王婆沒有為孩子的死亡而慟哭嚎叫,只是「起先我心也覺得發顫,可是我一看見麥田在我眼前時,我一點都不後悔,我一滴眼淚都沒淌下」。(彭放、曉川主編:《蕭紅研究七十年一九一一-二○一一(下)》,頁四十八)在蕭紅近乎冰點的敘述中,讀者還未從幼女死亡的悲痛中脫離,便又被王婆的無情所驚詫。可是驚詫之餘再回到文本中的時代大背景,又不得不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活著已是不易,人死了只能和動物一樣,再說死去的還是個女孩子,在當時重男輕女的社會便更不值得可惜了。接下來的日子,人們照舊要忙著吃喝,忙著生養,忙著掩埋豬狗不如的死人。畢竟「農家無論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蕭紅全集一》,頁五九)這是蕭紅在開篇所發出的——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生而為女」將是一個怎樣的大悲哀!
二、婚戀之「死」
金枝是小說所描寫的女性中,唯一能自覺衝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帶著愛的喜悅和青春慾望,在一個叫成業的農村男子婉轉的口笛和響鞭聲中,覓尋著心嚮往之的幸福生活。可是,當成業把自己要娶金枝的想法告訴叔叔福發時,福發卻搖著頭問道:「小姑娘到咱們家裏,會做甚麼活計」(《蕭紅全集一》,頁五五),由此可見,在福發世俗眼中,二人是否般配並不重要,女子首先必須是一個可以勞作的工具。如果說福發屬老於世故,精於算計,那麼作為年輕的成業對待女性是否又如他的口笛一樣清新迷人呢?當金枝與成業偷食禁果懷孕後,金枝帶著恐怖和顫索的心提出結婚時,成業卻完全不關心金枝的境況,還扔下無情的話語:「管他媽的,活該願意不願意,反正是幹啦。」(《蕭紅全集一》,頁六一)在封建傳統社會,一個女子未婚先孕是被世人道德所不容和唾棄的,金枝就如魯迅筆下〈娜拉走後怎樣〉中的娜拉,面對愚昧封閉的社會,被啟蒙的娜拉尚且無路可走,那麼任憑命運擺佈而毫無還手之力的金枝又怎麼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金枝母親一早就給金枝嘮叨,當年成業的嬸嬸就是和福發偷吃禁果,而在全村都抬不起頭,因此在金枝母親眼中,與成業家結親不僅沒有可能性,甚至是一種羞辱。可是當肚子一天天鼓起來的金枝不得不把懷孕的真相告訴母親,她以為必定會招致母親惡虎般的撕咬踢打,不曾想,原本堅決不同意這樁婚事的母親卻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好像本身有了罪惡,立刻麻木著了,很長的時間好像不存在一樣」(《蕭紅全集一》,頁六一),因為在滿腦子裝著三從四德的金枝母親看來,女兒已經失去了女人最為寶貴的貞操,當下最要緊的就是設法盡快了卻這樁見不得人的醜事。
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金枝惶恐地嫁給了成業,便也從此徹底進入男尊女卑的夫權體制。不懂愛情只有動物本能的成業,在滿足生理需求之餘,對金枝除了沒完沒了的怨恨和折磨,就是肆無忌憚的虐打,最後連同剛滿月的小金枝也被暴跳如雷的成業活活摔死。
後來成為寡婦的金枝決定離開傷心地到都市求生。然而命運的魔鬼哪能輕易放過她,她雖小心萬分,僥倖躲過日本大兵的魔爪,但一個年輕寡婦又哪能躲過被男人強暴的悲劇。更為可悲的是,當金枝在城裏通過出賣肉體和尊嚴換了幾個小錢,回到鄉下把錢交給母親,貪婪的母親眼中沒有比金錢更能給她帶來快樂,「母親不注意女兒為甚麼不歡喜,她只跟了一張票子想到另一張」(《蕭紅全集一》,頁一二一),於是,她「快樂而不自制地說:『來家住一夜明日就走吧』」(《蕭紅全集一》,頁一二一),本想從母親這兒獲得些許撫慰的金枝徹底失望了。
從鄉村逃往城市,又從城市逃回鄉村的金枝還能往哪裏去呢?孤獨無助的金枝想就此遁入空門尋求宗教的救贖,然而廟庵卻早已空了。金枝的路在哪裏?只懂得順從、忍耐而沒有反抗意識的金枝是不知道的。蕭紅試圖通過金枝遭遇向不公平的男權中心社會發出強烈控訴,試圖喚醒女性的反抗意識,試圖向整個社會發出憤怒的呼喊,沒有女性的徹底解放,「啟蒙救亡」的價值將大打折扣。
三、家庭之「死」
家是遮風擋雨的港灣,也是走投無路女人的最後避難所,然而蕭紅筆下的家卻是逆來順受,飽受摧殘的女性上演令人窒息的「死亡」場所。
月英曾經是「打漁村最美麗的女人」(《蕭紅全集一》,頁六九),卻不幸患了癱病常年臥床不起,「起初她的丈夫替她請神、燒香,也跑到土地廟前索藥」(《蕭紅全集一》,頁七○),後來看著月英病情不僅未見好轉還一天天加重,於是對身邊這個女人討一碗水喝的請求也懶得搭理,「宛如一個人和一個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關聯」(《蕭紅全集一》,頁七○),丈夫甚至把月英的被褥換成冰冷的磚頭圍住月英,讓她自生自滅。在丈夫的眼中曾經青春貌美的月英已經無法滿足自己性的需求也無法滿足傳宗接代的目的,她的價值便連「工具」也算不上了。月英那對原先多情、愉快、溫暖的眼睛不見了,白眼珠和牙齒變綠了,頭髮燒焦了似的,排泄物淹浸了骨盆,臀下的白色小蟲在活躍……最終打魚村最美麗的女人,以最醜陋的模樣離開了人世。
《生死場》中無論是福發嬸,還是五姑姑以及她的姐姐,在家庭中不都扮演著男性的奴隸和泄欲工具嗎?福發嬸看見福發好像自己變成一隻小老鼠:「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塊一般硬,叫我不敢觸一觸他」(《蕭紅全集一》,頁五四);五姑姑的姐姐在丈夫的眼裏根本就不是個「人」;五姑姑的境遇雖比姐姐好一點,但在粗魯的丈夫面前,她依然是柔弱的,「垂下頭,和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蕭紅全集一》,頁一二八))。
蕭紅透過一個個家庭悲劇,揭示出冷漠粗暴的夫權對女性的巨大摧殘以及給女性帶來的巨大悲苦,表達了她對女性生存困境的無比同情和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和無奈。

蕭紅透過一個個家庭悲劇,表達了她對女性生存困境的無比同情和對女性問題的思考和無奈。(資料圖片)
四、生育之「死」
《生死場》中,蕭紅不僅看到了貧困、疾病和男權對女性的壓迫和摧殘,還以自身遭遇和經驗控訴著一位位女性無法擺脫的宿命——觸目驚心的生育之「死」。
金枝、李二嬸、麻面婆、五姑姑的姐姐、二里半的傻婆娘哪一個又能逃出「刑罰的日子」,她們生育時的慘叫讓人掩目、不忍卒讀。五姑姑的姐姐為了避諱生育時「壓柴」便不能發財的窮講究,只能在揚著灰塵的土炕上光著身子,「和一條魚似的她爬在那裏」(《蕭紅全集一》,頁八○)生產。由於難產,女人忽然苦痛得臉色灰白此時全家人不是急著為她挽救生命,而是忙著預備葬衣。第二天雞叫的時候,在整個生育的悲慘過程缺席的丈夫像一個酒瘋子走進來,他甚麼也不講,一邊罵她裝死,一邊用長煙袋投向那個在血泊中垂死掙扎的女人。產婆讓她站起來走走,「她的腿顫顫得可憐。患著病的馬一般倒了下來」(《蕭紅全集一》,頁八一),孩子生下來就死去,產婦「橫在血光中,用肉體來浸著血」。(《蕭紅全集一》,頁八二)蕭紅將自身的生命體驗和慘痛的生育經歷投射在一個個產婦身上,用「越軌的筆致」把婦女在生育過程中所不能承受的生理和心理的巨大悲痛血淋淋呈現在讀者面前,令人不寒而慄。其實村裏的接生婆又能為產婦們做些什麼呢?正如王婆所說:「這莊上的誰家養孩子,一遇到孩子不能養下來,我就去拿著鉤子,也許用那個掘菜的刀子,把孩子從娘的肚裏硬攪出來。」(《蕭紅全集一》,頁四八)蕭紅筆下所構建的這片淒苦土地上,生育不再與甚麼「偉大創造」之類的讚詞有任何關聯,由於傳統的生育觀念,幾乎赤貧的生活現實,極度落後的醫療條件,使得生育成為女人一生中一場接一場的大災難,僥倖躲過死亡就繼續生,因生而即將死亡的就要趕快徹底死掉,人們沒有耐心去陪伴一個個生命的慢慢逝去,祖祖輩輩的女人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代復一代地上演令人慘不忍睹的「刑罰」悲劇。如此驚心動魄,殘忍而荒誕的生育場景,沒有與此有同樣生命體驗的男性作家所進行的書寫,無論如何也是難以企及的,可以說這也是蕭紅對女性文學書寫的一大突破和進步。
弔詭的是,文中在描寫女人「受刑」的同時與之交叉出現的是動物的繁衍場景:「房後草堆上,狗在那裏生產。大狗四肢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的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牠多數的乳房有什麼在充實起來。」(《蕭紅全集一》,頁八○)「人們來到人間,在一定的環境中生活,在生死場上喘息著、繁忙著、掙扎著,和動物的繁殖、交配、生產的畫面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古老民族的原始幻滅」(《蕭紅研究七十年(下)》,頁三五)。
其實《生死場》中的人和動物有甚麼不同嗎?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女人的境遇還不如動物,她們比動物更悲慘,女人除了忍受生育本身帶來的生理痛苦,還要同時承受男權肆無忌憚的心理摧殘和折磨。其實在蕭紅筆下這些女人早已是一隻隻不同的動物:麻面婆的喉嚨總是發出豬的聲音;老王婆是一隻貓頭鷹;金枝是隻小雞;金枝的母親是貓;五姑姑是隻小鴿子;五姑姑的姐姐是一匹馬……女人作為一個個溫順的「動物的人」的存在,不得不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更加惡劣的男權縫隙中苟活,她們深入骨髓的痛苦似乎和「痛苦」的本意無關,她們充其量是個沒有簽下賣身契的奴隸罷了。
五、向「死」而「生」
《生死場》中王婆是一個貫穿始終的獨特女性人物,也是一個「異類」般的存在。她是村裏唯一的接生婆,見證著村中所有生命的降臨,她還是全村唯一一個敢於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進行抗爭的人物,「全家人的衣服她不補洗,她只每夜燒魚,吃酒,吃得醉瘋瘋地,滿院、滿屋地旋走」(《蕭紅全集一》,頁九三)。不過這個如此獨特的人物,其命運也是歷經坎坷,一波三折。開篇王婆的幼女便意外死亡,不向命運低頭的王婆面對暴躁丈夫,並沒有選擇從一而終,而是決絕地離開,在遍嘗人間苦難後嫁了第三任丈夫趙三。當她得知兒子因當「紅鬍子」被官府槍斃,痛不欲生的王婆服毒自殺。服毒後的王婆臉是紫色的,「但微微尚有一點呼吸,嘴裏吐出一點點的白沫」(《蕭紅全集一》,頁八七),丈夫趙三已經等待得極不耐煩,於是:
趙三用他的大紅手貪婪著把扁擔壓過去。扎實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間。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漲,像是魚泡似的。她的眼睛立刻圓起來,像發著電光。她的黑嘴角也動了起來,好像說話,可是沒有說話,血從口腔噴出,射了趙三的滿單衫(《蕭紅全集一》,頁八九)。
如此懾人心魄的描寫,這便是宰殺動物也是慘不忍睹,可是蕭紅便就是這樣直觀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不是作者的殘忍,而是殘酷現實便是如此。經過如此一番折騰又死而復生的王婆便從此走出生活的羈絆,開啟與命運抗爭,與生死抗爭的更加堅強的生命追求。
她在得知女兒為了給哥哥報仇死於鬼子的槍下後,她用十年前支持丈夫組織「鐮刀會」一樣的膽識,沉著冷靜地應付搜尋鬍子的日本兵;當組織敢死隊打日本鬼子時,她和寡婦們在宣誓的時候先於男人發出響亮的回答——「千刀萬剮也願意!」(《蕭紅全集一》,頁一一一),這一幕的出現給《生死場》原本淒涼悲痛的灰色基調平添了一抹難得的亮色,不僅讓人想起魯迅筆下《藥》中夏瑜墳頭紅白相間的花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蕭紅以王婆為代表,表現出底層女性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這在當時的社會是有相當的突破和進步意義,其實反觀當下社會,這樣的女性抗爭意識依然有其不可低估的現實意義。
結語
以上對文本「死亡」書寫的梳理中不難勾勒出《生死場》所構建的這樣一條女性死亡脈絡:幼女之「死」→ 婚戀之「死」→ 家庭之「死」→ 生育「之死」→ 向「死」而「生」,從中你會驚奇的發現,開篇就意外失去幼女的王婆,又在後文中死而復生,那麼復活的是王婆本人,還是幼女的魂魄附體,如果相信佛家的輪迴,那麼在《生死場》中便巧妙形成了女性的死亡循環。當然這樣的解讀也是一家之言,蕭紅畢竟不是魔幻書寫,不過無論如何詮釋,有一條是繞不開的,那就是——《生死場》中所構建的女性在她生命的任何階段都會面臨死亡,都在與死神抗爭,即使在成長過程中僥倖躲過一次次死亡威脅長大成人,也只能在男權的壓迫縫隙間,用性慾的滿足、繁衍後代的工具和沒完沒了的勞作苟活人世。她們若想以一個人的姿態存活,就要如王婆一樣敢於掙脫封建社會的枷鎖鐐銬,在生死中掙扎,生死中反抗,才是希望的唯一所在。
綜上所述,蕭紅以女性的悲憫之心在《生死場》中用「越軌的筆觸」向讀者書寫了東北鄉村日常生活場景中最底層女性生存的深重苦難和悲哀,以她女性的敏銳感覺和閱盡人間滄桑的人生體驗,在書寫底層民眾生的堅強、死的掙扎的同時,對封建社會的男權世界進行了血淋淋的控訴,對造成女性悲劇命運的社會倫理道德根源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深刻揭露。
淵懿簡介:本名袁疆才。七十年代西北邊陲呼喊著跌落人間,隴上人家馬不停蹄野蠻生長。當下,垂釣香江,文字覓春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