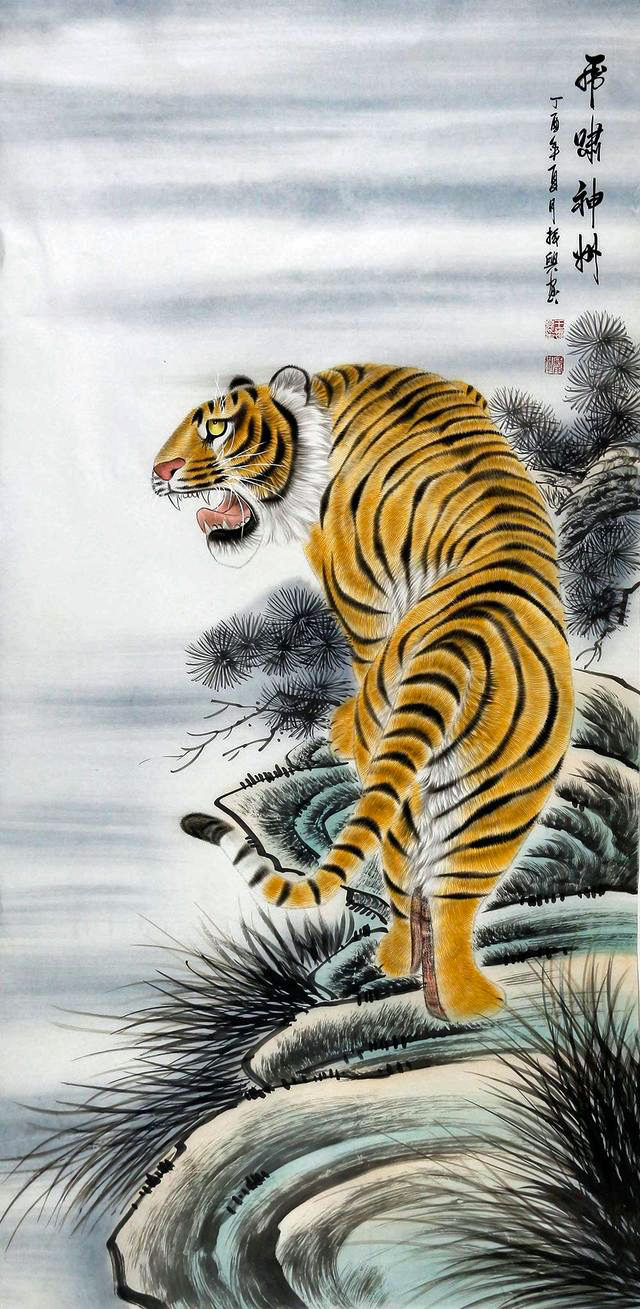黃耀輝
辛丑年十一月十五,是公曆二○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個極度平凡的普通老師靜靜地走了,無聲無息,讓我愕然。無論是手機、還是朋友的微信圈,即使同學間,或是曾經的工友,都沒有人知道。
何老師走的這一天,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柬埔寨首都金邊進行回國前的緊張疫情「隔離」,等待十九日最後官方核酸檢測後進入酒店封閉隔離,二十日血清抽驗,二十一日晚向中國大使館申請「綠碼」,二十二日登機飛抵國內指定的入境海關四川成都……
何老師在我心中的位置從來沒有撼動。二○二二年一月二日農曆十一月三十日晚九時多,在隔離酒店裏,我從手機裏找出電話打給何老師,對方「大眾小姐」說「關機」。於是,又極度平靜地找出小何老師的電話打,很快,傳來對方低沉的語調:黃大哥,我爸爸走了。秉承父業的小何老師後來告訴我,爸爸走後,我沒有告訴他的學生……
何老師一九四八年出生,二○一四年小腦出血治療後康復。二○一六年我奉命出任中新社柬埔寨分社社長前夕,春節期間還與同學蘇中波在韶關專程到府上拜訪了他,談笑風生……我愣住了,把斜躺的身體調好。什麼時候?我問。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小何老師回答的很平靜:醫院診斷心臟病發作導致。
我仔細回看「黃曆」,操,原來「諸事不宜」,即使打電話都倒霉!
一
一九七一年十月後,全家從韶關「紅工礦務局二礦(後更名:曲仁礦務局)」隨父親調動遷至「紅工六礦(後更名:紅尾坑煤礦)」時,我正上小學四年級。由於是新礦,沒有礦辦子弟學校,煤礦的孩子都寄讀在曲江縣龍歸公社社主大隊學校讀書,作為回報,礦上也會派一些「優秀青年礦工支教」。大約是一九七三年上半年,何老師來支教了,但還沒認識「老師」又走了,後聽說,他是回礦裏籌備子弟小學了。真正認識他是礦裏白天舉行的一次籃球賽。一九七二年底,全家從「東礦區」臨時住地搬至「西礦區本部」後,新家門前有一個新建的籃球場。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的一天,在門前的籃球賽場上,我記住了球場上「東竄西忙」的人。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礦辦子弟學校開學後,他成了我的老師,叫何益忠。學校學生不多,一至五年級各一班,我們班的五年級是學校的「老大班」。學校老師不多,何老師語文、算術、唱歌、美術、體育都教,在學生眼裏就是「不得了」。當然,學生最喜歡何老師的「體育課」,可以放羊式地「玩」。小孩那喜歡「翻跟頭」,何老師把「墊子」一鋪,讓我們挨個跳木馬、「翻跟鬥」……
何老師年長我十一歲,除師生關係外,更像大哥帶小弟玩,晚上吃過飯還到學校一起鬧。當時,同學蘇中波還在龍歸公社馬渡學校上初一,偶爾他帶上在韶關讀書的哥哥到學校和我們一起玩,但玩著玩著,他們就私下給何老師起了花名,背地裏叫何老師「方木頭」,意思是「翻跟鬥」的動作彆扭,不夠標準。那會,除了書本上,專業知識沒有來源渠道,在我們一群孩子眼裏,何老師的一招一式最標準,不理什麼「方木頭」啥意思,很少跟著叫的 。
礦裏學校辦起「初一」後,中波又轉回礦裏重讀,我們成了同學,還有一個叫張煉生的,原本我與他倆妹妹是同學,從此成了師妹。礦新子弟少,我們初一班僅二十六名男女同學,「調皮」的男生不多,活躍的不到六人,六名男同學後來成了全校的各種競技的勁旅代表,征戰全域各礦中學生競技場。過去的「外號」忘了,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記得什麼原因,又稱他「何老總」,師生關係「一團和氣」,亦師亦友,叫到學生的孩子還在叫。起先他不接受,但全礦上下都在叫,附近農村的大小農民也叫順了嘴,後來何師母也接受了:「何老總,去學校了!」
多年後,我寫了一篇短文見報,題目就叫「何老總」,他看到後很開心:師生一場呀。

何益忠老師。(作者提供)
二
何益忠,平凡的讓人過目就忘,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很難在人群中發現他的存在。但在同學中間,當年的每一場競技,何老師都是現場的「定海神針」,什麼團隊精神、什麼拼搏毅力,他一個眼神就讓場上的學生悟道,並發揮的淋漓盡致……根本不是如今自封「磚家」說的,什麼人生格言、什麼目標追求……全是胡說八道的「心靈雞湯」。
當自己職業生涯一次次「涅槃重生」,最終效力國家通訊社「開疆拓土」,成為外交新聞「發言人」後,越發感到何老師當年培養的真諦:競技場上沒人可憐「過程」,拼的是真功夫,講的是毅力,要的是結果。
「何老總」絕對是「遊擊隊」出生,到礦裏工作前,挺多就是曲江縣千萬「馬壩人」後裔中一個有文化的普通農村青年,但在同學眼裏,何老師的體育知識很專業。多年後才知,為了教好學生,他的專業知識都是從自學鑽研而來,有文化的人,玩體育還不行,還要看悟性,有悟性才有潛力。後來看到國內媒體介紹風靡一時的「馬家軍」田徑隊,如何因地制宜發明食譜和訓練器材時,我卻不屑一顧,當年何老總早就這麼做了。印象最深的是田徑起跑器。學校沒有錢,何老總就找礦裏的木工師傅自己做。學生看不上,他就說,再好的器材不是目的,結果最重要。
那年月,學校不正經地學習,我們就正經「玩」,何老師就認真地教,教同學們在籃球場上的基本功和「戰術」,教如何「穿插」和「突破」,教同學們如何打得全域各校中學生籃球隊暈頭轉向,雄踞亞軍,教師弟們後來居上,一個班就登上冠軍寶座,教得讓全域各校從百名學生中挑出的「精英」刮目相看,教得許多「老礦」的同學見面也驚訝:想不到小弟弟的礦惹不起了!多年後,師生一起回憶,嬉笑許多同學至今仍是全域中學生競技的紀錄保持者,可惜全域煤礦徹底關閉了,學校解散了。
一九七六年沒有考大學之說,高中四個月後,當年底就毅然棄學挖煤。沒想到,一九七七年底又恢復了高考……本來就沒有文化基礎,讀書時代又混在了競技場上,唯一是看到了文學藝術復興的曙光……有一次,我拿著自己寫的「小說」請教他,他說,「編」得可以,但關鍵地方編得不真實……突然,他問我,為什麼配音電影還要「導演」。簡單地說是為了包括藝術效果的統一,我說。後來他告訴我,他看到了我在市裏報紙發表讚美老師的詩歌。那是我與文字打交道後唯一發表的詩歌,從此再無「詩眼」。
當時,我正在尋找自己的「出路」,但條條大道荊棘滿眼,唯一對自己充滿信心的就是「不服輸」,不拿「過程」當回事,把當年學生時代的競技場拼搏,演繹成人生的追求成敗,看「毅力」的結果。一九八五年,我成了上海戲劇話劇導演系在廣州招生點僅有幾個專業合格生之一;一九九二年,紡織女工系列小說《女性世界》,獲廣東省一九九二年度期刊優秀作品二等獎……這些,都不是結果。
怎麼樣的人生格局,決定了怎麼樣的人生。不知道的以為是運氣,其實,正是當年何老師在競技場上的引導和培養拼搏精神:教練說的再好,都不能替代場上的選手,要打出基本功的同時,更要展示選手的悟性,競技場上別信「參與過程」,講的是實力和結果!
人生又何嘗不是如此!我一個從地球深處挖煤走上來的「礦二代」,靠的就是當年學生時代競技場上勤奮和悟性,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一生的堅定毅力和追求。我常想起,何老師在競技場上有「定海神針」般的眼神!
三
或許是師生情緣,或許冥冥之中的知感。二○一四年何老師大病一場後,按時休息成了何老師家的定律。以往春節期間打電話給他,都是師母先接再通報,何老師聞訊後高興地從床上起身接。每次聊完,還不忘叮囑,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體。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微信,沒有問,更不想過多地打攪他。
在韶關工作時,每逢過年回礦山看父母,也不忘上何老師家拜年。後來工作單位越來越「南移」,離家越來越遠。父親走後,就把母親接到了工作住地肇慶一起生活,但每年過年,我都不忘打電話祝福,銘記一生的師生緣。即使常駐國外工作後,每年回國述職,我都保留這種習慣,打個電話,聽他說:你小子還好吧……
二○一六年春節期間,我和夫人與同學蘇中波夫婦一道上韶關,晚上專程登門拜訪何老師和師母。我告訴他,我將奉命駐柬埔寨工作,有幾年春節回不來了。臨出門時,兩個學生還把何老師「夾在」中間照了一張。轉身那一刻,我看見他眼眶已閃爍著淚花。這淚花,讓我瞬間想起當年他在礦山和我說的一件事:那一年,他在礦山家門口散步,遠遠看見兩個當兵的過來,他想繞道走。他說,沒想到對方看見了他,幾乎是小跑地在他面前「啪」的一聲立定,倆人行了一個軍禮,說,何老師好,我們是你的學生,也是當年校籃球隊的學生娃的兄弟倆。他有些激動地閃著淚花回憶說,學生都是大軍官了!
何老師說的軍官兄弟,正是當年礦山「東區臨時房」我家的鄰居,我女同學的弟弟,當中一個已成了職業軍人在副軍級技術崗位退休。二○二二年元旦當日,我們還通了微信電話,問我什麼時候解除隔離。那會,我還沒有與小何老師通電話。
二日晚,何老師手機「關機」了,我隨即找到小何老師的電話,得知了噩耗。我寧願相信小何老師在騙我,立馬翻出手機的微信群……撥打蘇中波同學的電話,對方驚訝地說:沒聽說呀,稱前段時間礦山退休群還發出何老師他們一起樂的視頻。
還是為了證實,當晚我又發了一條信息給小何老師:能發幾張何老師的照片來嗎?
三日早上,手機裏傳來信息,收到三張圖片,留下一段話:大哥,父親很少照相,只有三張。僅有三張?何老總生前的照片就三張?他桃李滿天下,不乏攝影人,可他從不找學生……寧願這樣靜靜地走,低調地走了在新年前,彷彿在說,忘了你們的何老師吧,你們的「何老總」想休息了。
原本想告訴何老師,那年春節師生三人的合照,已收入學生《中國老記的高棉拾筆》中文版集子,獲批柬埔寨國家統一書號公開發行了……
可惜,天堂沒有手機!
二○二二年一月三日晚 成都大邑隔離酒店
黃耀輝簡介:資深媒體工作者、原中國新聞社柬埔寨分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