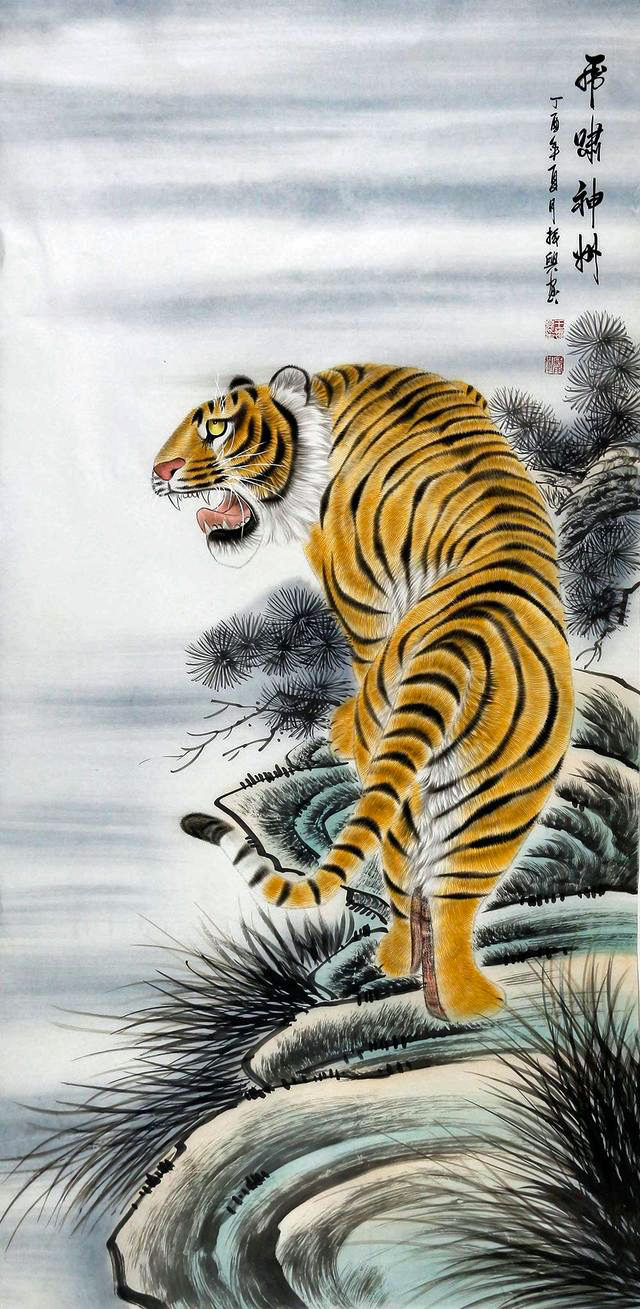楊潤樺

屯門藍地水塘。(資料圖片)
那是冷空氣躲懶的一天,陽光包裹著四肢百骸,連頭髮絲都被烘烤出金黃得有些透明的質感,我急沖沖地往藍地水塘山腳奔去,赴一個推辭了許久的登山之約。
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我下意識做了以往不屑的舉動,往臉上戴了很多個面具,高興的、健談的、開朗的、害羞的、溫柔的......這些矛盾著的面具被我強行擺在一張化了精緻妝容的我的臉上,層層疊疊,沒有露出蛛絲馬跡,也意外的契合,我隱秘的沾沾自喜,自以為塑造了一個良好的形象,直到我看見了那棵樹。
它臨著藍地水塘而生,樹幹較其他的樹有些纖細,枝葉卻分外的繁雜和舒展,斜斜的伸進水塘的上空,彷彿一個舞者在伸展,枝幹是她的雙臂,樹葉是她的衣裙,投在水面的影子是她輕柔動作的餘韻,影影綽綽,隨波而動。我沉浸在這優美的演出裏,久久回不過神來,直到被喊著不要掉隊時,我瞄見了她裹著的一層又一層的樹皮,外面一層的灰白中夾雜著風塵侵蝕後的點點黑斑,有些似掉不掉的半掛在裏面乳白的一層,就像似溶洞裏的鐘乳石,長年的堆疊,覆蓋,新舊混雜,竟有些許的猙獰,但經不住風一吹,顫抖得厲害,老舊的那層快要隨風而去。我的心頓時發出咚咚咚的迴響,倏的回頭,是被那聲催促驚動,還是徬徨於那一小片即將失落在水面,漸漸被浸潤而消失的樹皮。我的面具還在嗎?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往水塘的方向一撈,隨即放下,驚懼什麼呢?且生長著呢,不論是她的樹皮還是我的面具。
初次相遇後我再未想起過她,大概是她的樹皮讓我瞬間直面到自己也許並不如想像中完美無缺的面具吧,可與那種沁人心脾的優美姿態共生著的崎嶇褶皺樹皮,給我心底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跡,不知道是害怕她的樹皮?還是厭惡我的面具?我選擇了刻意忽視,但轉頭卻被牢牢強調,在自然寫作的第一節課上。我期待著這門會去田野調查的課程很久了,卻沒料到第一站是藍地水塘,命運般的再次駐足在她的身邊。
「我們去那裏拍照留個紀念吧,正好我想介紹一下。」老師指了指她,「這是白千層,樹皮一層一層的不斷蛻不斷長,而且葉子汁液提取可以做精油,有安神舒緩的功效」,說著一邊摘下一片葉子,對半撕開,讓我們聞一聞。
我放到鼻端,一股清新中帶著絲絲苦的芳香瞬間沿著我的脊柱衝進神經中樞,很不同,與雜亂疊著的樹皮,這是魅惑的。誘著我再靠近她一點,摘一片葉子,但她周邊圍著很多興致濃濃的同學,沒有可以插入的縫隙,我扶著樹幹,幾番嘗試後放棄了,回身時卻覺得手下的觸感很柔軟,是樹皮。手指微微往下陷,我忍不住用力蹭了蹭,是乾淨的,只不過看似污糟罷了。我不由自主地攥緊手裏破碎的葉子和軟滑的觸感,希望能夠帶著她們回家。一路上都不敢輕易鬆手,生怕留不住。但很可惜,還未下至山腳,就都消散在來時的路上,葉子斷開處的汁液也乾了,我嗅了嗅手心,是太用力後微微滲出汗液後的些許酸,不同第一次被洞察後的倉皇轉身,我在遺憾中釋懷了,美麗與醜陋從來都不是對立的,面具與真實也不會自相矛盾,總害怕會在偽裝中逐漸忘記自我,唾棄虛假卻又無法丟棄,卻忘記了,美與醜的融合,假與真的交織,都在證明著我在不斷的成長。於是,我開始想念她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遇見了今天一同上課的同學,她手上捏著眼熟的葉子隨著步伐輕輕跳躍著,我上前打招呼並自然的聊起今日印象深刻之處,情不自禁的表達著對她的喜愛,同學表示想送給我,驚喜之餘竟然有種奪人所愛的羞愧,畢竟,彼時樹下的喧嘩都在昭示著她的受歡迎?
我把意外獲得的這一片葉子種在日記本裏,想像著再次打開的時候,會聞到一片成熟的白千層林,盈滿我的過去,現在,陪伴著我的未來。

城門水塘水浸白千層樹林。(作者提供)
我搜尋附近的白千層,發現城門水塘有一整片的白千層林,於是約上友人一道同行。到時發現這裏的白千層每一棵都筆直得直衝天際,就連枝葉都不願低頭半分,一個一個爭相往天空攀去。我很想摘一片葉子,聞一聞是否是懷念但氣息,可惜,任我似猴一般蹦躂,抓住的都只是撼動後灑落的塵土,我不甘心,圍著整片林子轉悠,最後終於在一個低窪處見到了新生的樹枝苗,低低的,我燃起了希望,但走進一看,發現即使是幼苗,但仍比我高出二十厘米之餘,我只能借力延出身子夠,終於夠到了一片嫩葉,放到鼻尖,不是想像中的味道,更不是記憶中的味道,我疑心自己找錯了樹,但手裏摩挲著樹幹褪下的舊皮,如紙般柔軟,沒有錯。是什麼讓同樣的樹散發出截然不同的味道?土壤?氣候?水源?還是......亦或是她自己。她不願如藍地水塘的白千層一般親近著水面,而是想追逐著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鳥兒,所以竭盡全力的向上生長,即使這使她與其它的白千層格格不入,但這也恰恰顯出她的獨一無二,不是因為樹皮,也不是因為汁液的味道,只是因為她自己,所以,眾人臉上面具的更替,並不醜陋和猙獰,反而是獨一份的,而我的這個,也正正使我,顯得更加是我。
回去的路上心裏縈繞著溫暖的慰藉感,彷彿找到了似我、明我,可以訴說心事的人生知己,按捺不住的想雀躍歡呼,心裏盤算著下次看望她的時間。
卻有一日在走了千百遍的紅綠燈口神遊時,發現了三棵不知注視了我多久的,被我視為好友的白千層,掩藏在一些不知名的草木之中,分外沉默和透明,樹皮一如既往的卷起過去的歲月,可惜,樹葉不是我所能觸碰到遠方。忘記過去了多少個綠燈,只記得仰頭後脖子留下的久久不去的酸脹感,我記不清是在看樹,還是在看映著樹的天空,也許都不是,我只是在看,看樹時的我的迷惘。天空的枝杈化作即將畢業的未來交叉口,我陷入茫然與不知所措的懈怠中有段時間了,正在張惶地左顧右盼時又碰見她了。每每遇到她時,總是在意料之外的時間和地點,卻次次都能讓我思緒翻湧。
其實,不論是藍地水塘向著水的白千層,還是城門水塘向著天的白千層,亦是在紅綠燈口甘於沉寂的白千層,他們都是白千層,卻也都不只是白千層,因為不同堅持造就了她們的特別,我會找到我的方向嗎?會的。起碼我知道了我想往何處紮根,往哪片天空生長。
楊潤樺簡介:嶺南大學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