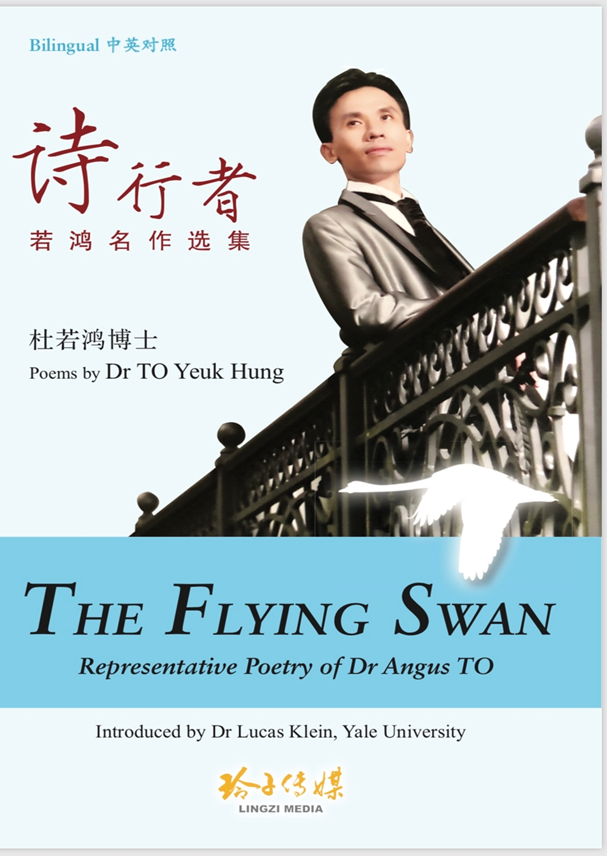梁 晚
「我做了一個傷心的夢。」這是她半夜三點給他最後的留言,然後,她就此消失沒有再出現過。
現在他打算背起書包,下決心去尋找她。她消失的這一個月裏他什麼都沒有做,她早已經變成了他生活的全部,所有事都是為了對她說,為她想,感受她而發生的。如果他再不行動,他的生活會到此結束一切停止下去。他別無所求只為愛情(如果這是,他找不到更好的總結)而活,沒有額外的期待,或者說他本來就沒有期待,是他發現了一種發覺並且只屬於自己,如果不是因為她突然消失,他不會有任何行動,在他心裏幾乎從沒存在相見的衝動,一切原本都讓人很滿足。
可是她消失了。他是知道總會有這種結果的,畢竟他們彼此沒有現實生活的交叉,關於這,會把一場純粹磨滅,他曾經慶幸不已,這是他心中愛得高層的重要地基,所以直到今天,他也沒有打過一通電話一封郵件,事情發生的一周後他就再也沒有別的猜想,電話和郵件都不是必要的,他在等待決心,尋找的動作會將一切都推向中心,似乎早就預備動身。

仰望夜空。
關於他要尋找的這個人,或許他沒有真的認識過她,在社會的層面上他對於她的一切一無所知,這使接下來的這場尋找行動變得像是一個拼圖遊戲,它將完全不完整甚至完成不了。但是他的補充將會充實這幅拼圖背後的整個牆面,他的生活在等待全面的發生,等他造好之後他幻想會成為一條具體的河流,他的循環就在其中得到運行。
晚上,他出門為這次的冒險採購物品。他從來不愛白日出門,夜的世界似乎是一個分裂,相對使它超越現實。他走在夜風中吹來的虛假裏托舉起真實的波浪,越是吹越是感覺到一種輕浮,他為自己即將的出行再次雀躍,而路邊有許許多多不回家的人,他們似乎變成了另外一種路燈,蹲守著在一個個路口,他們的心中有沒有什麼寄託呢?蹲在那裏簡直會產生一種他們是否真的是懷疑,似乎被融化倒膜去一種靜置裏面——倒進去這一天就結束了。藉此他獲得了一種高尚的幸福感,凌駕所見之上,而他在行走如車過風景一般,入眼的都是陳列,思考也顯得表面。夏夜是不是會讓人像那些腐敗的垃圾一樣也極度放縱起來?因為就這不算長的一段路,已經有相隔不遠的兩輛警車在閃爍,那些泛著疲憊油光的警務插著腰想要聽清楚那些激烈的指責和失控,疲憊已經不是重要的事了,狼狽更為難堪,任何人都根本不會聽明白究竟怎麼了。好有趣,相比白日現在更具有活得氣息,人在困境裏面被放大了——不,不是,他想,人的身上如今只因困境而顯得動態,更多的時候,人已經湮滅在這個世界的運動中去了,如果不時刻保持警惕,自己又將去向何處?他在找各種方法不凝固成路燈,能做的極少。但是總不至於讓真實只有在一個時段才能緩慢亮起。
就是夜晚——回到自己的居室是層層掉落中的一環,是在剝玉米吧,從白日到現在獨處的深夜,一層層展露脫離寄主的真實。他躺下,平日此時他在和她聊天,他們彼此陌生又親密。
有一個男孩讓我為他寫下一個故事。我同意了,並且決定可以就此消失在他的眼中。我想,我消失了他會有什麼樣的經歷?就這樣開始寫了第一句。寫第一句的時候我在想要不要有個告別或者留言?不,不了吧。他是虛假的投射,自我的騙局。或許只是充實自己的假裝劇本,自己太枯竭了。能發生的太有限,我要怎樣才能快樂,使自己的耳朵裏不是嗡嗡得鳴響,世界外面,到底什麼樣的?就這樣,由一句成型的話語,導致無數的幻想。
我想,今天又白白過去。幻想沒有價值,只會更加痛苦。
空空如也得空氣和夜晚裏,風環繞我的四周,一點點變冷。奇怪卻又安靜,我在下陷,似乎是在颶風的眼裏,那種底下無限的掉落。這個時候我是多麼想他。我想立馬爬起來,告訴他我在這,我在這。可是一切都不真實,下陷不真實,衝過去的衝動不真實。真實會阻擋我的腳。真實只是一段不可能實現快樂的追尋。他也不是他。我無數次勸導自己由內尋找,卻總是有徒勞的寄望,需要每每克服一遍嗎?
這不是愛情故事,在女主角眼裏沒有男主角,在男主角的世界,女主角是泡影。這只是關於猜測和映射的抓手。我無法入眠,只能由它去,由它剝奪夜晚和自由。把我的渴望和無法言明的吶喊帶到那個底下的無限,我們之間的共同——每當這個時刻都讓人孤單的明白,那是無可救藥的自言自語。只有消亡才能使它類似呈現。
我知道不會那麼簡單,消失和慾望都是反复鬥爭的噩夢。這是一種個人的史詩。如果沉入水底,那麼一切都好辦了。當你把容器灌滿,那重量會消弭一切的疑問,嚴絲合縫的整體不會喪失穩定,液體就是答案——無人問,無人答。充盈將作為整個宇宙。
可是作為人,我此刻握緊的手,蜷縮的心,身體的飢渴,它們壓抑下產生的——抵抗伸出了觸角,完整的如此重要,它是無法掌握的活性分子,任何的動盪,都會挖走我的一塊。
我想,如果所有人都能意識到我如此自私,那是多麼開心啊。
入眠是件難事,今晚我就到這了,否則又是頭痛和失眠。放空之前我在想,我把他給刪除了。他不重要,什麼都不重要。我這樣躺在床上,自己沒有種類沒有實體,沒有液體的空瓶,對。空瓶子。獨自一人時,真空的狀態前所未有的明顯,每一次都是那麼鮮明,從來不會讓你覺得熟悉和過時。我已經想盡一切辦法了,睡覺吧。
然後我就做夢了。
城市到處張貼著我的照片,尋我啟示。
女,封閉者。曾在多處商店盜竊,失眠症。頭髮長,近視八百,從不在飯店就餐。
我想知道她是否還在這座城市。
有線索可撥電話,十分感謝。
傳單發到我的手上,他看著我的臉,說:希望你提供線索。
在場,不在場。我也只能在一種懷疑和委屈中醒來。
很快,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他躺下後,想起她偶爾會念念叨叨,那時就是那天發生了些什麼。她說她在商場盜竊,一塊精品店裏的水晶,一塊零食店裏的糖果,一雙襪子,最難的是一本書。事情完結之後,身體變得很沉,她說。她總是想著之後的事情,對,就是盜竊發生後的事情,不在她的身邊,但是已經有無數事情發生。那很重要,她說。能發生什麼對我很重要。她重複。他沒有一次看見過她的表情,她的臉。但是當她在說這樣具體的事情的時候,他知道她在說一種私密。他就是因為這樣的私密而一點一點的想要做出一點付出,「人是萬物的尺度」——她曾經在留言區留下這樣的帖子。她的帖子讓他想要與她發生的聯繫的慾望一天天在加強,他簡直忘了自己一切的生活——因為本身就曾經什麼都未發生過。他一直這樣無法鏈接自己的生活,這樣使他越發傲慢,他每日其實都在為這傲慢而苦惱,直至他發現了她,發現了他原來在苦惱。他從未主動回想,今天發生了什麼,今天是怎樣的,對比一下昨天和今天,對比一下現在和過去。從來沒有,直到他聽到她問:你的生活是怎麼樣的?他慢慢的被痛苦找上門來,他試圖用理性去對抗這種疑問:這只是網線另一頭一個不如意的女孩,在用情緒和我糾纏。怎麼會有因為四季太過分明而在生活中崩潰這樣的事情呢?他在覺得可笑的時候,隱隱在想像那種感覺,他開始分辨蛋糕的甜度,早上醒來游絲一樣的感覺。他開始有意無意思考活著這件事,他問跟自己定期發生關係的女孩,什麼時候感覺充實。她說你操我的時候,他再也沒法問下去。往後再做愛,他也沒有辦法再說一句話,女孩的叫聲堵在了耳朵眼裏像一團棉花。不過他依然赴約,直到幾天前的最近一次。
他以往所有的戀愛痕跡都變淡了,導致他也記不起來在那個時候做愛是什麼樣的身體感受。
他現在依然握著手機在等待,他看著房間拐角今天採購的用品,覺得自己的生活豬狗不如。

長夜難眠。
無數次的深夜,她打來電話(通常都是單向打來的語音,他從未打過去,因為他知道會打來,甚至一度讓他有掌控感),話語很少,但是他喜歡這些空白。有的時候他開著電話,聽著另一邊的安靜,盯著月亮。月亮靜而秘。他覺得充盈,一片漆黑裏面他沒有心情,電話那邊也是同樣。他猜她或許也是在看月亮。 ——她就是在看月亮,他從不問,恣意想像。
他拒絕承認被改變了生活。瞬間他發覺出發沒有意義。她不是必要,只是他的一種發現和發明。消失和出現應該如同自來水的來去,你上班路上偶遇一隻螞蟻,你怎麼還會在幾個小時下班後原定等待它再次回到原地?
靜靜躺了幾秒,他蹦起身來,撕開今天採購的那些塑膠袋,拿出所有能吃的,他開始吃,開始塞,不停地吃,他想要把食物全部塞進去,他感受到食慾在肚子裏擴張身體,一種煎熬開始燒灼他的自尊。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渺小地想要吃掉所有讓他感受到的掙扎和否定,吞下去。他咀嚼的時候強烈的感覺到了自己的依賴,一種無法擺脫的追逐感,他分辨不出食物的任何味道,他不知道現在口裏吃的是哪種麵包,他想著別的,他想,我要把手機砸碎。
我想要殺人。這似乎是個聲音,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想起來的。我跟A同居的時候,一天夜裏,他睡得很熟,我抽完不眠的煙,腦海裏有個聲音說:摁下去,摁下去。我看看自己的手,夜裏露的一點不知哪裏來的薄白光芒,照的我的身體那麼聖潔和漂亮。但是聲音在強烈的抖動,摁下去摁下去。於是我把煙頭摁在了A赤裸的肋骨上。
A的拳頭和巴掌是我這輩子最疼的體驗。除此之外,我第一次感覺自己是一個動物,肉感那麼的噁心,我的臉被扇得抖動的時候,我想吐。我沒有怎麼抵抗,自由的攤開在地板上,神志游離得非常遠,我的心臟第一次那麼的放鬆和平靜,跳動的非常踏實。 A沒有再理我,我猜他的靈魂離他而去了。我看見床底有一隻小蟲,速度很快在陰暗的地方快速地移動。它不知道有人在觀察它,它不知道我一出手就會碾死它。後來我感覺非常的冷,但是我沒有權利拿一條毯子蓋在自己的身上。我害怕,我只要一動就會觸怒床上的A。我知道如果不開口,這一夜過去,什麼都解釋不了。
但是後來我睡著了。
第二天的太陽掛得特別高的時候我才醒過來。 A坐在床邊發呆,我光著的身體每一處都在疼痛,浴室的鏡子裏,我斑駁得很怪異,看見自己的身體有這麼多顏色甚至讓我想拿相機拍下來。這比做愛更讓我感覺掌控了一個人,我看了好一會,同時也知道它們很快就會復原。
然後我就走了,A依然坐在床上。本來他應該去上班的,我知道他今天是沒有辦法走出門了。錯過了昨晚的沉默,殺人不外乎這麼容易。
A再也沒有聯繫過我。
我把這個故事變形,告訴了那個男孩。我告訴他我燒掉了A的陰毛,A拉我去做精神鑑定,把我一個人丟在醫院。
他總是對我的各種故事感興趣,那些故事全是謊言,他被謊言深深迷住,並且愛上我。他並不知道,我蒼白得像一塊玻璃,污垢使之美輪美奐。而我面對他的時候,那些謊言和闡釋,令我覺得自己純潔無比。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從這裏開始的交往,讓他不自覺把每次和她的交談歸為美夢一樣的經歷。
他去蒐集答案,他問他的女伴,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遭到了反問,你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他突然覺得這個問題好有魅力,是一個怎麼回答都不夠真實的答案。
然而,他越去追問越不自信,越是發現難以啟齒,別人的眼光在浸潤了這個問題之後顯得輕蔑、抗拒。他在問出口的時候心中也虛弱地沒有對應的答案。當他終於要回答她的問題的時候,他充滿了沮喪和敬意。他只能回答,不知道。不僅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別人。他不禁失望,他沒有對任何的人把握,他以為他也有網絡,社會網絡。他曾經因為能夠輕鬆駕馭而瞧不起這種人際網絡,他自詡在蜘蛛的背上,現在他知道他在回答不知道的時候是羞恥的。無知在撕咬他,可是他沒有更好的答案,他已經隱約的被看穿,奇妙的是,這是他在選擇她,與真實擦身的權利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其實可以偽造出一個答案,好似起伏丘陵上的厚雪一層,他本來的掌控是要把這片平坦掛成臥室的風景圖,從未想要進去看一看,他本來與痛苦無緣。他用不知道敲開一切。
她說,空瓶子。我眼裏所有的人都是空瓶子。
他想,是因為人無法被定義,他覺得他理解了「人是萬物的尺度」。
而她想說的是因為她曾經被抽取。抽取出來才能站立著觀看。但是他不知道,在他眼裏她就是個每天不一樣的空瓶,他已經樂於灌滿一個完整的對象,灌裝接近於他最想要平穩的思索。這是一種他打開眼睛才發現需要平衡的翹板,每個發現這個翹板的人,下一秒會驚覺自己距離深淵那麼近。
現在他想起了這個空瓶。懊惱昨晚為什麼吃得那麼多,那麼的失控,他想,我毫無頭緒,我往後退步了。人對於未知都會害怕,可是這是場冒險。現代社會裏真正的探險,它將用愛情檢驗我的勇氣,我的智慧,我的不凡。又一次,他被一個點聚集到一起,再次產生了巨大的推力。不凡太誘惑,他曾經自己淘過的一層層沙,用自己原始的邏輯,明白了網線一頭他們之間簡單的問答中揭開答案面紗的鐵鈎,如今,他握著鐵板手馬上就要開始撬動自己軌道。
有幾個人能在生活的蒸汽裏看清鼓動的真實樣貌?有幾個人能在一團混沌的窗面上偶然留下手印,從而發現清晰被隱藏著。
這是勇氣。接著他去了火車站。
買的車票上的班次要途徑鳳凰山和山海關。他滿意這兩個地方,或者說地名,他小時候最愛看《魯賓遜漂流記》,他想,他去一趟哪怕找不到她,翻過這兩個雄偉的名字,再次回到人流中,他也多出了一次歷史,他也會帶著人類逐漸被稀釋的氣味——再也沒有什麼會淹沒他,就像他終於從海面露出第一次鼻息那樣,不會再被湮沒。他將擁有一種辨認和被識別的驕傲,但不是優越,人類的生活被優越弄得混沌不堪,他只會到達那故意被削弱的山峰,這是他與她與同類們的平靜景色。他又回到了往日的夜景中,被吃掉的物品再次被補充。口袋裏是明天的車票,與昨日相同又不同,昨天他帶著一點憐憫和機靈看鏡像的世界,今天他重新思索,現實就更新了。風裏帶著人的氣味穿過他,他看著每一張臉人來人往的流痕,他現在不敢說充滿希望,但是他開始相信,等他回來,他會從這些中剝離出真實而不是帶著優越的同情,他會像一個真正的人,有過體味甘於沐浴平靜。
這張車票,鳳凰山,山海關,還有她。他握著手機,翻來覆去,這份即將到手的新生,他簡直要沸騰。他曾經想要她為他寫個故事,是的。她會寫,她寫的小小故事雖說不算特別完美,但是就像一台顯微鏡,人類在此之前沒有見證過活動之中還有活動。她的小故事,讓他參與到人與人不同的縫隙中去,他們變成了一個戰線的盟友,帶著轉動去看對面天才層面的轉動,承認還有接受差距的神化,從而為了擺脫無知牽起手來。他想知道,她寫了嗎?
「我就要來了」他打下這五個字。
但他沒有發送,他重新打字「我明天要爬山,爬出來見到你,就會變成你說的發生」,發送過去,他真高興啊接著又打了一條——此時他另一個神思一閃而過的想著不管回不回覆都沒關係,他手上在打「這是我第一次,我好像知道你去商店偷水晶的心了」也發送了出去。信息發送出去之後他按下鎖屏,黑黑的手機被他拎在手上,他的嘴上有著笑,然後按亮屏幕,上面是一輪小小如豆的月亮。他按滅,接著按亮。十幾秒後,手機自動暗了下去。他覺得室內的燈光也忽然暗了一點,他拿起手機,看著對話框,他期待上面顯示對方正在輸入。她究竟有沒有看到?她消失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這麼突然?戰友,盟友,我們真的是一起跨越的人嗎?
他沒忍住,「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發送之後他立刻撤回了,不對不對,他想了想,冷卻的心還是打下了一句話:你人呢?
他期待了一夜,在床上失落得渡過天亮,他似乎看見了剛出的陽光和昨晚的月亮在一片待變化的天空中同時出現。他想,如果樓下的孩子看見這個場景大叫起來,世人都不會責怪他打破了清晨睡眠的晃蕩。他扣下手機,翻過身體不想再面對散著微光的窗台。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接收到的第一個信息是:唐山鐵路鳳凰山段山體滑坡,導致G1234列車緊急停靠。前方在全力疏通,索性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我錯過了一切。」
那張車票,這部手機。他把它們疊在一起,捏在雙手裏。
她說,能發生什麼對我很重要。
他的胳膊搭在窗台壓了好久,然後他猛地把手機砸了出去,遠得一聲脆響,他才發現他的雙臂麻了很長時間了。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凌晨三點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梁晚簡介:九十後,現居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