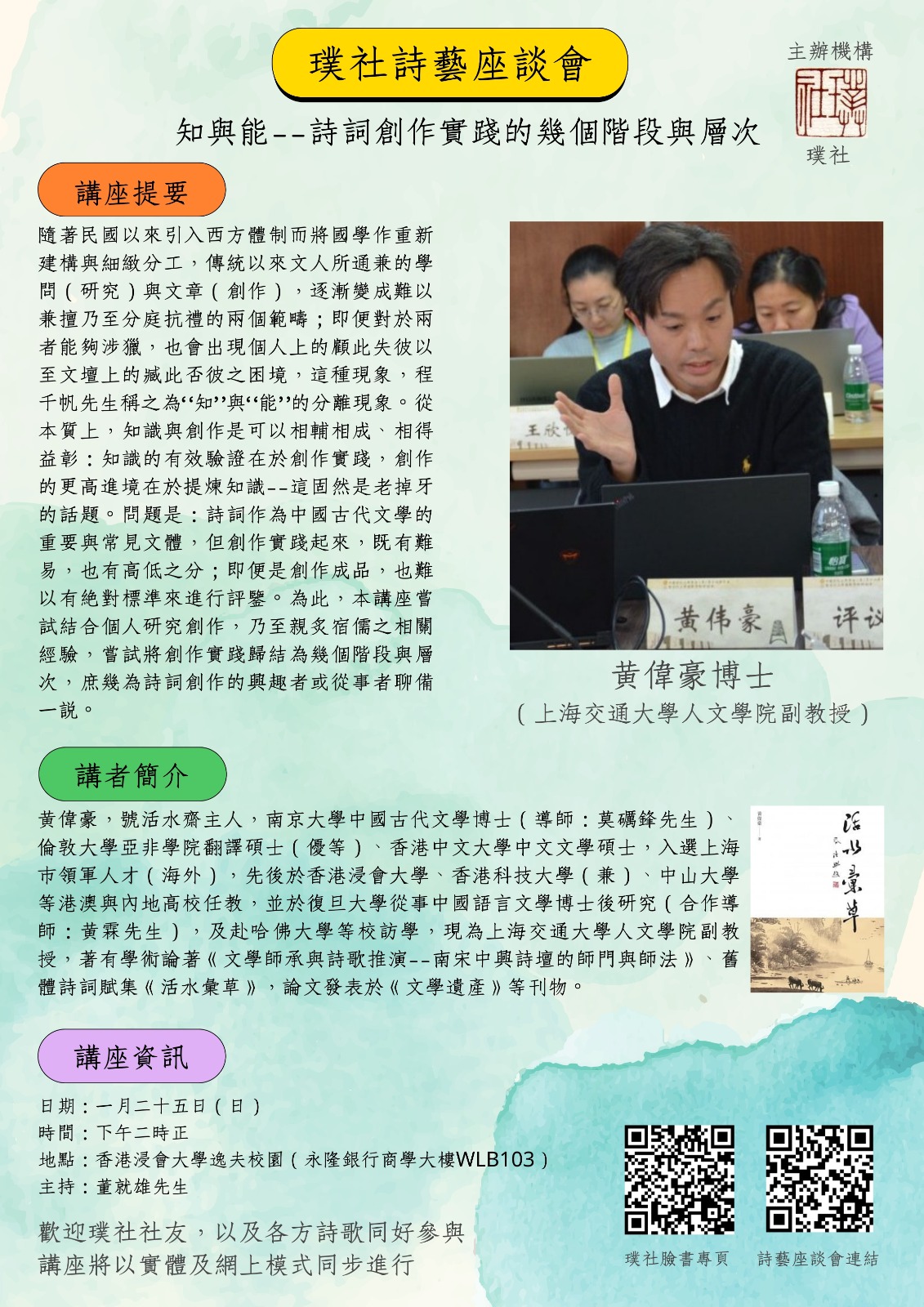潘耀明
時序初冬,夜色蒼茫。幾乎與大埔宏福苑無情大火同時,李天命掩臉而去,告訴這個噩耗的潔明,幾度哽咽,黯然傷痛。
香港的夜空,又遠去一顆獨特閃爍的智慧之星。李天命先生的離去,留下了一片澄澈的哲思天地,讓後學在其中仰望、沉思、前行。他是一位罕見的智者——擅以手術刀般的邏輯剖析迷思,卻懷抱如詩人般的溫柔觀照生命;在講壇上論辯無敵,在書房中卻能對一缸游魚靜觀半日。紀念他,便是重訪一種將思辨之銳與生命之悅融為一體的生存藝術。

李天命先生留給世人最鋒利的遺產,是他創建的「思方學」。對他而言,清晰的思考不僅是學術工具,更是一種倫理責任——對自己與他人的心智誠實。在其廣為流傳的著作《李天命的思考藝術》(目下已經印刷六十五版次)中,他將複雜的思維過程化為可操作的「招式」,引導讀者穿透言語的迷霧,直抵問題的核心。這種能力在辯論場上展露無遺,往往能一擊即中對方邏輯的脆弱環節,故有「小李飛刀」之譽。然而,他的「鋒利」從來非為炫耀或征服,而是為了「清場」,為建設性的對話與真實的理解掃清障礙。他畢生致力於將哲學從繁瑣的學術囈語中解放出來,使其回歸「思維的藝術」的本質。
若「思方學」展現其理性之剛健,其「天人學」則蘊含了生命感悟之柔韌與通透。李先生對生死課題的思考,尤為深刻地體現了這種剛柔並濟的智慧。他借香港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對聯:「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闡發三層境界:從見萬事虛空的頹然,到帶有幽默的坦然,最高一層,則是體悟到與所愛之人、歷代賢哲「殊途同歸」後的平和與從容接納。這種接納,並非消極的認命,而是建基於一種「神秘樂觀」的宇宙信託。他深信「分散了的靈魂,必在愛中重合」。在預想的生命終站,他願將一生的透悟,凝結為一念:「把所愛的人們緊抱入自己的心裏,把自己的心魂交回到宇宙的懷中。」這是一種將個人情感與宇宙秩序合一的終極安頓,是理性思考之上綻放出的詩性智慧花朵。
李天命先生的哲學,從未與生活隔閡。他最愛將孔子與蘇格拉底的對話,稱為「高級的閒話家常」。在他看來,哲學的至高境界,正是融入這種看似隨意的思想交談之中。他的課堂與客廳,便是此種哲學的實踐場域:天南地北的話題,最終總能迂迴地引向對根本問題的思索。他建議學生多觀看原始自然的紀錄片以「破生死關」,自己卻也能興味盎然地欣賞一缸熱帶魚的《魚樂無窮》。這種從磅礴到微末的觀察,皆為「與天地合一」的修行。他的哲學是「可親」的,這種可親,源於他對人的真切關懷——那句對學生說的「拿些什麼沒所謂,我只怕你撞到而已」,其體貼之情,溢於言表。
先生的為人行止,與其思想互為表裏。他對文字抱有近乎虔誠的嚴謹,校對書稿時,甚至以尺丈量字距、標點,務求精確完美。這份「怪癖」,正是其思維縝密在物質形態上的極致體現。然而,面對外界聲名,他卻異常低調,曾婉拒利用名人閱讀其書的照片進行宣傳。他彷彿一位思想的匠人,只專注於將手中之玉打磨通透,而不計較它被置於何種燈盞之下。這種慎獨與淡泊,在哄哄喧囂的時代裏,本身即是一種無言的哲學宣言。
李天命先生的一生,示範了一種完整的哲人生活:以清晰的頭腦思考,以溫暖的心靈觀照,以從容的姿態面對終極。他離開了,但他所點燃的思辨之火與生命之悅,已匯入無數讀者與學子的精神脈絡。紀念他的最好方式,或許便是如他所願:好好運用思方學,建立起自己妥善的人生觀,然後在愛中,與一切美好的靈魂重逢。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轉載自《明報.明月灣區》202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