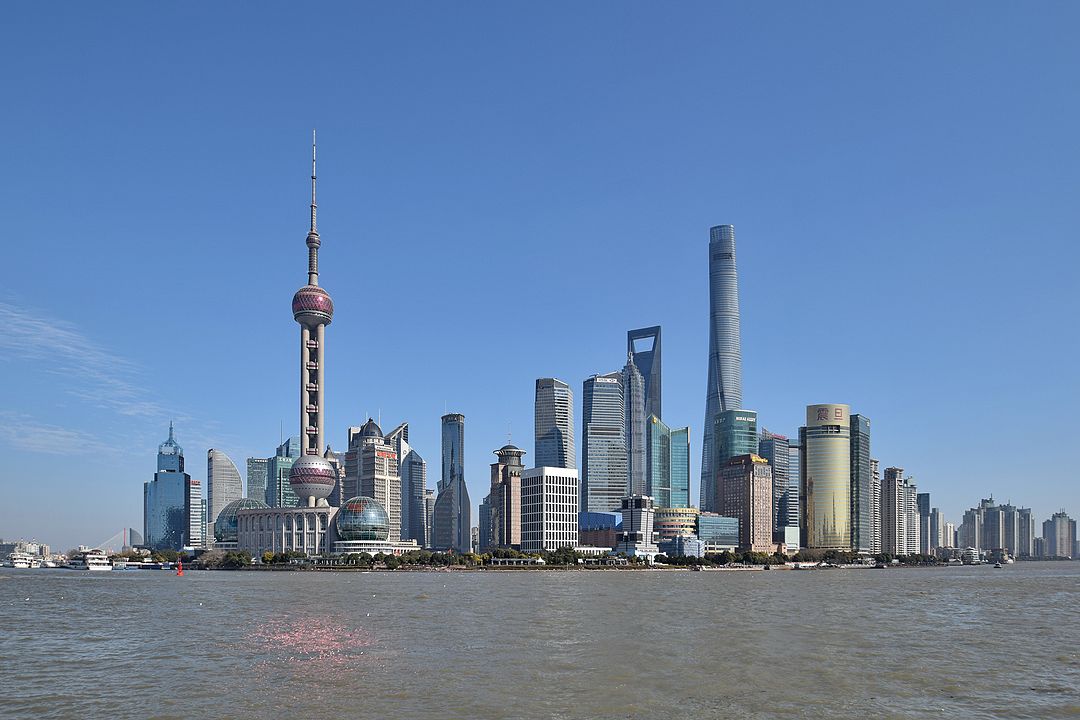林祁
在香港這座高度折疊的都市空間裏,楊夢茹以詩畫藝術家的敏感,以泉港女性溫柔的執拗,構建獨特的風景詩學。從泉港到香港,走過人生的大半個世紀,向你展示兩港之間一道如約的動態風景,從記憶的原點出發,經歷語言的縫隙,心向超現實的彼岸,即原風景—詩風景—夢風景的三重進階。我們不再把風景看成一個供觀看的物體,或者供閱讀的文本,而是一個過程,一種意象,一種心靈和情感的建構。
一、原風景:兩港之間的船與風
楊夢茹,日前在泉州舉辦詩畫作品展,題曰「夢如印象多元藝術展」,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八個置放於高低錯落木樁上的腳印,笨笨地嵌實在兩港之間——泉港與香港,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在此稍停片刻,有如「千山鳥飛絕」,詩的盡頭是靜寂,是木樁腳印歪歪扭扭地記憶著時間。時間可以穿越嗎?
這始終是大難題,但泉港自古就在想像,中國下西洋在穿越。亦有今人蔡國強,一個泉州老頑童,一個「天空巨人」,以火藥藝術的二十九個大腳印,有聲有色地跨越天際。她是他的「老老鄉」,她也試圖「穿越」「季節的錯誤」(楊夢茹的處女詩集),以獨特的筆觸勾勒出細膩的情感與深邃的哲思。也許,從泉港到香港,是一種跨越,她在詩中透露著某種輕鬆。
纜繩既已鬆懈
船
便是自由身了
連詩中常用的比喻,也還是「船」:故鄉泉港的船、鄭和下西洋的船、實實在在漂洋過海的船。看來,詩人的「原風景」是船。哲人說,「原風景」影響人的一生。然而,詩人給我的回答卻是:「我是印尼歸僑,一九六〇年回國,獲分配住在泉州雙陽華僑農場,舉頭便見雙奶山,很想進泉州城看看,到底城裏有沒有山,城裏的山長什麼樣子呢?常常對著墻壁、地磚、以及陽光移動的紋理發呆,臆造許多故事情節。自幼便想去外面看風景,總是幻想自己拎著皮箱在火車站,無止境的旅程,其實我只是在月台上,車門邊等車而已!」原來她的「原風景」裏沒有船只有山,「船」只是她想像的「山」,一種幻想的外面的風景。
而帆
仍在靜默中等候
風的造訪

〈等候 風的造訪〉水墨 27x20cm
不僅詩中有船的意象,連畫裏也有船的形體,題詞卻巧妙如風:「等待風的造訪。」船與風的關係,或劍拔弩張,實相依相生,詩則於虛實之間贏得張力。
被霧漂洗過的碼頭
此刻無須承載
太多的鄉愁
陽光明媚
絲綢鋪就一條水路
唐風宋雨 繁華盛世
古典詩詞中的碼頭常負載離愁(如柳永「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而此詩卻以「漂洗」消解了悲情,讓碼頭成為空鏡頭,指向一種懸置的平靜。「霧」作為時間與記憶的過濾器,以「朦朧美」稀釋了碼頭作為離別符號的沉重性。但「唐風宋雨 繁華盛世」突然嵌入歷史語境,似在提醒——所謂盛世,不過是絲網般交織的幻影,而「水路」始終虛浮在時間之上。
有人站在岸上
偶然看見了
風景中的你
穿越鄉愁,她進入風景,成為風景中的詩人。楊夢茹封筆十八年後,二〇一七年,她以新筆名「印象」重新出發,開啟了藝術人生的新篇章。這種在創作道路上不斷突破自我、勇於探索的精神,留給人藝術生命力的鮮活印象。尤為值得一提的是,當評論家紛紛給予表彰時,她卻華麗轉身。
而你已不在
風景之中
這一結尾構成哲學意義上的凝視悖論。而當「你」從風景中抽離,卻因他人的「看見」獲得另一種存在形式——如同量子世界中被觀測的粒子,存在因注視而坍縮為具體形態。這讓人想起卞之琳的〈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而似乎楊夢茹更決絕,索性消逝於風景,成為他者記憶的殘像。這種「缺席的在場」,是否揭示出現代人身份的流動性——我們終將成為他人敘事中的符號。此詩〈等待風的造訪〉,配楊夢茹的畫,就這樣以極簡的意象與留白,構建了一幅水墨畫般的詩意空間,通過「船」、「帆」、「霧」、「絲綢」等物象,探討自由與束縛、在場與缺席、歷史與當下的辯證關系。詩中暗含東方美學的空寂感與存在主義的哲思,柔軟的語言時而如刀,切割出生命狀態的複雜褶皺。作為「水墨紙本」的配詩,文本與畫作形成互動。水墨精神與空間詩學交錯,時而筆觸枯潤變化:「船/便是自由身了。」「船」單獨成行,彷彿畫中孤舟的題款;而「唐風宋雨 繁華盛世」八字密集排列,恰似畫卷角落的篆刻印章。畫的物理尺度,亦被語言復刻:霧的氤氳、絲網的細密、水路的綿延,皆在有限空間內,營造無限的意境,踐行了傳統水墨「咫尺萬里」的美學原則。 這首詩的終極等待或許永無答案——風可能來,也可能讓帆靜止。但,在風中懸置的永恒狀態,構成了生命的詩意本質——碼頭上,歷史的霧與當下的光共存;風景中,消失的「你」與凝視的「他」同在。楊夢茹以水墨淡淡的筆觸,書寫了一則關於存在的寓言——自由從來不是終點,而是風中搖曳的未完成時態。

〈斷章〉水墨 60x60cm
二、詩風景:帶著自己的「古代」
她的詩畫作品〈呼喚夏荷〉,一開篇就濕(詩)了:
整個下午就這麼 濕了
你坐擁的水湄
也這般湮著濛濛雨霧麼
風拂過荷塘
留下淺淺笑靨
夏荷在雨中搖曳,其清麗脫俗與古典意象一脈相承(如王維「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雨霧籠罩下的荷塘,既是自然景象,也是詩人內心情感的投射。古典詩詞中,「荷」常象徵高潔與孤寂(如李商隱「留得枯荷聽雨聲」),楊夢茹也將「荷」置於雨中,賦予其更強烈的現代性:荷塘在雨霧中若隱若現,彷彿一種未完成的期待,一種模糊的呼喚。
「風拂過荷塘/留下淺淺笑靨」一句,將風擬人化,賦予荷塘以生命的靈動。這裏的「笑靨」既是荷塘的漣漪,也是詩人內心情感的波動,輕盈而短暫,卻令人回味無窮。詩中既有古典詩詞的婉約與含蓄,又融入了現代詩的語言實驗與情感張力,展現了詩人對孤獨、等待與自我燃燒的深刻思考。

〈呼喚夏荷〉水墨 50x50cm
墨色 自紙背一寸寸逼來
你點燃自己
光照幽冥
火苗為清癯的臉
勻上淡淡胭脂
森森沉寂中
唯我獨立
等你擎一把油紙傘
款款
從雨的字裏行間
步出
「逼來」逼得好,逼出文字與現實的交織——墨色既是外在的黑暗,也是內心的壓抑,而「你點燃自己/光照幽冥」則是對這種黑暗的抵抗。火苗的意象取代了古典詩詞中常見的「月光」,成為詩中的光源,象徵著詩人內心的燃燒與自我救贖。荷在詩中以自身潔凈抵抗黑暗,與古典詩中的孤高自照(如蘇軾「明月夜,短松岡」),形成精神共鳴。其中「胭脂」不僅是色彩的修飾,更是情感的隱喻,暗示詩人在黑暗中依然保持對美的追求。脆弱而執著。「帶著自己的『古代』」(黃子平語),從古典到現代,「森森沉寂中/唯我獨立」,僅一句,便將詩的情感推向高潮。詩人在沉寂中獨自等待,這種等待既是對某種未知的期盼,也是對自我存在的確認。古典詩詞中,「等待」常與「月」相伴(如李白「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而楊夢茹將等待的場景置於雨中,賦予其更強烈的現代性。「等你擎一把油紙傘/款款/從雨的字裏行間/步出」,是全詩的結尾,把我們帶到現代詩的「雨巷」。這種模仿看似敗筆,卻成功地把我們從古典帶往現代,「款款/從雨的字裏行間/步出」,通過分行製造出節奏感,步向現代詩的美學探索。
〈呼喚夏荷〉是一首兼具古典韻味與現代詩意的作品。詩人通過對「雨」、「荷」、「火」等意象的巧妙運用,構建了一個朦朧的意境,既表達了對孤獨與等待的深刻思考,也展現了現代詩的美學探索。詩中的情感細膩而克制,語言簡潔而富於張力。詩中融入了對文學、歷史與哲學的思考,使詩歌不僅是對這一具體場所的描寫,更是對人類文明與精神世界的探索。這種融合使詩歌具有了更廣闊的視野,以及更深厚的文化底蘊。
楊夢茹自一九八六年開啟寫作生涯,其間封筆十八年。創作的詩集《季節的錯誤》、《穿越》,以獨特的筆觸勾勒出細膩的情感與深邃的哲思,文字間流淌著對生活、對世界的深刻洞察。她的詩畫合集《夢如印象詩畫作品選》,用文字與色彩共同構建起一個奇幻而美妙的詩風景。作品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書信手稿獲臺灣文學館典藏,並廣泛收入各類文學、詩歌史以及大中小學的教材,這不僅是對她作品文學價值的高度認可,更是其作品在文化傳播領域影響力的有力見證。

〈那一朵午荷〉水墨 120x60cm
三、夢風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
日前讀到關於風景美學的論述:在風景作為主觀形式的概念演變過程中,從伯明翰《風景與意識形態:英國鄉村傳統,一七四〇-一八六〇》,到希拉里《風景:想象世界的方式》,再到達比《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都提出了相似觀點,伯明翰認為風景是一種話語的意識形態,希拉里認為風景是一種想象世界的方式,達比則認為風景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日本學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提出「風景乃是一種認識性的裝置」。
在歷史上,風景概念多種多樣,正如傑克遜所說:「這個詞本身很簡單,我們似乎都能理解,但對於每一個人來說,其涵義又不盡相同。」楊夢茹從其名到其詩其人都是愛做夢的。如,明明畫的是一個馬頭,卻配了一首詩,題「如約而至」,和誰約會呢?

〈如约而至〉粉彩 37.5x55cm
用一艘漁船經過的時間
回溯
那口荷塘的
前塵往事
騰出最空的地方
讓你的馬蹄急馳而過
留下靜止的風
以及風中凋落的
長短句
任由久別重逢的驚喜
劫持
荷苞尖尖上
那顆出神凝望的 露珠
一夜之間
河的兩鬢梳起
雪白的蘆花
眉宇中
從此有了揮之不盡的
煙嵐
佇立良久
天空以閃電的速度
刪除了
剛打好腹稿的一首
詠物詩
就這樣,一夜之間帶著夢,由天而降如約而至,以粉彩畫的柔暈筆觸與斷裂性意象,構建了一場時空交錯的記憶儀式。詩中「漁船」、「馬蹄」、「蘆花」、「閃電」等物象,既是視覺投射,也是時間褶皺中的隱喻符號,探討存在與消逝、語言與沉默的永恒博弈。
開篇將其慣用的「漁船」意象化為時間之梭,在荷塘的鏡面上劃開記憶的裂痕。「漁船」作為移動的視角,暗示觀畫者凝視畫幅時的目光遊移——粉彩的氤氳質感中,荷塘的「前塵」被暈染成模糊的色塊,而「回溯」本身成為一場徒勞。「騰出最空的地方」一句,以空間騰挪喻示記憶的讓位——當「馬蹄急馳而過」,動態的蹄印反而凝固為「靜止的風」,而風中凋落的「長短句」,既是枯枝碎葉,亦是未被寫下的詩行。粉彩畫中虛實相生的技法在此轉化為詩的時間性——流逝與駐留的悖論。詩人試圖「劫持」——露珠本是古典詩詞中易逝之美的象徵,(如白居易「露似真珠月似弓」),在此卻被「重逢的驚喜」強行佔據,暗示記憶對當下的入侵。荷苞尖尖上的凝望,恰似畫中的一點高光,在粉彩的灰調中刺破柔膩,成為情感的高潮與傷口。「劫持」亦指向創作本身:詩人被靈感突襲,露珠成為詩句的冷凝,而這一過程注定伴隨對純粹自然的「破壞」。粉彩畫的疊色技法在此顯影——每一筆溫柔覆蓋,皆是前一層色彩的湮滅。「一夜之間」,蘆花白髮,美學風景使之「有了揮之不盡的煙嵐」,宣告青春的潰退與滄桑的入駐。但衰老不再是哀悼的對象,而成為風景被觀看,被「照花前後鏡」。閃電之刪除並非否定,而是將語言未及言說的部分交還於沉默——正如粉彩畫中,最強烈的表達往往依賴色彩的隱退與留白。粉彩的脆弱性(易被塗抹修改)與此形成共振:每一幅畫都是未被閃電擊中的僥幸之作。楊夢茹以「如約而至」為這場記憶儀式命名,卻揭示了約會的虛妄——我們等到的永遠是時間的替身,是粉彩褪色後的殘章,是被閃電赦免的、幸存之物的沉默展覽。如夢似約,一種心靈與情感的建構。
在這人類的黃昏時刻,詩與風景的對話獲得了救贖的意味。在語言的廢墟與自然的存在之間,詩不再滿足於田園牧歌的抒情,也不停滯於創傷檔案的慟哭,依然執著地尋找著那道通向本真的存在,黃子平教授解讀為「帶著自己的『古代』」,或也可理解為當代人各自「發明」了自己的「傳統」。由於時代的斷裂,使我們可以帶著自己的「古代」進入當代。有人帶著李白的盛唐來進入當代,也有人帶著蘇軾的北宋來進入當代。「過去、當下、未來」是一種時間的構建,而你怎樣進入你的當代?且讓我引述日本明治維新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的一句話:「一生而歷二世。」正因為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生活過,很自然產生觀察角度的差異。這是一種「照花前後鏡」的效果,都讓你時刻保持疏離感以及超越的衝動。正如段義孚所謂「風景就是這樣一種意象,一種心靈和情感的建構。」之前有李歐梵等著述與之互為印證,後有楊夢茹等後來者為之豐富。「風景」成為動詞landscaping,意義即時生成,形成詩學與風景學的共構——一場永恒的凝視與解蔽。
夢風景是夢非夢。當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採摘的不僅是自然物象,更是在時空褶皺中凝結的永恒凝視;當王維寫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不僅描繪了視覺經驗,更完成了對存在本身的拓撲學測繪——水窮處是現象界的邊界,雲起時是本體界的綻出;而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並非簡單的擬人修辭,更留待後人「風景」為媒,在「歷史之後追跡」。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林祁簡介: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師承謝冕)、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日本華文女作協副會長。來往於中日之間,現爲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教授。出版詩集《唇邊》、《情結》、《裸詩》、《莫名「祁」妙》及論著譯著非虛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