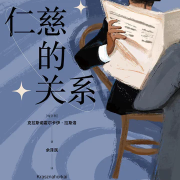惟得
未知其他留學生有何感受?初進大學,只覺人海茫茫,課堂動輒容納百多名學生,上課一如觀劇,教授高高立在講壇上講學,考卷多由助教判改,遇上像我這樣害羞的學生,一個學期結束,與教授真如老死不相往來。你的教學方法卻別樹一幟,倘若很多教授只向學生派發單程車票,你卻要求來回,你喜歡借用課室裏的電視機播放錄影帶的片段,然後追問學生的反應,所以上課前你特別忙碌,在講臺上走來走去,肯定所有插掣各就各位。有一次一名學生想向你發問,又不敢騷擾,默默尾隨在你背後,你昏頭昏腦在臺上巡視,不提防被人跟蹤,猛然轉身,看見一個人影,嚇得怪叫一聲。眾多教授中,我挑選了你作為我的顧問,就因為這聲怪叫。原來以為教授都是腳踏層雲俯視人間,不料你倒會像凡夫俗子擔驚受怕,人頭湧湧裏,我攀附到一片浮木。
你的校務處卻令我大開眼界,堆疊的書本,錄影帶與文件把你半埋在寫字桌後,你需要把紙張從椅面移到地板,才勉強騰出一個座位給我,一個同學參觀過你的辦公室,決定不選修你的課程,我倒覺得她太苛求,細心想想,教授多是一腳踏地一腳踩夢,有時難免顧此失彼,何況你的俏皮倒流露了一份對人事的圓通,譬如你會拔著唇邊的鬍子猜測我的國籍,你並沒有猜中,卻敲碎了師生初見的靦腆。
友誼也在你我之間默默滋長。另一個學期,我選修你主持的研討班,全室只得十名學生,課程快將完結,你都邀請到家裏晚膳,我們登堂入室四處參觀,來到廚房門前,卻被你嚴令止步,列為客人禁區,門後是怎樣的風景,至今是一個謎。同學間不禁議論紛紛,懷疑你把碗碟刀叉都丟棄在洗碗盤裏,任由蟑螂攀爬,然而大家吃過你親自下廚的晚餐,都精神爽利,謠言不攻自破,我覺得廚房更像你的八寶箱,你舞動著圓胖的身軀,在廚房與飯廳間團團轉,一忽兒捧出嬌艷欲滴的牛肉,一忽兒端來晶瑩透剔的意大利粉,彷彿魔術師躲在黑布後變戲法,看得我們目眩心惑。其實你的教學方法也像弄法術,有時點唱歌劇的詠嘆調,有時播放世界經典的片段,或者指派我們到美術館看一組畫,回家讀一本小說的幾個章節,看似毫無章法,多思多想,卻體會到你小心鋪設的紋路。
還是你珍藏的錄影帶引起我的好奇,那時節還未流行DVD,見微知著﹐依然可以窺探你的內心世界,你也不避嫌疑,沒有用抽屜安置,堆堆疊疊放在書桌上,彷彿解開衣鈕,任由大肚皮像西瓜乘涼。初來作客﹐你指派我坐在書桌前,守著搖搖欲墜的盒帶,正襟危坐。多來幾次,開始放肆,忍不住側頭細讀寫在盒帶邊緣的片名,赫然發現多是迪士尼出品裹著糖衣的卡通,或是《黑色星期五》式血肉模糊的恐怖片,平日你在課室裏義正詞嚴分析經典片的結構,閒來卻沉迷於官能刺激,我不禁質疑你的品味。「有何不可?」你說著還哼唱一段迪士尼的插曲﹕「吃素的人有時也會思念肉香,我們偶然到快餐店吃一客漢堡包,回頭品嚐大師烹調的珍饈百味,倍覺可口。」然而你到戲院觀賞已經足夠,為甚麼還要記錄下來,這些電影都沒有永恆價值。「甚麼叫做永恆價值﹖」你嗤之以鼻。「價值觀念總是隨著時代改變。十七世紀莎士比亞寫的戲劇,至今仍然有人研讀與搬演,豈不就是永恆﹖」我有點不服氣。你卻笑得更響。「現代人詮釋莎劇,與他的原意已經大有出入了,傻瓜。」你用唇槍舌劍向我進攻﹐我招架不住﹐敗下陣來,卻又茅塞頓開,奢言藝術的人多是道行未深的小卒,用冠冕堂皇的字眼掩飾思想的單薄,等到修成正果,刀槍不入,穿梭於雅俗之間,面不改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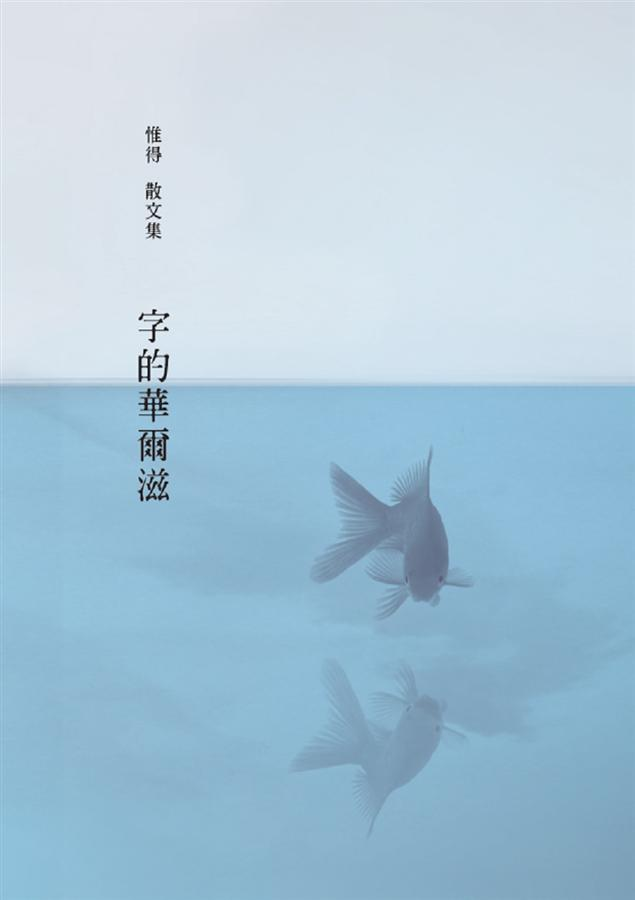
熟絡後,你還滿不在乎地告訴我,有一個深夜你抱著貓在客廳看錄影帶的恐怖片,看到驚駭處你尖叫,貓嚇得站起來,貓爪嵌到你的睡袍,我不知道好氣還是好笑。
多去你家作客,心想做一次東道,然而我不懂得烹飪,惟有打電話越洋向母親求助,母親提議我把叉燒蘿蔔切成條狀,加上芽菜和蔥,用紅橙黃綠配襯白色的米粉,相信可以滿足你視覺上的要求。你吃了一口,索取豉油,留學後,過著清苦的生涯,細節得過且過,起居飲食少有調味,抓抓頭皮,只能交白卷。下次你再造訪,攜來一瓶魚露一瓶生抽,特別強調說﹕「這是日常必需品。」經過你鼓勵,以後我也想到在生活加鹽加醋,增加情趣。
畢業後,我仍然尊稱你為教授,你打趣說﹕「為甚麼這樣見外﹖我倒有個名字。」你著意衝破師生的界限,卻衝不破浮華的虛榮心,你精通多國語言,有時閒談,禁不住在我面前賣弄,我不是語言專家,難辨真偽。有一次你流露學中文的興趣,我即管在你面前說了幾句,你卻被「平上去入」四聲弄得頭昏腦脹,索性放棄。《老子》規劃的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相信你也不及格。你的一個門生投身到佐治魯卡斯麾下工作,一次請你參觀光影魔幻工業公司,回來後你竟像初入夏令營的小學生,打電話來向我說了個多小時現場特效。後來格力哥利柏到校園訪問,你敬陪末座,更加口沫橫飛,然而世間有多少人兩袖清風呢?你身處儒林,未必就脫了塵俗氣,日久見人心,你性格上的瑕疵逐漸顯露,彷彿名瓷上裂出一道淺痕,有點礙眼,到底無傷大雅,索性視而不見。
是個無事的清晨,開工前我循例察看電郵﹐接到同學傳來的一封短信,訴說你在上一天與世長辭,我第一個反應是吃驚。十多天前你還來我家進膳,當時你有點咳嗽,卻堅持要喝酒,我還以為你只是患了氣管炎。相信你也不知道自己病情嚴重,同學說你上一天如常起床更衣,準備回校上課,猝然倒斃於衣櫃裏。接到噩耗,我只感到失魂落魄,站著也感到樓面飄浮大地震盪。講壇上下你都對答如流,展露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我下意識認定你永垂不朽,猛然驚覺你也是人肉之軀,需要經歷生老病死的循環,不禁黯然神傷。
一天經過圖書館,心血來潮,想看看你有甚麼著作,來到電腦目錄前,輸入你的名字,一個書名在熒幕上顯露,我追隨編號來到書架前,找到你評論一部德國默片的小冊子,薄薄的數十頁,拿在手中也感覺不到份量,有些教授年青時已經出版洋洋數十萬言,你除了教學之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費在看電影、聽歌劇、遊畫廊、翻書報……的活動裏,寧願與好友共享佳餚美酒,算不算枉費此生?然而著作等身未必等於名垂千古,你不是也說過,價值觀念隨著時代轉變,現代人寫的書,流傳到下一世紀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反為你把握時機,珍惜當前。你的戲已演完,書名只不過像快要消失在銀幕上端的幕後英雄榜,聲沉影寂之後,眼前是否只餘一片空白?從良師到益友,我的腦電波不自覺把你的言行一一錄影,伺機在記憶中重播。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惟得簡介:散文及小說作者,兼寫影評書評,文稿散見《明報》、《香港文學》、《香港作家雙月刊》、《信報》、香港電影資料館叢書、《字花/別字》、《城市文藝》、《大頭菜文藝月刊》、《虛詞.無形網志》。著有短篇小說集《請坐》(二〇一四年,素葉出版社)及《亦蜿蜒》(二〇一七年,初文出版社) 、 散文集《字的華爾滋》(二〇一六年,練習文化實驗室有限公司)及《或序或散成圖》 (二〇二一年,初文出版社) 、電影散文集《戲謔麥加芬》(二〇一七年,文化工房) 、遊記《路從書上起》(二〇二〇年,初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