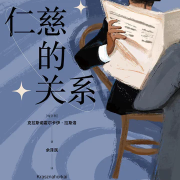陶賦雯
戰爭歷史的教訓揭示,歷史的敘述權往往掌握在勝利者手中,而失敗者則更多致力於內部重建,對歷史進行深刻或隱秘的反思。在當代,戰敗者如何書寫歷史成為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以影像媒介為主導的「新歷史表達」已經成為戰爭記憶剝奪的關鍵領域。在歷史的長期演變和不同的道德框架下,日本國內對戰敗的認知表現出三種相互矛盾的記憶模式:否認近代侵略歷史的「自虐史觀」、掩飾戰爭的「話語裝置」以及對戰爭進行有限反思的「無主體」態度。這些多元化的戰敗歷史在銀幕上的呈現,成功激發了日本國內關於「戰爭受害」、「殘酷」和「銘記歷史」的討論。同時,在電影的宣傳和傳播領域,競爭性歷史記憶的建構形成了差異化的傳播策略,滿足了影像時代對淺層認知的需求,將歷史記憶轉化為文化記憶,塑造了通過記憶障眼法實現的「現實性」政治訴求,以此來掩蓋歷史上的「戰敗之恥」。
一、對近代侵略史的否定與「自虐史觀」的駁斥
戰敗被視作一種深重的「國家創傷」,戰敗國往往需構建新的敘事架構,以詮釋國家所遭受的沉痛挫敗。在當代日本,一些持有右翼和保守主義觀點的頑固分子以及陣亡日軍遺屬組成的遺族會,持續不斷地在系統層面捍衛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歷史「正當性」與「合法性」論述,堅持天皇制度的必要性。他們憑藉對國民教育、新聞媒體、影視動漫及網路輿論等多管道傳播媒介的掌控,努力塑造並宣傳戰爭中日本天皇及各種「軍神」(如乃木希典、東鄉平八郎、山本五十六等)的「特攻英雄」形象,極力編造為天皇和軍部推卸責任的虛假歷史記載,並對近代以來日本的殖民侵略歷史予以否認,並對日本國內的「自虐史觀」進行批判,旨在構建有利於日本的國家形象。在文學和歷史領域,被稱作「日本帝國的辯護士」的林房雄提出,日本進軍中國是在歐美帝國主義壓迫下為了生存的無奈選擇,是一系列「無法停手的戰爭」,是「日本的悲壯命運」。他將歐美帝國主義者喻為「縱火狂徒」,而日本所策劃並參與的「東亞百年戰爭」,則被美化成「與縱火者抗爭的英勇壯舉」。同樣,在被中島誠譽為「對日本亞洲主義最正確理解者」的竹內好的觀點中,「為了將侵略者從東亞驅逐出去,我們無需進行任何道義上的反省」,因此侵略中國大陸、朝鮮、菲律賓等地,成為其將東亞解放並建立新秩序世界的道義上的正當理由。
在文史學界,二戰歷史的敘述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斷被重新詮釋。在當代影像媒介與數位互聯網的廣泛傳播下,對戰敗歷史的複雜情感,尤其是那份不甘,依然在某些角落悄然滋生,尤其在媒體宣傳的棱鏡下,顯得尤為刺眼。例如,二戰題材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一九九八)、《我們的戰爭》(二〇〇六)和《歸國》(二〇一〇)等作品中,通過「英雄」敘事手法,試圖影響公眾情感。以《自尊:命運的瞬間》為例,該片以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定為甲級戰犯的東條英機為主角,對其進行了過度的美化和頌揚。影片中的東條英機,被刻畫成了一位自尊而愛國,勇於獨立承擔戰爭責任的護國勇士,甚至在戰敗國的陰霾中,他被塑造為一位獨一無二的抗爭鬥士形象。在影片中,由津川雅彥飾演的東條英機及其辯護律師在法庭上反復提出「歷史虛構論」,聲稱戰爭是國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採取的行動,並辯稱日本是在保護中國,試圖混淆侵略戰爭與反侵略戰爭的本質區別,拒絕承認對亞洲各國的戰爭罪行。影片還公然宣稱戰後出生的日本人不應承擔「謝罪的宿命」。影片不遺餘力地渲染東條英機在審判臺上那「命運的瞬間」,展現出的日本式悲劇自尊,同時,它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的戰後審判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那是「戰勝者對戰敗者的不公復仇」,充滿了深深的憤懣與不平。這種通過影像手段有意掩蓋、偽飾、歪曲和篡改歷史的做法,成功地將觀眾的注意力從日本發動戰爭及其戰敗的責任上轉移,從而構建了一種歷史否認的「反記憶」。

二、轉移焦點:戰爭話語的「修辭機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並實行無條件投降,此日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定為「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紀念日」。然而,在日本國內,此日被稱作「終戰日」(終戰の日),而非「戰敗日」。在這一天,日本會舉行「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日本首相會發表關於戰爭歷史的「反思」言論。日本人通過其特有的「內部記憶」方式,對歷史日期的性質進行了結構性的重塑,將戰爭「失敗」的烙印悄然轉化為後世所銘記的「終結」這一中性表述,僅作為戰爭落幕的象徵。每逢「八一五」,日本的各大報刊、網路媒介、影像紀錄片等都會圍繞「終戰」主題進行報導。近年來,日本媒體更傾向於挖掘二戰中的個體化平民悲劇,通過私域視角對戰爭歷史進行「反思」,以此警醒世人,這已成為當代日本媒體紀念戰爭報導的主要方式。儘管日本媒體和政治人物中存在對侵略歷史的否認和淡化,但也有學者和媒體呼籲正視歷史,反省罪行。例如,《朝日新聞》曾用四個整版刊登名為《日中戰爭》的專題報導,對侵華戰爭進行全面冷靜地反思。此外,日本天皇和首相在公開講話中也提及對過去的深刻反省。僅在《每日新聞》和《東京新聞》等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中,才能看到對日本國內右傾化的批判之聲;而在《讀賣新聞》、《產經新聞》等保守媒體的主流報導中,它們多鼓吹日本擺脫戰後體制,鼓勵參拜靖國神社,並否認「慰安婦」的存在,這些失實報導成為其自我寬慰的手段。
在電影藝術領域,日本當代電影理論家四方田犬彥指出,蒙太奇技術賦予了電影將「未發生事件」轉化為「可能發生事件」的能力。他從影像構建的角度探討了修辭改寫的技巧,這種技巧能夠實現從「無」到「有」的轉變,進而更新和改編歷史敘述的權重。通過轉移焦點,蒙太奇技術能夠刻意掩蓋和偽裝戰爭的「話語裝置」。例如,日本在一九九四年製作的動畫電影《戰地啟示錄》以太平洋戰爭為背景,展現了日軍與美軍之間的激烈戰鬥。影片通過角色對話構建了歷史的假設場景,通過對比蒙太奇手法展現了「若無戰爭」、「若無戰鬥」、「若我能再活三十年」的不同命運。影片中日本士兵和美國士兵對未來的設想被呈現為一種追求類似美好命運的影像,但最終他們共同走向了戰場,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影片頻繁借助主人公對「若無戰爭」的遐想,試圖遮蔽日本發動戰爭的真正動因,這種修辭策略的本質無異於一種虛假的掩飾,就像脆弱的肥皂泡,輕輕一觸便即刻破滅,最終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反戰敗」邏輯怪圈。

三、對戰爭「無主體」現象的有限性反思
在探討「隱蔽性記憶」(Screen Memories)的過程中,佛洛德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何人類對某些事件能夠保持精確而詳盡的記憶,而對其他事件的記憶卻出現中斷,甚至徹底遺忘?這種選擇性記憶現象背後,實際上隱藏著更為關鍵和根本的事件。然而,正是由於人們有意識的掩飾和無意識的壓抑,那些本不那麼顯著的事件反而被凸顯出來,成為了記憶的一部分。遺忘,實質上是通過有意識地拒絕性編碼,對不願面對的場景進行排斥。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溝口雄三指出,日本人的感情記憶中幾乎未留下侵略中國的深刻印記。即便存在,也僅限於東史郎等退役軍官和士兵的記憶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在日本被稱為「活斷層」,象徵著「日本最漫長的一天」,意味著日本歷史從這一天起開始「歸零」,重新開始,形成新的歷史「層次」。這種斷層表述中的記憶清零,實質上是抹去了歷史苦難的起點。當前日本的二戰題材電影,常常運用心理防禦的手段,偏好輕描淡寫地處理敏感歷史,對戰爭加害者的責任以及國家所煽動的軍國主義熱潮選擇視而不見,僅僅局限於一種「無主體」的片面反思之中,進而導致了對真實戰爭罪行的淡忘乃至歪曲。
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作為日本新浪潮電影運動的領軍人物之一,導演大島渚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推行了所謂的「國策電影」,在戰爭局勢有利時,製作了大量影片,旨在向國民傳遞日本的「勝利姿態」。然而,隨著戰爭接近尾聲,由日本軍隊拍攝的戰爭場景數量顯著減少。戰後,電影界轉而以模糊的群體形象來描繪民眾的戰時生活狀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宣布無條件投降,即所謂的「天皇玉音」,當天日本國內的電影放映記錄顯示為零,電影院亦暫停營業。大島渚對此提出質疑:「我們的停戰是無影像的停戰。為何在錄製天皇玉音廣播時,竟無人拍攝哪怕一張照片?我們關於停戰的電影總是缺乏影像,只能勉強拼湊一些無關緊要的片段,並配上那個聲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裕仁通過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事件沒有伴隨天皇的影像記錄,從而支援了「敗者無影像」的觀點,即歷史往往只記錄勝利者的影像。這裏的「無」體現了對歷史記憶影像的清零敘事策略,而聲音則成為一種超越性、純粹性的神話象徵,「空缺」形象的黑洞,導致歷史認知成為無根之木,使得後代在接受戰敗這一資訊時「看不見」,無法繼承歷史真相,主動放棄了反思與批判的立場。
在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過程中,戰敗國日本採取了一種以「現實政治需求」為依託的歷史解讀方式,對歷史進行了某種程度的粉飾性接受。這種做法在銀幕上塑造了日本人的祖輩作為被迫為國家犧牲的受害者形象,從而消解或轉移了他們作為加害者的身份,並將亞洲其他國家的二戰受害者排除在懺悔和紀念活動之外。隨著偽史的不斷重複,它逐漸被接受為真實的歷史。從這一現象中,我們可以洞悉日本人在面對戰敗時所表現出的複雜心理狀態,以及通過藝術手段反映「戰敗者」在構建記憶過程中的多重矛盾。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陶賦雯簡介:南京大學藝術學博士,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博士後,東京大學表像文化專業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師範大學副研究員、碩導,中國新聞史學會外新史分會副理事長、中華日本學會理事。主要研究當代中日媒介文化、戰爭與災害記憶、影像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