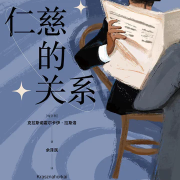邵迎建
引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跨過蘇州河,進入公共租界,太陽旗取代了米字旗與星條旗。
日軍報導部將書店街四馬路的店鋪全部接管,沒收書籍達數百萬冊,期刊被一掃而空。
同一天,日本電影代表川喜多長政的中華電影公司接受了大光明大戲院(以下簡稱大光明)等六家美籍一流電影院及八家美國電影發行公司的經營權。
傍晚,從前燈火輝煌的上海市街一片黑暗。
日軍在國際飯店設立了思想部,對有抗日嫌疑的人,以談話為名,帶到憲兵隊監禁拷問。一周後,陳歌辛、周曼華、許廣平等被捕。
四二年新年前夕,外國片來源已斷,元旦,有四部話劇上演,均以女性為題材。四月,上海十二家電影公司被日本統合,中華聯合制片公司(以下簡稱中聯)
成立。組織要綱規定目的為:
作為執行中華民國國策的機關,必須用電影促進國民文化,徹底普及國民教育,向國民提供健全的娛樂,充分發揮電影作為向國內外進行思想宣傳的武器之功能,宣揚建設新中國和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真正意義。
夏天,四十年未見的高溫持續不降,七月下旬,霍亂流行。
七月九日,中聯的第一部片子《蝴蝶夫人》在大光明大戲院首映。

公映特刊封面
大光明為西片首輪影院,此前不能放映國產片。
特刊扉頁刊載了中方最高負責人張善琨的「獻詞」, 強調了將電影從「商品」改造為「藝術文化品」的決心和方法,特別指出:
特設一科,聘請專門人材,按照各片的情調,配以音樂效果。總之,我們的製作態度是,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務期卅年的中國電影歷史,更能發揚光大,寫成輝煌的一頁!
公映兩天後,觀眾小平在《平報》發表了觀後感:
總該記得吧?數年之前,上海連續放映了一兩年的《蝴蝶夫人》,主演人薛爾維雪耐(另譯作薛爾維雪妮)一舉成名,那是一部哀艷的戀愛影片……因此當時轟動了中外影壇……。
現在我們的影壇,也搬演了《蝴蝶夫人》,而且又是中華聯合股份有限公司處女作,換句話說,《蝴蝶夫人》是劃時代的獻映,從今以後,中國的電影從業人員,在同一步伐下,為自己的責任而努力,為自己的國家而奮鬥,因此,《蝴蝶夫人》可說是一個寶貴的紀念。
編導者李萍倩,主演人陳燕燕與劉瓊,都是第一流人才,李萍倩是以「細膩」 的手法聞名於影壇的導演。在他編導下的《蝴蝶夫人》,劇情與好萊塢的《蝴蝶夫人》稍有不同……
在九十餘度(筆者註:華氏)的熱浪中,看《蝴蝶夫人》好像吃了一杯「冰激淋蘇打」。
一 文本的衍變
《蝴蝶夫人》的原始文本为美國作家約翰・路德・郎的小说,發表於一八九八年。講的是美國海軍軍官平克頓在長崎短期駐紮期間,「租」娶了十五歲的日本少女蝴蝶,他以一張租借九百九十九年民房的契約(實際上每月底均可解約)得到蝴蝶的信任,接著又勸蝴蝶改信基督教。不久平克頓返美,承諾蝴蝶「當知更鳥築巢時」即回。一年後,蝴蝶生下一子,平克頓給的生活費日漸匱乏。苦等三年後,平克頓攜同美國妻子終於來日,他不見蝴蝶,但要求蝴蝶交出兒子。蝴蝶用父親留下的短劍——上面刻有「若不能名譽地活,便光榮地死」——試圖自刎。看見流出的鮮血,她想起了平克頓的人生觀,念頭一轉,選擇了活。
小說面世後兩年,在美葡萄牙裔劇作家兼導演貝拉斯科將其改為獨幕劇,結尾改為蝴蝶自刎後,平克頓及妻趕到,大幕落下,定格在平克頓擁抱蝴蝶和手持星條旗的孩子的造型上。一九〇〇年四月,此劇在紐約上演,大受歡迎,五月又去倫敦公演。一九〇四年,普契尼將其改編為歌劇,結尾是,臨終前平克頓出現,抱起了蝴蝶。
此文本凸顯了二十世紀東西方的社會矛盾——種族的,男女的,經濟的,宗教的,不同版本各異的細節,尤其是結尾透露出背後的社會規範。
隨著新媒體電影的興起,該文本獲得了青睞,默片時期便有了美國版、德國版,三十年代好萊塢又將其再次搬上銀幕,四十年代後,誕生了上海版、香港版、日本版,上世紀九十年代還有了法國版。
二 好萊塢版在上海

西海戲院廣告(《申報》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轉引自中村翠論文
據研究者中村翠考證,一九三三年二月廿四日,《蝴蝶夫人》在上海租界中心的光陸大戲院和蘭心大戲院公映,從頭輪到三輪影院,連續上映了六個月。巴黎大戲院四月的廣告宣稱,五天中有一萬八千人觀看,男女老幼交口稱讚。在上海大戲院公映的一周,有七萬多人觀看。
當時,九一八(一九三一年)事變及上海事變(一九三二年一月)已發生,反日浪潮日益高漲,隨著放映區域的推移,廣告詞發生了變化:頭輪影院的廣告為「悲酸沉痛哀感絕倫大悲劇」,聚焦於「赤裸裸介紹東洋藝妓院的花絮・細膩地描摹洞房花燭夜的歡娛」;及至三輪的西海戲院,廣告詞變為「膽大大的直敘美國兵拋棄日妓」,下面還附有「我們看了心中極痛快」的感言。因為戰事,民族感情壓倒了一切。
三 電影音樂
在淪陷的語境中,中聯又是怎樣演繹《蝴蝶夫人》的呢?
《特刊》中的本事如下:
北京某大學的學生劉伯瑤暑假旅遊到華南濱海某地,路過某街,見有懸牌蝴蝶者,乃知新妓院開張。妓女蝴蝶,系出名門,知詩書,美風姿,因父死,家道中落,其母受人慫恿,開設書寓,藉選金龜佳婿。是日,劉入作漁郎,蝴蝶初落平康,固無勾欄中人習氣,劉頗愛之,加之與談身世,憫其孤苦,慰之,贈與情歌,共成鴛鴦。……蝶感劉誠懇,即思全盤寄託與劉,母亦深許。論婚嫁,收牌子,時至七夕,共誓神前。
到底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磨練的,有著奇異的智慧的上海人!文本已脫胎換骨,全盤中國化,「美」「日」自然消亡。收尾仍是女主角自殺,但死因卻有著質的區別——非男方背叛,而是其父作梗造成的誤會所致。編導李萍倩反復強調的是,此片「沒有一個壞人。悲劇演出如此辛酸,舊禮教所賜也」。他意不在追責,而是――
《蝴蝶夫人》是一首抒情詩,全片自始自終在靜穆優美的旋律中進行。譬如劉瓊邂逅陳燕燕,一直到劉瓊北返,幾乎是二分之一的戲,在詩意的環境中進行著……。
傳達詩意般的美,是編導的目的,也是中聯的韜晦策略,利器便是「音樂」。
據機關報《中聯影訊》介紹:「過去國產電影對配音工作相當馬虎,各影業公司很少有特設音樂科,至多由一二個人主持而已,原因是缺乏音樂人才及經費。中聯公司成立以後,決意提高國產電影的技術水準,對音樂相當重視,人才有梁樂音,陳伯石,黃貽鈞,陳歌辛等。對於歌譜唱片的收集,不惜重金,新片攝製之初就按照劇情的需要開始工作,如有適合的外國唱片,就先行辦購,否則全科人員自己製譜。九日公映的《蝴蝶夫人》就是音樂初顯身手第一聲,全部配合工作在開始拍片時就與導演李萍倩共同商討,所以,每一個鏡頭,每一場戲,劇情的起伏與音樂的陪襯都是恰到好處。」導演與音樂家商議的結果是以「莫查德」(莫札特)的兩個樂題為中心——「《蝴蝶夫人》的海邊花插曲,採用了聖莫查德一百五十周年紀念之作,歌曲經陳伯石李雋青諸氏悉心製為詞譜,加以音響佐助全片效果之濃烈氛圍,創中國影壇之新聲。」
海邊花插曲很快成為了宴舞廳中最流行的華爾滋曲,與《魂斷藍橋》中的燭光舞同樣的受人們的愛好。
歌詞其一
海邊花,海邊花,海浪打,海風吹!海風吹,海浪打!
愛花的人要知道花有情!
愛花的人要知道花無價!
你若真愛她,就不該讓她在駭浪颶風下。
其二
海邊的花兒溫馨,海邊的人兒輕盈。臉兒似深霞樣美麗,心兒似海月樣的光明!
你有的是海水樣的深情,我有的是海月樣的熱情。
除了一顆愛你的心,我什麼都能犧牲,我們要生死不離分,不要學那一年一度的天上雙星!
《中聯影訊》報導,電影公映的同時還打出了贈送《蝴蝶夫人》歌譜的廣告,不日便收到一萬三千六百五十八封來信,另有兩千二百一十六人到中聯寫字間面索。歌譜初版印一萬份,兩天即售罄。
《蝴蝶夫人》在大光明公映時,七天的票立即售罄,之後,又在新光大戲院放映了近一個月。
此後,中聯的音樂跟電影,便如影隨身,歌唱插曲,連綿不斷。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行進在大上海劇場前的日本軍隊。引自《上海租界滅亡十日史》華中鐵道株式會社刊
尾聲
寫到這裏,不禁猶豫,反躬自問:在刺刀圍城的時代,拍那樣的作品,難道不是製造麻痹人的鴉片嗎?
想起了逝去不久的疫情歲月。與彌漫在空氣中的、無形的病菌作鬥爭,除了病毒科學家們能直面敵人以外,普通人只能被動防禦,別無他法。防禦的關鍵是提高自身免疫力,將身體鍛煉得百菌難侵,其前提必須是,有一顆強韌的心。而音樂藝術,便是滋養心靈的糧食。
神經科學家說,音樂是通過啟動大腦的默認模式網路 (Default Mode Network,DMN),將意識轉向自身的開關。音樂幫助人從關注外部刺激的狀態轉向,聚焦於自己的情緒、記憶及自我認知。
音樂像光一樣從下意識中流入人腦,讓人感動、奮發、療愈創傷……。
隔著八十年的艱辛路往回望,驀然看清,《蝴蝶夫人》猶如標杆,高高地豎立在中國電影音樂專業化道路的起跑線上。從此,孤寂的深夜,人們有了「薔薇薔薇處處開」的歌聲陪伴,憤怒時,聽金嗓子高歌《瘋狂世界》,更有「天下興亡,天下興亡,責任每個人同樣有份」的《舞女曲》呼喚著中國心。我歌我嘯大江旁,青山不老,綠水綿長……。
二〇二五年八月三日完稿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邵迎建簡介: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文學。主要著述有:《張愛玲的傳奇文學與流言人生》(增訂本)、《抗日戰爭時期上海話劇人訪談錄》 、《上海抗戰時期的話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