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思
外婆坐在夕陽裏,柔軟得像一朵雲。黃色的風吹亂她白色的頭髮,像是斑駁已久的黑白照片。外婆看了看我,喃喃地說:「人呐,是條苦蟲,沒有吃不完的苦,只有享不完的福。」
一九二九年,外婆出生於皖北貧瘠的小山村。為了能嫁個好人家,六歲時,外婆便被裹上小腳。外婆的童年和青春,就像她那雙永遠長不大的小腳一樣,局促不安。
十一歲那年,抗日的戰火燒到了皖北,為了省下糧食,外婆成了隔壁村彭家的童養媳。抗戰結束,饑荒蔓延,丈夫彭順舟看了看面黃肌瘦的外婆,說:「走,我們去逃荒。」
兩人走走停停,一直走到藕塘鎮,走不動了,因為外婆發現自己懷孕了。夫妻倆很高興,貧賤的日子總算閃出一絲光亮。
藕塘鎮水多河寬,以養藕、魚為生。淤泥裏挖挖,便可得幾根藕節,燒水煮熟,粉且脆。彭順舟便挖了許多藕來煮,頓頓吃藕。不久,女兒生下來了,乾癟瘦小,像一段黑小的藕節。彭順舟看了看面色蒼白如藕的外婆,夫妻倆抱頭痛哭。
許久,外婆對彭順舟說:「出去看看吧,能不能弄點別的,只要不是藕,都行。」
彭順舟說:「好。」
很快,彭順舟頭破血流地回來了,在橋洞裏哭嚎了幾天。一是因為偷紅薯被村民打得滿身是傷,疼。二是因為女兒夭折了。三是因為外婆連驚帶嚇,一病不起,臉色蠟黃,眼見得撐不了幾天了。
彭順舟對著外婆說:「這日子,真的……沒法過了……我要走了,再不走,我也會死在這裏的……」
外婆掙扎許久,終於坐了起來,大口喘著氣說:「你想走……可以。但……你要先把我們的女兒……埋了。」彭順舟說:「好。」便抱起孩子,低著頭,走開了。
當彭順舟的身影消失了之後,外婆無力地看了看外面藍藍的天,白白的雲,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外婆說,當她再次醒來的時候,身邊多了一位老奶奶。老奶奶面容微笑,慈眉善目,狀態安詳,老奶奶喂了外婆半碗麵湯。夕陽下,端湯的老人渾身發著光,外婆覺得身體暖和了起來,力氣也在慢慢聚攏。
外婆問:「我這是死了嗎,你是菩薩嗎?」
老人說:「人間哪有什麼菩薩,佛是死了的人,人是活著的佛。我看你還有半口氣,剛好我有一碗湯,就救了。你要是不想死,就跟我去要飯!去南方,南方有大米。」
外婆掙扎著說:「好。」那一年,外婆十九歲。
……
外婆靠乞討為生,受盡磨難,嫁了兩次人,又懷了幾個孩子,不過只有我母親活了下來,生活也終是不如意。一直到十年後,那個男人再次出現。
原來,那日彭順舟從藕塘鎮逃出後,一路逃荒要飯。後來,聽說朝鮮那邊打仗了,他想,反正都是死,只要不是餓死,都行。於是便參了軍,身負十幾處槍傷。終於,戰爭勝利了,復員回家,享受殘疾軍人特殊待遇。又憑藉著這個身份,把外婆再次「娶」回了家。
遺憾的是,彭順舟因為舊槍傷發作,留下一個未曾謀面的女兒,便很快離開了人世。不過,等待外婆的,還有一個更加大的災難。
大煉鋼鐵過後,糧食已所剩無幾。
先開始田裏還有野菜,勉強可以充饑。後來,大家只能在山裏刨地,偶爾刨出半個紅薯或芋頭,放進鍋裏多加水煮,可以勉強貼補一天。
村裏餓死人,還能抬上山埋掉,漸漸地,大家都沒了力氣,抬不動了。村口的幾間空房子便專門用來停放。能走得動的人越來越少,大家都沒精打采,東倒西歪,肋骨清晰可數,不成人形。沒事的時候,大家都是坐著,不說話。
直到有一天,一個好消息傳了過來。說是睢寧那邊沒有饑荒,還有玉米可以吃。這條消息像條野狗似的在村子裏亂竄。外婆先是不信,後來見幾個回來的人走路挺直,說話響亮,夜裏煙囪偷偷冒煙,便知道消息差不多。
外婆問:「那裏真有玉米可以吃?」
「是的!」
「能讓我們吃?」
「只要不被發現,就行。逮住了,就往死裏打!」
外婆咽了咽口水,不再說話,過了好一會,又看了看兩個餓得面色發黃的女兒,咬咬牙,說:「反正都是死,走,去睢寧!」

睢寧離外婆家約四十五公里,男子們都是中午出發,深夜走到,吃飽便回,運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帶些糧食回來。外婆便清晨出發,出發之前,讓母親在家看好妹妹,說會帶好吃的回來,母親高興地答應了。
外婆早就問清楚了走哪座山,哪條路,哪條河,也弄清楚了去的那個村叫大榆樹村,村口有棵極高的大榆樹,樹上全天都蹲著一個持槍人,持槍人看護著樹下一望無際的玉米地,玉米地的西北角有方魚塘,魚塘四周有茂密的蘆葦,從蘆葦叢裏潛入玉米地是最安全的。
外婆說她趕到大榆樹村的時候,月亮已像太陽一樣亮堂。魚塘是有的,不過沒有村子人說的那麼大,蘆葦叢也並不是太深,也不茂盛,外婆先是坐在塘邊,揉打著酸痛的小腳,讓其儘快恢復知覺,順帶觀察下周圍。過了一會,外婆逮個機會潛入蘆葦,紮進水裏,爬進溝渠,像泥鰍一樣鑽進了玉米地深處,糧食的味道便像月光一樣鋪滿地上。外婆高興了,滿足了,她小心翼翼地掰了一個玉米,「啪」的一聲,玉米莖折斷的聲音在月光下被傳得很遠,玉米細細長長的葉子在野風裏顫動。
「誰!」大榆樹裏傳來一個堅定且威嚴的聲音。外婆趕緊趴在地上,像石頭般一動不動。「我看見你了,出來!再不出來,我就開槍了!」聲音從黑魆魆的大榆樹裏硬硬地傳來。只見一個人從樹上麻利地滑下,貓著腰,手裏攥著一杆長槍,槍頭的刺刀在月光下閃著白光。很快,那人便到了玉米地頭,外婆哪里見過這種場面,只好無奈地閉上眼睛,慢慢地舉起雙手……
「撲棱」一聲,一隻黑色大鳥從外婆不遠處起飛,很快便消失在雲邊。持槍人愣了一下,便慢慢地將槍插回背上。「媽的!我以為是偷玉米的呢,原來是隻鳥。」那人嘟嘟囔囔,罵罵咧咧地又爬回大榆樹上,不見了。
外婆也愣住了,不過很快便穩住了神。她看了看黑森森的大榆樹,又看了看眼前的玉米秸,緩緩站了起來,十分警惕地剝開玉米穗的苞衣,踮起腳尖,湊嘴上前,把玉米一粒一粒地輕輕咬下,然後小心翼翼地裝進袋子裏,穩穩地掛在胸口的布袋裏。
外婆大約啃了小半斤玉米,並把啃過的玉米苞衣裸露著,這樣從外觀上看就很像是蟲鳥啄過的痕跡,外婆不敢貪多,趁著月光,鑽著溝渠,爬出地裏,穿進葦叢,像黑魚一樣隱入水中,慢慢地浮出水面。「撲棱棱」一群黑色的鳥兒受到驚嚇,忙不迭地從蘆葦叢裏起飛,躲進雲層,遁逃遠方。
「有人偷玉米了!」一聲喊叫從大榆樹裏傳出,聲音像一支毒箭一樣擊中外婆疲憊不堪的心臟。緊接著,水塘對岸,「邦邦邦」的腳步聲由遠及近地傳了過來,外婆攥緊玉米袋,撒腿就跑,奈何跑不快,怎麼辦?逮住,就是個死。
水塘對岸,蘆葦深處,「邦邦邦」的腳步聲像雨點一般砸在水面上,看不見人,只看見刺刀的刀尖在蘆葦花上方左右搖擺,忽隱忽現,刀尖上的月光像冰塊一樣窸窣作響,閃閃發光。外婆看了一眼水塘,毅然決然地又鑽了回去。
腳步聲逐漸消失,外婆便出來換氣。斜刺裏,一把明晃晃的刺刀頂在外婆胸口。「出來!還往哪里躲!」月光下,一個黑衣人,目光兇狠,表情嚴肅,持槍頂著外婆。外婆抹了一把臉上的水,抬起頭,說:「你殺死我吧,反正都是死!」黑衣人見是一個弱女子,把槍托後撤了一點,說:「糧食是隊裏的,必須留下!你,可以走!」外婆說:「一樣的,沒有糧食,兩個女兒都得餓死。」黑衣人愣住了,又看了看外婆,然後把長槍慢慢地插進後背的槍托裏,一邊走,一邊說:「剛才明明看見有個人,一眨眼,不見了,真是奇怪!」
……
外婆精疲力盡地回到家裏,顧不上休息,趕緊把來之不易的玉米捏出幾粒,輕輕放進鍋裏,多加水,糧食的清香便撲鼻而來。就這樣,兩個女兒終於活了下來。
多年以後,外婆已不願意過多提及這段往事。不過,她總是會說起那晚的月光,以及月光下那忽閃著白光的刺刀……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申思簡介:安徽人,現定居佛山。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佛山市文學與批評協會理事,作品見諸《香港作家》、《中國文藝家》、《安徽日報》、《佛山文藝》、《少男少女》、《佛山日報》、《嶺南文學》等報刊。曾獲得《香港作家·明月灣區》徵文大賽優異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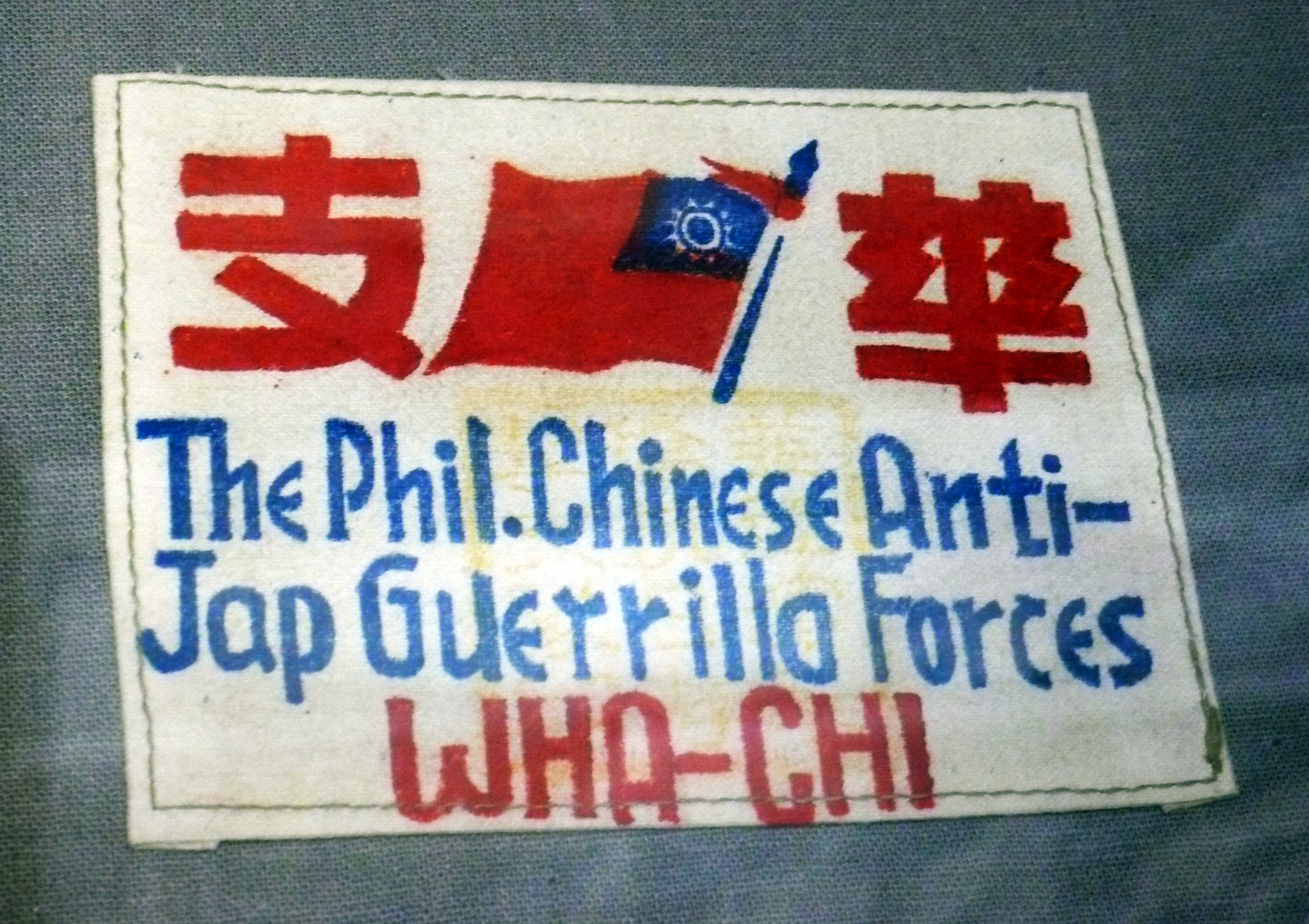





感谢编辑用稿,感恩香港作家联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