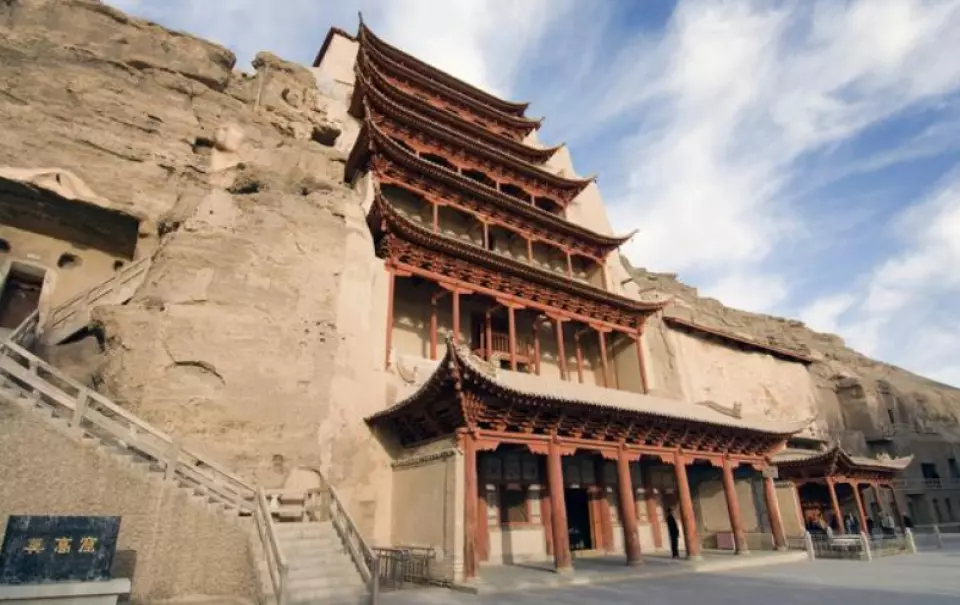黃秀蓮
四哥四嫂與我姑婆、父母相識在仄隘的空間,正因環境困逼,最易感受得到彼此的憂愁,名字中有個「俠」字的四哥,適得其時地發揮了俠氣,於是一道光環牢牢地鍍在他們交往的歷史裏,本來貧寒的歲月因而閃著光芒透出溫暖。
人與人的相遇必然是時空的巧合,往後相交更需要借助於一個據點,讓感情扎根,然後縱深發展到盤根錯節花繁葉茂,風雨不移的情誼多半是這樣結下的。那據點是一幢戰前舊宇,這類房子受政府租務管制,租金不可貴於一九四一年的水平,業主不得隨便加租或逼遷,租金廉宜加上居住權受保障,自然成為窮人棲身之所。那幢舊樓位於深水埗基隆街,四層高,殘舊破敗,木樓梯踏上去就吱吱作響,梯板好像會裂開甚至塌陷似的。騎樓挺大,只有這兒有光,另有幾間無窗的房間,燈影昏暗,廚廁幸而有窗,也有點風吹進來。包租將房子用木板分隔為幾個小房間,將之分租給三房客,四哥跟我們都是三房客。份屬同屋,彼此只是一板之隔,咳嗽、打鼻鼾、孩子哭泣、夫妻齟齬都聽見,少了私隱多了理解,鄰里相依之情由是建立。

業主跟我們是親戚,四哥與我們毫無血緣關係,他排行第四,人人都稱他為四哥,連比他年長的姑婆都這樣稱呼。初時四哥獨居板間房,妻子仍在廣州等候機會來港,我舅舅要跟鄉下的女友成親,因為無法負擔鄉下的繁文縟節,打算在廣州結婚。四哥得悉,便叫妻子想辦法幫忙,結果四嫂把自己的房間借出作新房,自己搬回娘家幾天。俠氣義氣之所至,鞭長亦及,全賴另一半來支持,四嫂配合無間,完成丈夫跨境式照顧朋友的心願。後來四嫂探得門路付了費用,登上一輛貨車偷渡來港,車上除了她一個女流,其餘都是漢子。他們坐在本來載貨的車尾,車頂有蓬蓋,掩飾了行藏,終於繞過逶迤而漫長的大埔道抵達了市區。貨車依照約定停在「嘉頓」麵包廠房,讓人蛇下車,她識字,認得「嘉頓」二字,知道自己已安全抵埗,忙向途人問路,不太艱難便尋到基隆街。來應門的正是一口開平鄉音的母親,大家打個照面,當時她們都只得二十來歲。四嫂說不純的廣州話,與母親相交數十年,依然雞同鴨講,母親的鄉音她大概只明白一半。
基隆街那低矮的房子我們只住了兩年,因父親從緬甸回來,便搬到汝洲街七層高的唐樓,業主也是親戚,父親付過「匙金」(即頂手費)便成為包租。姑婆早到香港,本來跟家姑同住,受盡欺負,向母親哭訴,母親說:「搬來跟我住吧,我們有粥吃粥,有飯吃飯!」從基隆街到汝洲街,一直患難相依。姑婆的身世是一個荒謬年代的反映,她在鄉下嫁給富戶,丈夫像許多四邑人一樣要到美國闖天下,婚後不久便離鄉遠去。不久大陸的政策要鬥爭擁有田產的地主,姑婆因夫家富裕而受累,慘被罰跪玻璃,淒涼光景實在不忍提。她心思細密,處事謹慎,離開鄉下前悄悄把金器用罎子盛著,埋在家裏某處,相信埋藏得非常隱蔽,不會讓人發覺。家鄉她再也不會回去了,可是金子怎辦?四哥是最值得信賴的人物,有次乘他回鄉,便託他繞路到開平把金子取回來。這差事極之難為,於四哥是大考驗。一是如何避開眾人耳目,揮鋤挖泥取金,怎樣做到神不知鬼不覺呢?二是海關會隨機檢查旅客行李,尤其是形跡可疑的,當時黃金嚴禁出口,一遭發覺,立刻充公,且不予文件證明。這情形常有,姑婆與四哥雙方都清楚知悉的,行動完全建基於信任。不過萬一倒霉,黃金被海關沒收,這不止叫人難過,四哥也擔心……
四哥身形高瘦,瘦而硬直,濃髮大眼,雙目炯炯,嗓音清亮,說話爽快,手腳麻利,一站出來就有點威儀。挖掘金子之經過、懷璧在身過海關之情形,我不知曉,只記得姑婆稱讚四哥人好。姑婆五十出頭就去世了,四哥四嫂送殯送上山墳。後來四哥常說:「你姑婆在生時常說,她一生人最敬重的是我!要是我說過海關時給查出來了,黃金全沒收了也可以的,可是我把金器一件不漏交還給她。姑婆喪禮那一段日子我天天都要開夜工,但姑婆那麼信任我,再眼睏再疲倦也要送她上山。」墳前撒一把黃土,厚厚重重的信任跟隨著黃土,細細碎碎的輕輕就落在棺木上,長埋了諾言,長青了德行。
基隆街老屋終於要拆了,租客可獲業主賠償,其中一個鄰居在電力公司工作,懂得條例,教四哥快點在板間房裏搭建「閣仔」(天花板下加建樓閣),把居住面積加大,則賠償額亦會加大,果然如是。同屋之間互通聲氣,在面臨遷拆的彷徨間相濡以沫,又是一段情義。四哥搬到大南街唐樓一間有窗的板間房,四個孩子陸續出世,直至一九六九年入住長沙灣政府廉租屋邨,他們終於在熟悉的地區擁有獨立的單位,扎下根,怡然生活。四哥本來在工廠工作,既然居住環境改善,便有了新的打算,與其付車資和午飯費用,不如辭工,寧願留在家裏與妻子一起車牛仔褲。兩部電動衣車並排放在屋子裏採光最理想的地方,衣車從清晨就噠噠響起,堅韌的牛仔布在腳踏和車針強力帶動下,線步緊密地縫成時尚,風行全球。我母親也在家裏車牛仔褲,那牛仔褲廠在深水埗,母親向老闆推薦四嫂,老闆問:「你朋友車得好嗎?」「她是我師傅,你說好不好?」四嫂在廣州已學會車衣,把知識技巧都傳授給我母親,二人又多了一重師徒關係。許多年後,母親再作介紹,為他們的兒子做了冰人,撮合了良緣。
後來牛仔褲廣告「Levi's」、「Apple Jeans」、「York」不復鋪天蓋地,車衣廠的訂單不再應接不暇,香港的製衣業已日漸式微,他們亦步入暮年,正好是退休時節,四哥便約我父母一塊兒隨團去北京旅行,患上心臟病的父親略帶憂鬱且動作遲緩,想不到在四哥鼓勵和照顧下,居然登上長城,那趟旅途載欣載歡最堪回憶。四哥又借賦閒而大展廚藝,其拿手好戲是蟠龍鱔,先買一尾生蹦活跳的鱔魚,巧用刀章把鱔的肉與皮斬得連而不斷,還有一道秘技是向相熟肉販預訂一塊網狀的豬橫膈膜,裹著鱔,用竹籃子隔水清蒸,豬油滲進白鱔則去寡提鮮且鱔質油潤,彈性的肉質混和了蒜頭豆豉,濃香四溢,更難得賣相滿分,一吃難忘。四哥在廚房忙完後就與客同樂,且吃且飲且高談,興會淋漓。不請客的日子也習慣在晚飯後喝雙蒸,酒量很好,也抽煙。他的廚藝不止滿足了美食主義者的胃腸,還扶持了病者的康復,我動鼻竇炎手術後,四哥希望我儘早復元,持續多天給我送田雞焗飯。
四哥偶然發些議論,如:「天天都那麼多人從羅湖來港,難道人人都睡天橋底?香港樓價怎能不升?唉,只是我沒錢買樓吧了。」這番話說在八十年代初。我家在八二年抽到居屋,搬到長沙灣淺褐色的房子;九四年他們的屋邨重建,便買了我們旁邊新建的白色居屋。來自基隆街戰前舊宇的兩戶,後來皆自置物業,又巧合地挨肩而住,既是緣份所繫社區所依,亦是房屋政策的落實,更反映了香港人上游的決心與改善居住環境的努力。
九七移民潮下,我父母移居到多倫多數年,豈料期間四哥患了肺癌,遵醫生之命立刻戒了煙酒,化療後的樣子我竟然認不出來,一年多便去世了,唉!他還不到七十哩。後來父母回流香港,失去了四哥這中流砥柱的朋友,一切變得索然。幾年後父親心臟病發,半小時間就逝去了,享壽八十二。在艱難的香江歲月中,他們都胼手胝足養大兒女,然後安享晚年,最後人事代謝,歸於寂滅。
四哥的剛猛與妻子的平和互相配合。每次去探望四嫂都見她坐在採光最理想的沙發上打毛線,跟當年車牛仔褲相似,奇怪是她已年等耄耋,居然不用戴老花眼鏡而能夠把圍巾打得針步結實,一針也不漏。什麼人請她打圍巾都一口答應,連相熟的茶樓侍應也領受手打毛線的溫暖。我坐在她身邊聽她憶述如煙往事……童年時替爸爸買鴉片煙,出入煙窟,品流複雜,竟不害怕……舊樓包租婆耳朵不靈,常常罵人,幸而不曾罵她……她身體挺好,除了雙腿漸漸不良於行。「我很想去探黃師奶,可是走不動了!住基隆街時黃師奶買菜時都順道替我買,說多幾斤也拿得起。」當時她們都只得二十來歲,「我媽已經不很認得人了。」
在和合石墳場,我在四嫂墳前撒一把黃土,黃土細細碎碎的輕輕就落在棺木上。世事玄妙,在我擬定了「貧賤之交」這題目的晚上她去世了,比我母親小兩歲,享九十五高壽。黃土細細碎碎的落下,冒險掘金、懷金在身、瞞過海關、悉數奉還的俠義,車牛仔褲為生的勤奮,蟠龍鱔宴的豪爽,暢遊北京的歡欣……賤之交的含金,如細細碎碎的黃土,給早上的陽光照耀得閃閃的。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黃秀蓮簡介:廣東開平人,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中文系畢業,從事散文寫作,獲中文文學獎及雙年獎散文組獎項,並任中文大學圖書館「九十風華帝女花──任白珍藏展」策展人。著有散文集《灑淚暗牽袍》、《歲月如煙》、《此生或不虛度》、《風雨蕭瑟上學路》、《翠篷紅衫人力車》、《生時不負樹中盟》、《玉墜》、《揚眉策馬》八本,數篇散文獲選入中學教科書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