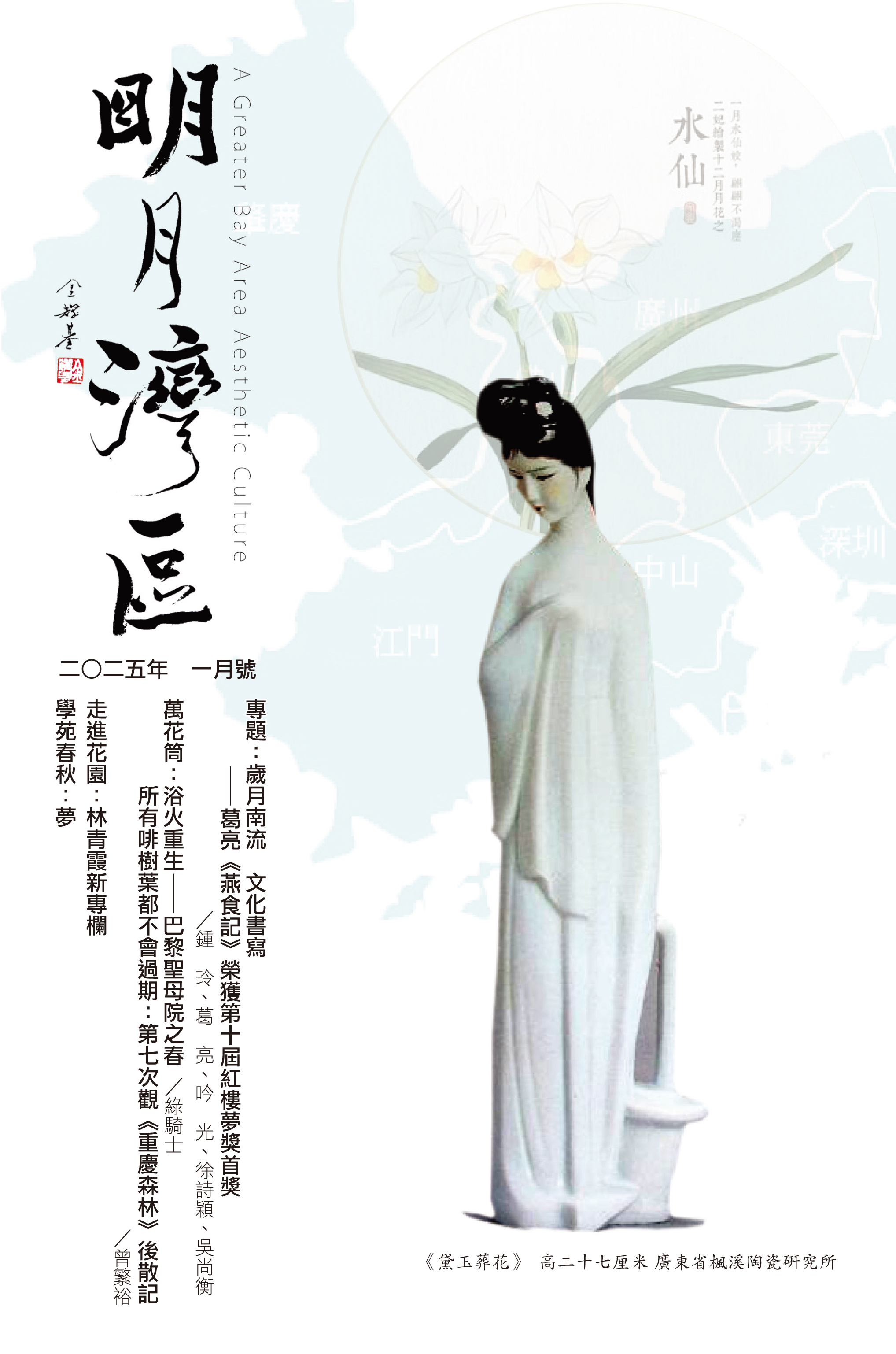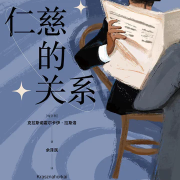吳志良
編按:「只要澳門作家在當前百花齊放的榮景中齊心協力,互相扶持,用心栽花種草植樹,必能創造出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的創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為說好『澳門故事』立碑,更為擁抱人文灣區和人文中國,增添斑斕華彩。澳門文學長出參天大樹,必將指日可待。」今年適逢澳門回歸及特區成立二十五周年紀念,本刊特邀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撰文回顧澳門文學的發展、重要歷史時刻與豐盛成果。

澳門文學因着澳門擁有豐厚歷史文化底蘊和充滿人性光輝的面貌而綠草成蔭,生氣盎然。 (資料圖片)
澳門,由於她的歷史和地緣關係,是近代史上中西文化最早交匯的地方。自明中葉以來,中外文人墨客相繼來到澳門或附近地區旅居、遊歷,所見所聞,無不觸動他們的情感和靈感,在諸多文學佳作中也留下了這些蹤跡。湯顯祖所作的《香嶴逢賈胡》,便反映出他首次遇見西方商人的驚喜,在《牡丹亭》中以佛學的宗教標記指代澳門天主教傳教事業的蓬勃景象;葡萄牙詩人賈梅士(Luís de Camões)遊歷東方所作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Os Lusíadas,又譯《葡國魂》)的部分情節,早已通過紀念建築的描繪而深入澳門民心,成為了澳門城市文化標記的一部分。
及至清代,吳歷創作《澳門雜詠》三十首,其中「一曲樓台五里沙,鄉音幾處客為家。海鳩獨拙催農事,拋卻濠田間浪斜。」生動地反映出當時澳門商埠的地位以及在經濟上對海外貿易的倚重。晚清來澳門生活的葡萄牙詩人庇山耶(Camilo Pessanha)所創作的《滴漏》(Clepsidra),更被葡萄牙文學界視為象徵主義詩歌的典範,對二十世紀葡萄牙的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產生巨大影響。
澳門文學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
進入二十世紀,澳門文學進入百花齊放的繁榮年代。中文、葡文以至「土生葡語」文學都取得長足的發展。以創作舊體詩詞為主的「雪社」,與民國幾乎同齡,雖然它只是一個由五六個人組成的雅集,沒有嚴密的組織,但作為澳門文學史上第一個以本地居民為骨幹的文學團體群落,對澳門詩歌發展有突出的貢獻,影響也非常深遠。上世紀三十年代,筆名「華鈴」的澳門詩人馮錦釗在上海發表過大量新詩和譯作,在抗戰時期名噪詩壇。而一九五○年《新園地》創刊和六十年代「紅豆文社」的成立,既標誌着進步文學與澳門文學合流,文學創作題材走向本土化,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殖民管治的環境下澳門基層社會生活的種種現實,奠定日後澳門文學蓬勃發展的根基。葡裔社群在同一時期也湧現出一批既反映族群生活,又反映對不同族群和文化之間和平共處的期盼的作者,例如江道蓮(Deolinda da Conceição)、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飛雅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等。
一九七六年,葡萄牙進入第三共和,權力下放讓澳門掀開社會制度本地化的歷史新頁,並隨着中葡兩國順利解決澳門前途問題而進一步深化。漸漸地,不少在澳門居住的人從過往「逗留」的心態演變成「定居」,而各項社會設施的建設和落成,使澳門的不同群體有了共同相處的空間和溝通的機會,造就了澳門本地造型藝術、文學創作、歷史研究和出版方面自八十年代開始蓬勃發展。在這段時期成立的「澳門筆會」,目前仍然是聯繫團結澳門文學創作者的廣闊園地,在構建澳門本地身份認同的過程中,發揮總結經驗、鞏固記憶、提煉精粹、充實內涵的作用,現已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報界和學界在推動澳門文學發展上也不遺餘力。一九八三年,《澳門日報》開設「鏡海」文學專版,翌年舉辦「港澳作家座談會」,呼籲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時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於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舉辦過兩次澳門文學座談會,進一步凝聚澳門文學界的集體意識,大大激發了澳門本土文學創作的熱情。
一九九二年,澳門基金會改組,成為一所致力推廣澳門的教育、科學、文化和中葡合作的機構,也為抒發澳門文學創作熱情提供必不可少的平台。在澳門筆會和《澳門日報》的大力支持下,澳門基金會設立「澳門文學獎」和「讀後感徵文比賽」活動。隨後,澳門基金會編輯出版澳門文學「八選」——《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當代詩詞紀事》、《澳門短篇小說選》、《澳門散文選》、《澳門新詩選》、《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當代劇作選》,以及《澳門現代詩選》,形成澳門文學的基本面貌,樹立起澳門文學界的群像。
為發展和壯大澳門文學事業奠定基礎
就在這個時期,在澳門基金會的統籌下,澳門的文學界也逐漸與內地的文學藝術界團體建立聯繫,還在回歸前夕與中國文聯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二十冊的「澳門文學叢書」。隨着澳門回歸祖國的大家庭,本地文化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並存的特性既是社會現實,也成為澳門社會的普遍共識。澳門回歸二十五年,既是澳門歷史上發展得最快、最好的時期,也是澳門文學最活躍、最繁榮的時期。澳門文學界不但有幸成為這個激情澎湃時代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更有幸成為這個翻天覆地時代的記錄者和書寫者。「澳門文學獎」和「讀後感徵文比賽」的參賽規模不斷擴大,現已成為代表澳門文學界最優秀一面的品牌項目,加上由其他文學團體和文化主管部門舉辦的「澳門文學節」、「紀念李鵬翥文學獎」、「澳門文學館」等,更為儲備澳門文學創作人才提供平台,為進一步發展和壯大澳門文學事業奠定基礎。
事實上,澳門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大家庭的一分子,既有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的基因,也由於澳門城市開放包容的特性,而又有着她獨特的個性。澳門文學的個性也隨着澳門城市的變遷和發展而變得更加鮮明,藝術表現方式也趨向多元,其背後的思想意涵也漸漸成熟。以「澳門文學獎」為例,主辦機構注意到澳門在從以往一座具有現代氣息的城市,發展至今成為一座國際化的城市的過程中,她的知名度、關注度在華人世界裏也越來越高,因此從第十二屆開始,把參賽對象擴展至全球華人,目的是希望澳門文學在既有以本地視角創作的作品基礎上,盡可能吸納以外地視角觀察澳門的作品,通過不同表現形式和不同思想之間彼此交流、碰撞,提高澳門文學的參與度、質量和傳播力。目前本地作品和外地作品的參賽比例大概是二比一,獲獎的本地作品既有資深作家,也有青年後進,外地作品對澳門的想像,也為我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新鮮感。
二○一四年,澳門基金會與中華文學基金會合作出版「澳門文學叢書」,至今已出版五批共七十九冊。「澳門文學叢書」將古今、中西、雅俗兼容並蓄,呈現出一種豐富多彩而又色彩各異的「雞尾酒」式的文學景象,這在中華民族文學畫卷中頗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續發展的文學。「澳門文學叢書」體現着一種對澳門文學的尊重、珍視和愛護,極大地鼓舞和推動澳門文學的發展。叢書是澳門回歸之後,文學收穫的第一次較全面的總結和較集中的展示。從全國角度看,這又是一個觀賞的櫥窗,內地寫作人和讀者可由此了解、認識澳門文學,澳門寫作人也可以在更廣遠的時空裏,聽取物議,汲取營養,提高自信力和創造力。
澳門文學再上層樓的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為澳門文學再上層樓帶來機遇。基於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歷史和地理條件,由廣府文化、客家文化、華僑文化和粵商文化作為主要組成部分的嶺南文化,是構建灣區文化共同體的豐富泉源,而澳門數百年不間斷的中西交流經歷,不僅奠定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地位,也造就了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事實上,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貫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鑑豐富經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獨特話語體系,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文明實驗室。澳門最擅長的中外文化交流互鑑,也是國家在全力提高軟實力的當下所最需要的,也是澳門在協助文化強國建設,推動灣區文藝創新中最能發揮作用和作出積極貢獻之處。
正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本身既有的共同性、獨特性和多樣性,為我們把文化資源優勢轉化為文化發展優勢,通過文學創作展開形式多樣的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提供格外優越的條件。澳門的文學不僅書寫小城的人事景情,其視野也逐漸拓展到更廣闊的時空,把城市的命運與國家和世界的命運更緊密的聯繫在一起。澳門文學作品的讀者,在中原大地也找到了知音,不少優秀作品還翻譯成外文出版。通過人文灣區的平台和跳板,澳門文學創作使澳門鮮明的文化城市形象、韻味更加親近、可愛、鮮活,大大促進了人們對澳門文化的了解和認知,為塑造灣區人文精神提供豐富的養份。
誠然,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的最終目的,是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雖然澳門文學仍缺乏標竿性作品和標誌性作家,但澳門文學因着澳門擁有豐厚歷史文化底蘊和充滿人性光輝的面貌而綠草成蔭,生氣盎然。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所折射的精神、價值和力量,必將協助澳門文學栽培出參天大樹,使澳門文學發放更璀璨的光芒,照耀更多的人們。
澳門回歸二十五年來,作家也成為這個偉大時代中的積極建設者和貢獻者。只要澳門作家在當前百花齊放的榮景中齊心協力,互相扶持,用心栽花種草植樹,必能創造出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外的創作成果和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為說好「澳門故事」立碑,更為擁抱人文灣區和人文中國,增添斑斕華彩。澳門文學長出參天大樹,必將指日可待。
(作者為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