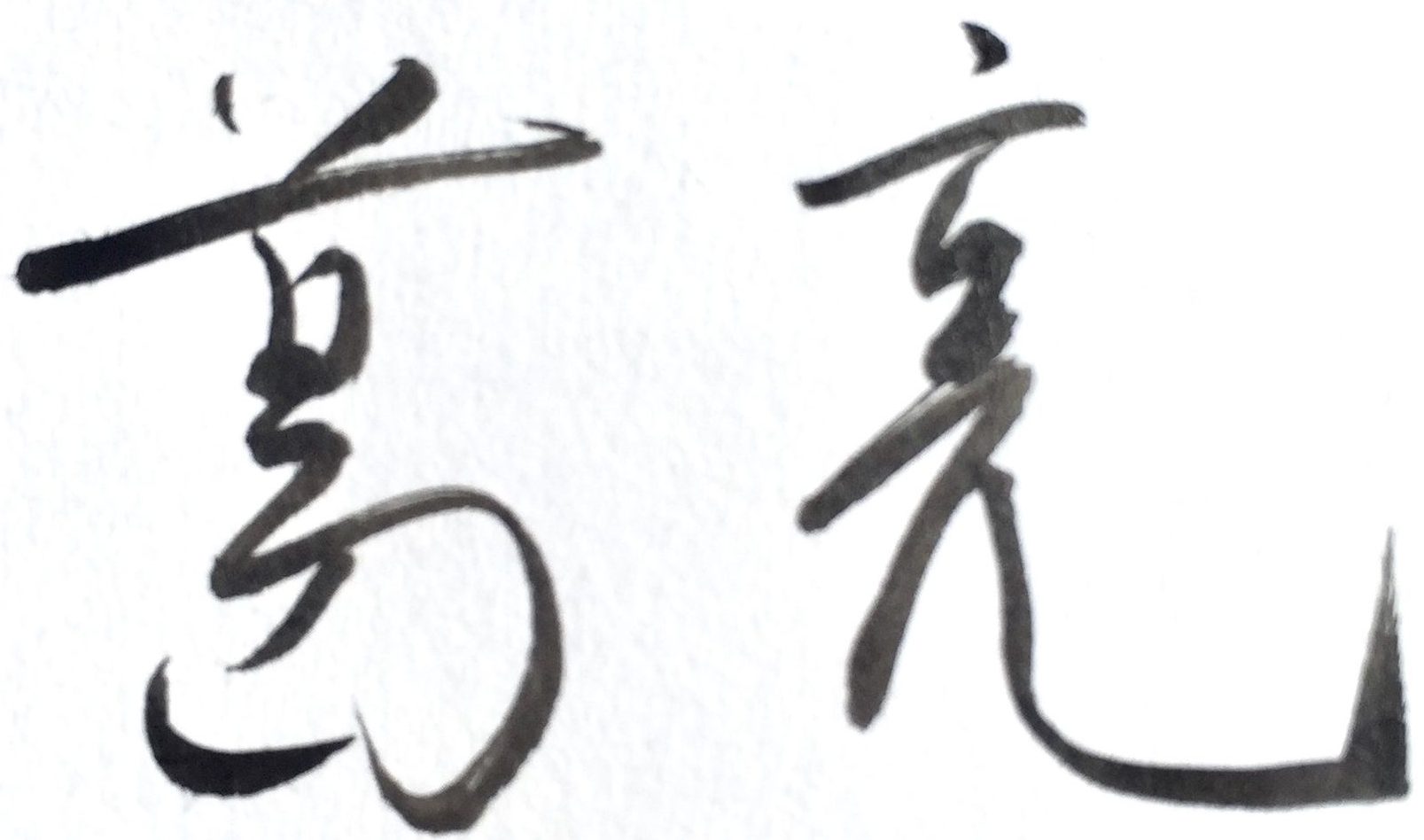 葛亮
葛亮
作家、學者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年幼時,有次關於瓷器的記憶。農曆新年的家庭聚會中,我和訪客家的小孩子,在玩鬧中打破一隻水仙盆。素來溫和的外公,出其不意地動了怒。後來知道,那是一隻嘉靖青花,產自景德鎮。有關時間,被外婆深埋在花園裏,才得以完存。它重見天日不到十年,終於粉身碎骨。我已忘了那隻水仙盆的形狀與圖案。但仍然記得落在地上,是滿地晶瑩而頽唐的瓷片。
令我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是《撿來的瓷器史》。碎裂的意義,因其不再完整,便不夠堂皇,為其憾。然而,也因是局部,管中窺豹,終得觀其盛。一個「撿」字,由字面已可見拾遺的意思。這本書的結構,以「瓷片」作眼,一章一枚,不貪其大,而聚焦於「瓷器史的重要瞬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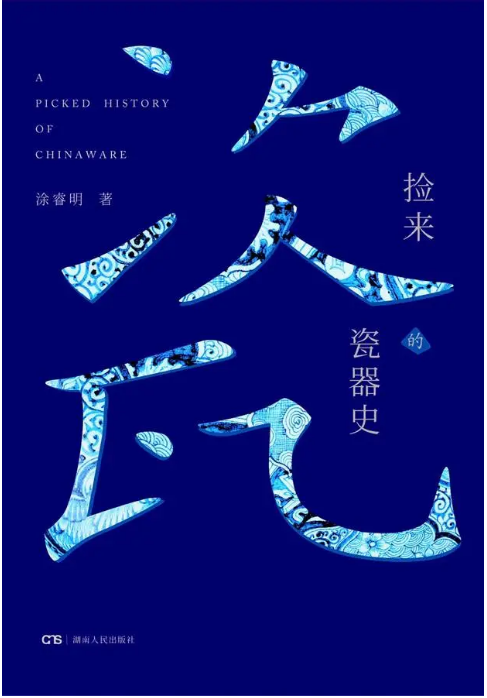
涂睿明著《撿來的瓷器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資料圖片)
或者說,這是一個有關於瓷器的故事。故者,舊也。有歲月洗禮,也有戲劇性的起承轉合。中國的瓷器,與香料一般,曾是中西外交史上的重彩。China與china的掌故,令我們對其中的政治與文化迷思念茲在茲。這本書自然屢次寫到瓷器與歷代皇室之間的關聯,縱橫中西,甚而以「皇帝的酒杯」、「皇帝的品味」、「皇帝的婚禮」作為章節名,然而,我很喜歡書中的一句話,「審美的趣味在一件件官窯瓷器中清晰地呈現。不過皇帝們以為自己在指揮一場演出,而歷史把他們當成了演員。」所有權力與自信,在時間的冥冥而視中,皆顯得微渺。藝術的成長有其定數,也有氣運。我所感興趣的,恰是若隱若現的「瞬間」史觀。在漫長而篤定的瓷器史上,那一次次的「意外」。
意外,在工藝上體現為無意為之的嬗變。就宋瓷而言,如鈞窯之「窯變」與哥窯之「開片」。前者初如無端涅槃,可遇而不可求,其中的辯證,在於「窯工們卻要努力將無迹可循的變化,轉化為可控的技術」。成為了「失控」之美至「可控」之藝的範例。而後者網紋一般的釉面裂縫,本是工藝上的瑕疵,然,宋徽宗卻於其中體會到「裁剪並綃,輕疊數重」的動人。出窯後,一次次細聲釉裂,可持續月餘至數年不絕,被稱為「驚釉」。一個「驚」字,道盡可待而不可期之珍。至於永宣青花,藍色在胎體上不可控制的暈散,以及青花料「蘇麻離青」中氧化鈷所含雜質造成局部色調中的不均勻,卻帶來中國劃一般的豐富層次與寫意效果。無心插柳,妙如天成。另有一例,是「豇豆紅」,它本是在燒製郎紅時「失敗」的問題產物。因為銅紅釉還原氛圍不足而呈現綠色,卻在紅綠相間中幻化出奪人之美。為後世傾心,冠以「美人醉」、「桃片紅」等美名,乃至競相模仿。吊詭的是,儘管對「豇豆紅」之迷戀誕生了一系列的可控工藝,如「吹釉」,但一窯能否燒出最美的成品,依然取決於「意外」與運氣。
瓷器發展的精彩,一部分也體現為其步履艱辛。在技術上的苛求與精謹,與其輝煌如一體兩面。萬曆年間,一次燒製龍缸的風險,終於帶來巨大壓力而導致景德鎮窯工的民變。一個叫童賓的窯工憤而跳入窯內。這一壯舉,令人不禁想起「干將」、「莫邪」捨身成劍的典故。現實中,他的壯舉點燃了工友們的怒火,趕走督陶官,甚至搗毀了禦窯廠。然而,這場對抗皇權如起義一般的工潮,並未受到殘酷鎮壓,而得到了頗意外的處理方式。自焚的窯工童賓被皇帝親自追封為「窯神」。雖然龍缸並未因為童賓的投窯而如神話般燒製成功。但是這次來自皇室的危機公關,卻出其不意地將政治的跌宕,化為瓷器史上的一則傳奇。
皇室依賴於景德鎮,並不代表自身一無貢獻。珐琅彩的誕生,便是紫禁城內的一次創新。它初始於康熙對於西洋彩繪的興趣,但事實上,其難度卻超過預期,以致這項宮廷實驗經年方成。並終結了青花瓷一統江湖的局面。熟悉瓷器的朋友,不會陌生於「大雅齋」的款識,這來自咸豐皇帝的手書,也是慈禧在「天地一家春」西間的私人畫室。大雅齋瓷作為宮廷著名的「設計師款」,為慈禧藝術天份的明證。其一是體量,整體化與系列化設計,為其在官窯瓷器中脫穎而出打下基礎。其二是風格化,慈禧很善於博采眾長,大雅齋的瓷器,在細節上總感到其來有自,但又有強烈的創意,如對配色運用的大膽,西太后堪稱是「撞色」設計的高手。
說起瓷器在皇室於民間的流轉,《神宗實錄》寫道:「神宗時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雞缸杯一雙,值錢十萬。」是指成化鬥彩雞缸杯。這杯子和香港頗有緣分,晚近的一次轟動是四年前,蘇富比拍賣會上,劉益謙以二點八億拍得一隻,創了中國瓷器的拍賣記錄,旋即用它喝了杯普洱。這舉動令一位叫仇浩然的香港藏家頗為不齒。而仇浩然的爺爺,即是當年名聞海上的大古董商仇焱之。奇妙之處是,這隻杯子據聞乃仇焱之的舊藏,一九四九年以一千元在香港打造了「撿漏」神話,其後輾轉於其他大藏家包括坂本五郎、ESKENAZI、玫茵堂等之手。最後落在土豪手中,被仇浩然視為明珠暗投,卻也無可奈何。既是珍品,自然歷代仿者甚眾,乾隆康熙年尤甚。成化鬥彩海藻三魚杯之類的出現,更是撲朔迷離。我大感興趣的,卻是雞缸杯在香港民間引起的別樣影響。這則拍賣盛事,讓香港人日常使用的雞公碗順勢大紅。甚而,有人不厭其煩地考證兩者之間的淵源。因其與雞缸杯太過神似。這自然是個笑話,雞公碗又叫「雞角碗」,流行於嶺南鄉野已久。若不熟悉,大可以多看看周星馳的電影。這碗時而出沒其間,更是TVB重要的道具。
談到民間的碗,自然都是集體回憶。香港的「雞公」,對仗工整的,自然是內地的藍邊白瓷大碗。瓷不是上好,可每家都有這麼一兩隻。冬天盛過八寶粥,夏日裝過酸梅湯。如今靜靜地摞在碗櫥裏,有些不用了,已落了塵。這些碗,像是家常溫潤的老人家。不是為了居家的排場,倒是像是時光堆疊的自然印痕。不完美,可是都捨不得丟棄。如斯器物的意義,自然是用於懷舊。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具體而微。那藍邊,也是如此典型的東方符號了。然而,事實上,此碗的流行卻恰非中國原創,出自舶來。在一九二○年出版的《景德鎮陶業紀事》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人民喜購外瓷貨,如中狂迷,即如瓷器一宗,凡京、津、滬、漢以及各繁盛商埠,無不為東洋瓷之尾閭,如藍邊式之餐具杯盤及桶杯式之茶盞,自茶樓、酒館以及社會交際場所,幾非此不美觀,以至窮鄉僻壤、販賣小商,無不陳列燦爛之舶來品瓷,可知其普及已至日常用品。」作為瓷器大國,民間的流行,竟是洋風中漸,幾乎成為時尚甚而擔當時代記憶,也是一種光景。景德鎮迫於市場民意,在近代的「山寨」行為,影響因此而深遠。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國首次出現了瓷貿易逆差,也是令人扼腕的事實。
正是這些對不期然的關注,成就見微知著的意義。談起瓷之所大,與中外交流之功,也令讀者會心於出其不意。其一當然是日本,日瓷之盛。有田燒可為一例,據聞其深深影響了德國「邁森瓷器」的創製。除了形制華麗的金襴手,我手上的一兩件碗盞,則簡白細膩,可見其瓷色曼妙,蓋因站在中國的巨人肩膀上。這書中提及日本人小森忍,遍仿中國名窯瓷器,幾可亂真。其技之高,作者寫道:「這完全不可思議,他簡直就是就是金庸筆下的姑蘇慕容。」慕容擅「斗轉星移」,其入化處便是以己之道,還彼之身。對應小森在華仿製復興中國瓷器,可謂恰如其分。而另一節,說的是中西外交史上一次極具象徵意義的事件。英國的威治伍德瓷與中國官窯,在乾隆皇帝壽辰之時首次會面。這其間的交流、碰撞與制衡,以「碰瓷」為章節名,可說是意味深遠,又令人莞爾。
法國人佩雷菲特將這一刻記錄在《停滯的帝國》中:「一七九三年的相遇好似兩顆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險家到了獵頭族之中,而是兩種高雅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發現。」這次相互發現,並沒有一個十分美好的結局,甚而顯得尷尬。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皇帝的傲慢與硬頸的英國使臣馬戞爾尼,在禮節上互不讓步。然而,他們畢竟留下和帶走了,彼此的瓷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