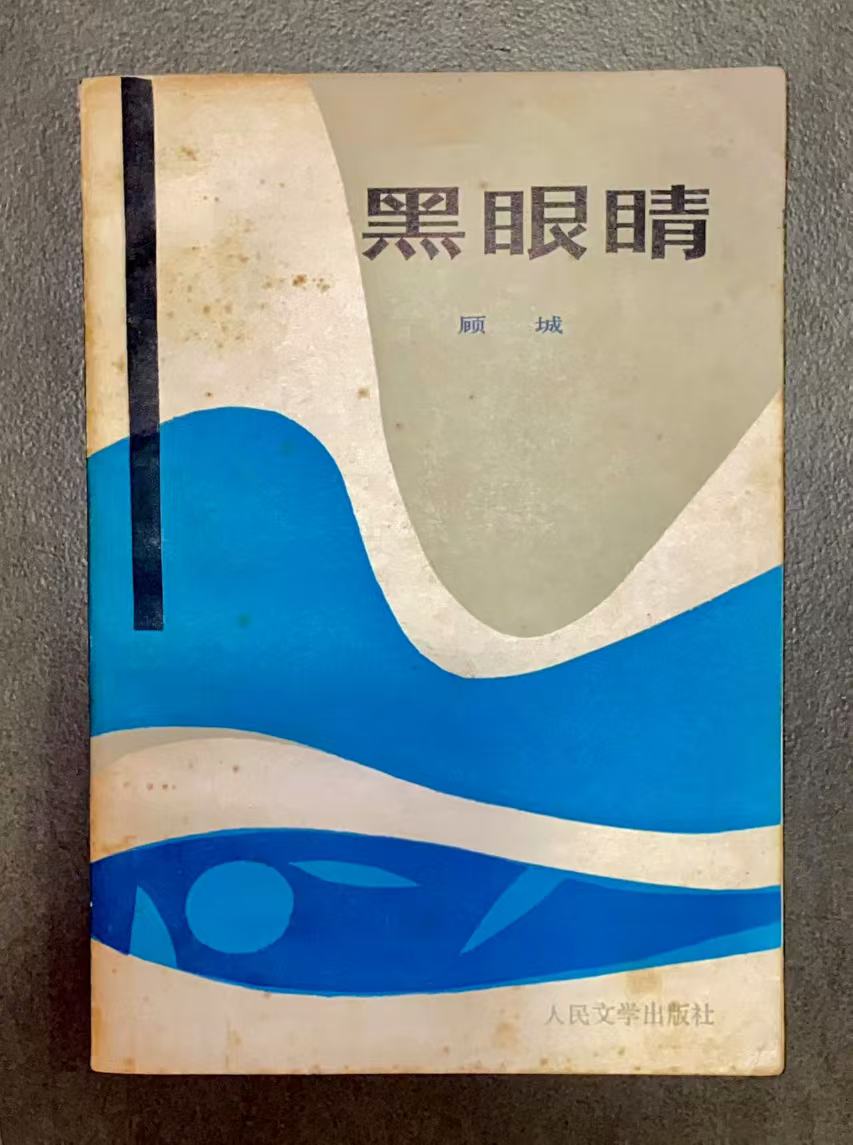江 揚

文萊清真寺。(作者提供圖片)
飛機降落在文萊首都斯里巴加灣市時,已近黃昏。
這個讓我在地圖上尋找了半天的國家,是舉行世界華文作家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文萊。它偏安一隅於東南亞婆羅洲的西北角,瀕臨南中國海,面積比廣州還要小一點。就這點土地,還被橫叉出來的馬來西亞分割環繞,截斷為東西兩部分。
面積不遼闊又缺乏國際流量的文萊,卻因國土下蘊藏的豐富油氣資源,而成為世界上最走運的國家。四十多萬人口用不著過多操勞,更用不著「卷」,就可以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何況,除了石油,這裏還有更多神奇的東西。
接機的文萊華文作家協會文友,打著橫幅等候在大廳。雖然從未謀面,也叫不出他們的名字,我卻能從他們的眼睛裏感受到一種和善與安詳。
走出機場,迎面撲來的熱帶氣息,夾雜著花香和海水的味道。這文萊的溫度,以一種特殊的熱烈迎接著我。眼前一座藍色穹頂的清真寺在夕陽的勾勒下,顯得柔和而莊重。伴隨著日落時的高聲宣禮,似乎在提醒人們,這是一個伊斯蘭國家。
從歴史中走來的文萊,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與中國發生聯繫。有記載隋朝重新統一中國後,當時稱「浡泥」的文萊曾派使者入朝進貢,確立了與中國的宗藩關繫。明朝時期,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帶著王後、王妃、子嗣、近臣一百五十人,乘坐遠洋大型木帆船來到中國拜見明成祖朱棣。可見當時造船技術已經相當成熟,能夠承載如此多的人和物資千里奔赴。明成祖朱棣在奉天門以國禮盛情款待。
不幸的是浡泥國王在訪問期間身染重病,明朝政府竭盡全力提供醫療照顧,可惜最終未能挽回國王的生命逝世於南京。臨終前浡泥國王留下遺願,希望體魄托葬中華。

南京雨花台浡泥(今文萊)國王墓。(資料圖片)
極為難過的朱棣「輟朝三日」以示哀悼,將浡泥國王厚葬於南京安德門石子崗的烏龜山,建陵樹碑,追謚「恭順」。六百多年過去了,「古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之墓」依然在山水環抱中,向世人述說著文萊王不辭千里、欣然而至的中國和文萊交流史上深遠的佳話。
明朝人對海洋的概念是以「婆羅洲」(今天的加里曼丹島)的文萊劃界。文萊以東稱之為「東洋」,文萊以西稱之為「西洋」。鄭和下西洋,指的是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去到最遠的地方是紅海海口和非洲東岸。要知道,這可是地理大發現之前人類航海史上的偉大成就,一舉打通了從中國到東非的航路,還將亞洲非洲的廣大海域連成一氣。
前些年石油公司在文萊近海作業時,從水下六十三米處發現了一艘古代沉船,船體雖然腐蝕殆盡,但卻承載著大量塵封的歴史信息,更為神奇的是船內上萬件碼放齊整的中國青花瓷和其它文物。在文萊海事博物館裏,我看到有些保存完好的瓷器造型優美,工藝精湛,白色的釉散發著清幽的光。它可能是官窯的精品,也可能是民窯的佳作。 每一件都凝聚著匠人的心血和智慧,訴說著驚心動魄的航海故事。

文萊海事博物館的沉船瓷器。(資料圖片)
煙塵散盡,這些殘片碎瓦留了下來。沿著這條明代商船從中國起運商品後出海,途中在越南和泰國進行小規模貿易,隨後駛往目的地浡泥國(今文萊)的路線,彷彿穿越了時光的長廊。當數百年前海上貿易的盛況被歲月風乾,以標本的方式留下來的時候,在中國古籍中稱為「四海流通,交會萬國」的浡泥國從歴史中走來,被推向世人面前,不能不說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個生動見證。
也許是有一種魔力盤旋在這裏,晚清時期,或者更早年代,華人華僑乘著「下南洋」的移民潮來到文萊,就不走了。無論目的如何,從人類進步的長河看,先人們來到這裏,沿著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都承續了一種血脈,傳播了一種文明。
真的很難想象,在遠離母國的文萊,佔人口十分之一的四萬多華人華僑,百年來建立了八所華文學校。從創校初期一直到現在,他們辦學就是為了讓子孫後代能識漢字,會講漢語。學生們學習的是一種古意,是上千公里之外,過千年之間一直生長著溫情的聯繫。在學習中華文化過程中,他們愛上中華文化,運用中華文化。憑借勤勞和智慧,融入當地社會,形成一種新的土壤。既包容萬端,同時又被世界包容。

奢華的清真寺內。(作者提供圖片)
曾以為盛產石油和天然氣的文萊像迪拜一樣,到處都是缺水的沙漠,人工建造起來的摩天大廈要多豪華就有多奢侈。而反襯在我目光裏的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熱帶雨林,樹太多了,把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土地都藏了起來。聽不見酒吧的喧嘩,看不見歌廳的熱舞,遇不到人潮湧動的場面。法律規定禁煙禁酒禁止夜生活,四處都顯得冷冷清清,倒是個耐得住寂寞的好地方。草站在那裏,樹站在那裏,都不曾移動,從存在起就一直處於人類無法觸及的範圍,它的語言不是聲音是生命。
時值春末,文萊卻不把季節寫在天上,而是寫在森林。層層疊疊的綠葉,交織成一片片濃密的綠蔭。無需下車,也不需要走進森林,只要看上一眼,那種清清爽爽的涼意,就會給妳帶來河水般的慰藉。

文萊河上的高腳屋村。(作者提供圖片)
文萊河是文萊境內一條重要的河流。當船犁開水面,一群水鳥在我們船頭上方的空中飛過。翻騰的河水,無聲地流淌,看上去平靜異常,只有仔細諦聽,才能得到時間深處的消息。寬闊的河面上綴滿了星羅棋佈的水上村落,規模龐大地由數十個甚至更多的高腳木屋組成。這些村落之間通過木棧橋相連,形成了錯綜復雜而又緊密相連的水上社區。
河上諸戶,家家開門臨水。醫院、學校、警察局、消防局、商店、餐館都色彩斑斕地立在水上。煙波中的清真寺,那是宗教信仰的象徵,整座水寨都處在它的威嚴之下。船長是馬來人,馬來人的祖先以捕魚、編織、製造銅器、造船為生。隨著時代的發展,捕魚這個傳統行業逐漸式微,可居民們仍然保持著對水上生活的熱愛和依賴。他們在這裏繁衍生息,世代相傳,就像河水不停地流淌,延續著古老的民俗。

文萊河上的清真寺。(作者提供圖片)
好客的船長把船停在了他家的高腳屋前,我望過去,他的家下層無牆,只有數根木樁支撐,河水在木樁間響著有節奏的濤聲。我踩著嘎吱作響的木板,走進上層他的家門。從外面看木屋簡單,原始而古樸,內部裝潢倒挺考究,屋內設施一應俱全。船長的家人熱情地拿出馬來糕點招待我們,馬來糕點極好吃,口感軟糯,別有一番異國風味。
水上村落是一部活的歴史,它見證著古老與文明。它還會存在多久?沒有誰知道,或許會到地老天荒。當無數的木屋矗立在河水中,演繹著水上人家與世無爭的生活時,文萊,從歴史深處走來。
(首發於《文綜》二〇二四年十二月)
江揚簡介: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曾任香港文匯報首席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