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啟章
我和劉以鬯先生只有數面之緣,全都是在文學活動上。每次知道前輩在場,也會主動上前打招呼。每次他都以懇切的神情,勉勵我要繼續努力創作。我跟先生的個人交接很少,但在精神上,他是我的香港文學啟蒙者,無論是閱讀上的還是創作上的。我是到了大學時代(八十年代下半)才知道有香港文學的存在,才認識到香港也有文學作家。當時接觸到的三大代表人物,就是劉以鬯、西西和也斯。《酒徒》、《我城》和《剪紙》,也就成為了我心目中香港文學的三座神山。
其中劉以鬯令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他本來並不是香港人,而是來自上海。但是,讀他的作品卻完全不會懷疑那不是一個地道香港作家的文筆。雖然他的小說也常常提到童年和青年時代在內地的生活,甚至滲入一股強烈的南洋風情(他曾經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但這些異於香港的成份,卻和本地生活經驗毫無隔閡地並置和融合,形成了一種複雜的質感和多重的視覺。這絕不是今天簡化的「本土」標籤可以涵蓋和解釋的。

劉以鬯《酒徒》成為了作者心目中香港文學的神山。(資料圖片)
香港文學基因
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雖然是南來文人,但完全融入地道文化和生活,以香港作家的身分寫作,並且在編輯的位置上竭力推廣香港文學。另一方面,他很有意識地以「香港」為他小說的描寫對象,從微觀的日常生活細節,到宏觀的城市發展,都有鮮活的刻劃和獨到的呈現。所以,到今天我們所有的文學後人,都會一致地把劉以鬯先生作為「我們的作家」去敬重、去懷念。但我認為,我們不要忘記他的特殊背景,因為這也是香港文學本身的特殊背景。甚至可以說,這當中藏有香港文學的基因。
這種香港文學基因,我們可以往劉以鬯的作品中追尋。《酒徒》固然是他最經典的長篇,但最鮮明地呈現出基因結構的,應該是一九七二年的《對倒》。《對倒》分為長篇和短篇兩個版本,兩者就創作意念來說沒有分別──以集郵學的「對倒」(兩枚郵票正反相連)為意念,以雙線交錯的手法,描寫互不相識的兩位主角某天生活的對照。在這部小說中,可以提取出來的對照點可謂層層遞進,揭之不盡。最表面的是男性(淳于白)與女性(亞杏)、長者與少年、衰老與青春、理性與感性、道德與欲望、外來(南來男主角)與本土(土生女主角)、過去與未來等。這些對立的特性分別派發在兩個主角身上。但是,另有一系列的對照點,卻是同時出現在兩位主角身上的,例如現實與理想(想像)、外在與內在、物質與心靈、集體(社會)與個人、他人與自我等。從更高的角度審視劉以鬯的書寫,又顯現出另一層次的對照點——嚴肅與通俗、傳統與現代、創新與繼承、西方與中國、大陸與海外(香港、南洋)、外來與本土、形式與內容、寫實與虛構、藝術與生活等。這三層的雙線結構,從單篇《對倒》中互相交纏,上升到劉以鬯書寫的整體,再而擴展至整個香港文學,形成了美妙的雙螺旋鍵結,也即是上面說的香港文學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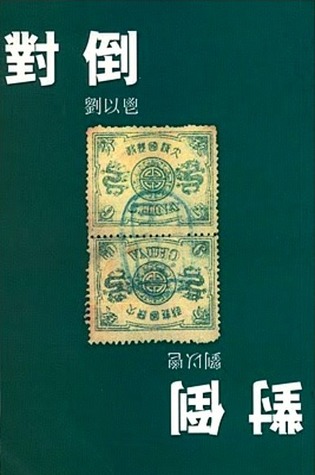
《對倒》鮮明地呈現出雙螺旋鍵結基因結構,也即呈現出香港文學基因。(資料圖片)
香港文學的特徵
我們不妨把劉以鬯的小說,讀成香港文學的基因圖譜。基因結構的根本形態,就是非單一的雙螺旋糾纏。永恆對照的二元線索,以多重組合的代碼互相配對,衍生出新的信息和意義,情況就像DNA雙螺旋通過不同的鹼基排序和鍵結,製造出複雜多變的有機物質、細胞、器官,甚至於整個身體。而男女染色體的結合,又衍生出完全不同的新個體。劉以鬯的作品說明了,創造力本身就是這樣的對照重組,而《對倒》非常精妙地演示出這個根本道理。所以,劉以鬯的非香港背景和經驗,不是可以忽視或者排除的偶然。不是「雖然他來自內地,但卻(全盤地)變得很香港」;而是,「他之所以很香港,(局部地)因為他來自內地」。劉以鬯文學的雙(多)重性和對倒性,建基於他的時空移動(遷徙)經驗,以及由此而來的開放和包容。而這就是香港文學的特徵。
雙城對倒的必然
我絕不是說,香港作家要有內地背景,或者香港作家都受到內地文學影響。只要看看也斯,看看西西,看看在香港成長的本地作家,我們也可以看到上面所說的香港文學特徵──雙螺旋基因的繼承──只是側重點可能有所不同。甚至是戰前的作家,香港文學開創期的一代,他們的文學基因也不可能是單一的、沒有對照結構的。侶倫、謝晨光、張吻冰那一代,立足的地方雖然是香港這個南方小島,但參照的卻是全國性的現代白話文文學,特別側重於上海的現代派,而上海的現代派又跟西方現代文學有所參照。由此觀之,劉以鬯之來自上海,是這個「雙城對倒」的必然了。
個人作品中的時代標記
劉以鬯先生接近百歲高壽,見證了同樣接近一個世紀的香港文學發展。遺傳基因的說法當然不只是強調繼承和不變的一面,也同時包含了演變甚至是突變的可能。所以,戰前一代、戰後至回歸一代(劉以鬯的文學生命期),以至回歸至今的一代,很明顯經歷了多番的變化。但是,無論是怎樣的變化,我們也要切記和警覺,不要輕率地切斷配對的鍵結。正如生命建基於基因的雙螺旋,「對倒」幾近文學的根本模式。「對倒」不是二元對立、黑白分明、互相排斥,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鏡像相連。單一而固定的「本土」和「自我」是不成立的,反之(全然的「外來」和「他者」)亦然。
我曾經連續十八年,在中文大學教授「香港文學欣賞」,書目上包括劉以鬯的《對倒》。每個學期的第一次功課,也有一題《對倒》改寫,要求學生模仿《對倒》雙線對照的形式,創作一個當下的故事。十八年來,從回歸之初,千禧的到臨,經歷了不同時代的政治、社會和經濟事件,以及種種科技用品、流行文化和生活風尚的改變,每一年的學生都把自己親身經歷的成長和時代,轉化為小說形式。金融海嘯、自由行、新移民、社區保育、反高鐵、反國教……這些時代標記都進入他們的作品中,在當中有對立的思想、相異的立場。雖然到最終每人都有自己一面的見解,但至少這是個反思的過程,是個代入不同角度的嘗試。
產生屬於自己的事物
因為是通識科目,學生來自不同學系,大都沒有文學閱讀的背景,更不要說寫作了。但是,多年來我見過無數令人驚喜的功課,就算未能算是優秀的文學作品,也至少是可讀、可思、可感的篇章。這是很多同學第一次寫小說,也很可能是最後一次。這是他們人生中唯一一次的文學創作,而他們在這個獨一無二的創作經驗中跟劉以鬯相遇,實現了另一種的「對倒」。《對倒》是一個神奇匣子。任何人把自己的東西放進這個奇妙的結構中,都可以產生出屬於自己的事物。劉以鬯先生留給我們的,不只是不朽的作品,也是這些作品所代表的,創造世界的形式──雙螺旋黃金結構。
(本文轉載自二○一八年六月十四日《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