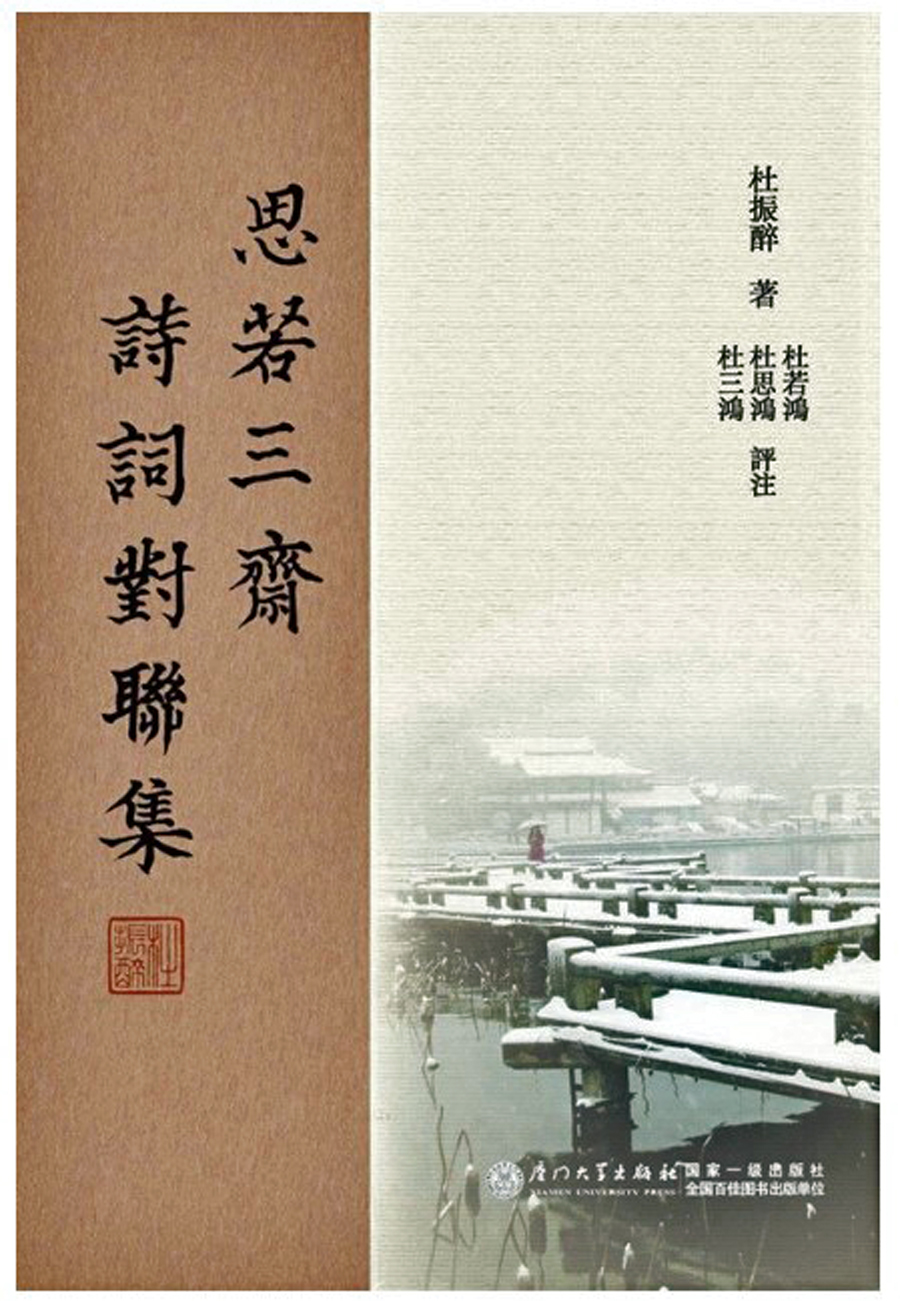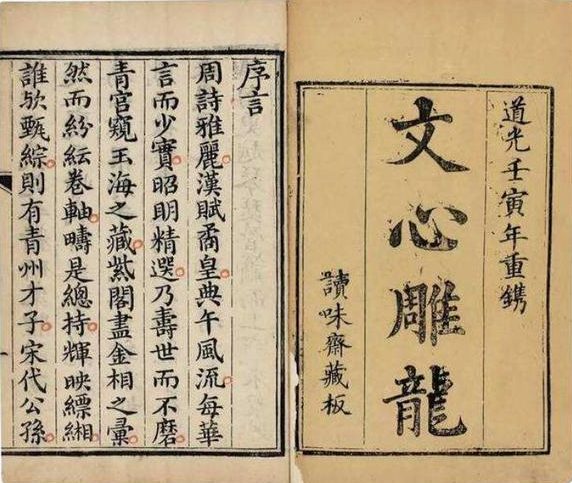王 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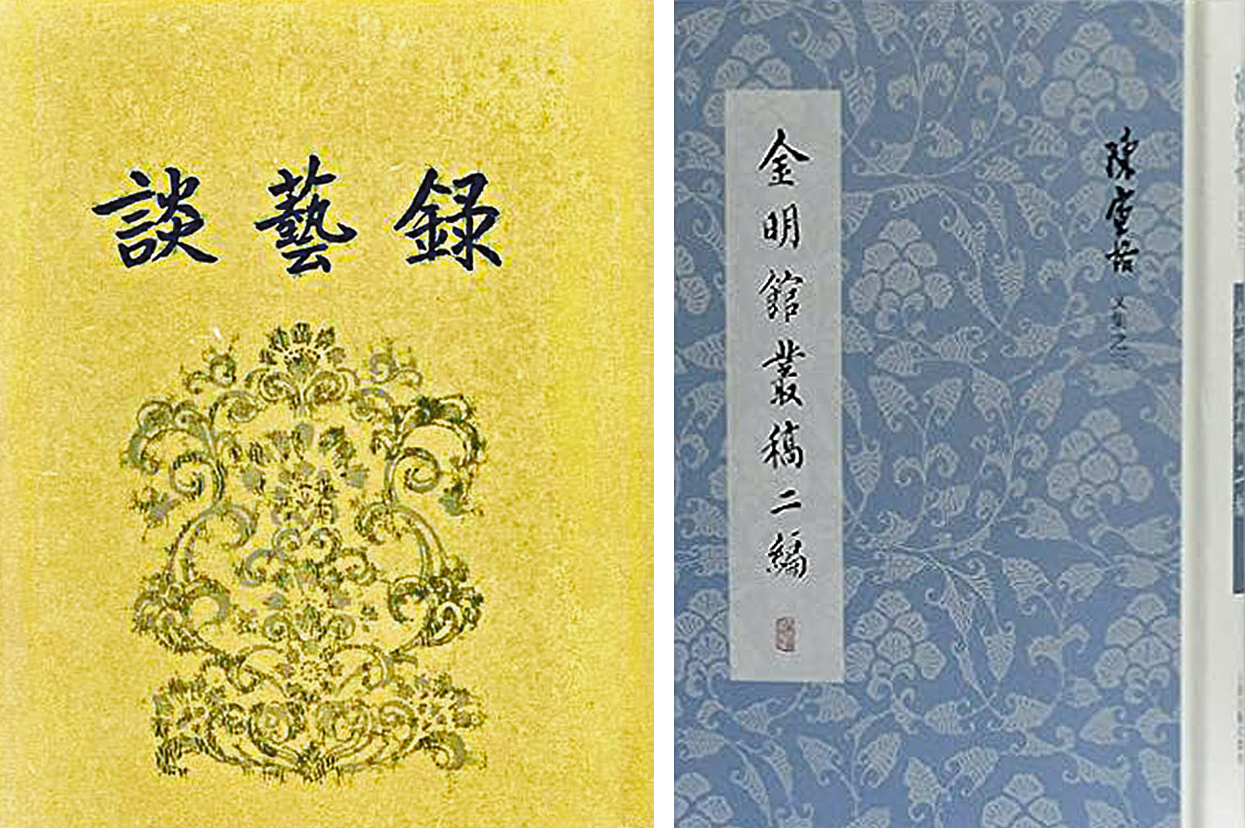
幾年前,《出版科學》雜誌請我為編輯出版業者、研究者推薦一本年度閱讀之書,當時我推薦了剛剛翻譯出版的《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今年,在第二十六個「世界讀書日」來臨之際,《中國傳媒科技》雜誌又請我為新聞傳播學領域從業人員推薦一兩本學術書,斟酌再三,決定推薦錢鍾書先生的《談藝錄》和陳寅恪先生的《金明館叢稿二編》兩書,以附驥尾。
這兩部書,是當之無愧的近代學術名著。不僅陪伴我度過漫長的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對我個人的學術工作影響很大,而且至今仍常置案頭、床頭,得暇即取閱之,每讀必有新的體會和收穫。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它們也經得起不同領域的讀者的批判和反覆閱讀。
先說《談藝錄》。追溯中國大陸人文學術「數字化」的歷史,錢鍾書先生的貢獻不可不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其指導、資助社科院文學所電腦室的建設,提倡、鼓勵同仁利用電腦處理古代典籍,既開風氣之先,亦屬「尊德性」與「道問學」並重之學人典範。不過,錢先生本人的治學風格,在今天看來,其實相當傳統:其述學文體,多為劄記、補註;其治學方法,雖受比較文學等領域之影響,但仍以廣泛搜集材料,從各種材料的排比、疏記、考辨中得出「卮言」「微言一克」為要,頗近乎乾嘉之學。與名著、皇皇四大冊的《管錐編》相比,《談藝錄》雖僅一冊,似亦能充分體現其治學旨趣、特色。此書雖為研究中國古典詩學之書,但正如其自序所言,「實憂患之書也」,細繹此書不僅能對中西古典文學、文化多所體悟,亦可知近現代學人在艱難時世如何以詩作為慰藉,啟迪我們仍須懷抱一顆詩心,在數字時代建構自己的精神家園。
再說《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先生在近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無需多言。但與錢鍾書先生以文學名世不同,陳先生乃以史學成家。文史二學,雖有殊異,但仍有不少相通之處,這是閱讀他們的著作時,首先能夠給予我們的教示。不過,由於他們的研究時常過於專門,讀者往往只限於一般治人文學術者,甚至專治古典文學、歷史者。但有沒有一部可以供人文社科諸領域乃至不同領域的讀者,可以廣泛閱讀、反覆閱讀的著作呢?竊以為,《金明館叢稿二編》便是這樣一部書,與中國古典名著、西方學術名著相比,亦可謂毫無愧色。此書並非是謹嚴之專書,而是一論文集,其中除收錄許多專論外,也囊括了陳先生的諸多名文,如〈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云:「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閱者當有所感焉。
不過,以上二書,乃為學術著述。我日常所讀者,除了這些專業研究,還有中國近代、現代、當代文學作品,及外國文學作品,各類文獻史料,但對這些文學作品、文獻的閱讀,雖或有一時一地之因緣,但究其實,仍與專業有關,可謂「專業閱讀」,因不讀不足以治近現代文學與文獻。此外,我最常讀的,為《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這兩種小書,雖然都是我自幼就開始閱讀者,亦即一般人所以為的發蒙之書,但數十年來竟不覺其蒙學、選學性質(取其廣義而言),而愈益體認其為可親可敬的傳統人文藝術經典,因此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構成了我「非專業閱讀」的基調和底色。

只是我小時候閱讀的《古文觀止》本子,不知何故,今已杳不知其所終。其後當然又擁有多個版本,既有「白文本」、註釋本,又有精裝書、口袋書,不僅滿足了我日常閱讀的需要,而且各有所長(亦各有其不足)。而最早閱讀的《唐詩三百首》,則有幸一直保存至今。此書全名為《繪圖註釋唐詩三百首》,是一古籍書店據民國時期刊行之石印線裝本影印而來,為家父上世紀中後期所購。因其中不止有詩有註,且有圖畫,殊感有趣,以致後來我自己購置了一些排印整理本,以及馬茂元先生編註的《唐詩選》,但讀來讀去,總覺得不如此一版本親切、有味。只可惜此書不比他書,除平裝、價廉外,用紙亦近乎清末民國書坊印製之大衆讀物,輕薄而易損,我少小時全無愛護書籍之觀念,因之時有隨意勾畫、批註之舉,但隨著馬齒漸長,頗覺其孟浪,而且越是年長,越不敢在此再添任何筆墨,以免佛頭著糞,有傷大雅。
而我的之所以嗜讀此二書,細想起來,亦可謂卑之無甚高論。讀《古文觀止》,誦先秦漢唐宋人古文,似可「養吾浩然之氣」;閱《唐詩三百首》,則以不獨此間蘊藏著中國古典文學、藝術、文化之精魂,且以無論時事風雲如何變幻莫測,科技如何驅動社會發展,我人如須安頓身心靈,仍不得不回向於此類傳統人文藝術經典,誠所謂「此心安處即吾鄉」,吾鄉即在斯文中也。
當然,拜時潮所賜,我的許多閱讀(無論「專業閱讀」,還是「非專業閱讀」),也都是透過個人電腦、Kindle、iPad、智能手機等進行的。但以上「四書」,以及一些重要的學術著作、文學作品及文獻資料,我仍喜歡閱讀紙書,且以一讀紙書為樂、為榮(雖然寒宅已跡近「書滿為患」)。除了近現代文學與文獻,我也研究一點書籍史、閱讀史、圖書館學史,近年來更對「數字人文」有特別的興趣。從「數字人文」的角度來看,閱讀、收藏紙書的興趣,或可視作一種紙質媒介時代所遺留的浪漫、頑固的習慣,即便不能說是被革命、鬥爭的對象,也萬難稱得上「先進」、「進步」;但從傳統學術的角度來說,因由紙書市場面臨嚴峻挑戰、紙質報章雜誌不斷關門歇業、「數字閱讀」逐漸成為主流的閱讀形態等狀況之發生,恰須我們較之前任何時代更珍惜各種與紙書有關的因緣,常常能盤桓於圖書館、書店、書攤、舊書肆,嗅聞那一縷縷書香,奉上自己的一瓣瓣心香,透過無盡的書籍的閱讀、收藏、利用與製作,將紙書帶給我們每個人的記憶、體驗、感覺和認知,以不同的形式傳遞給其他的讀者。就此而言,閱讀、照管紙書,促進其流布、利用,乃至寫作、出版紙書,皆可看作是對日趨式微、邊緣的人文精神與人文傳統的一種守護、捍衛和聲援,而非是一種已顯「保守」、「落後」、「過時」的趣味、情懷和習慣,或是一代又一代「好書之徒」、「獵書客」的物證與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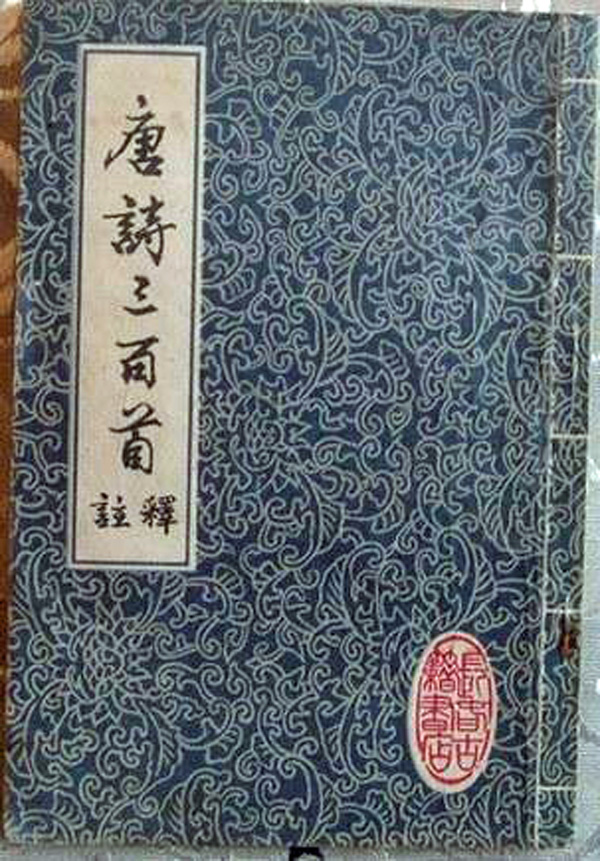
由此推而廣之,任何閱讀實踐、行為,不僅是個人的、私人的,不僅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歷史,同時也具有了公共性和未來性。換言之,竊以為,並不存在那種單純的、所謂的「個人閲讀史」。無論是我們對自己的「個人閲讀史」的記錄和整理,還是我們對前人的「個人閲讀史」的研究,都不能忽視它背後更大的歷史、社會網絡與其中所潛藏的時代精神等複雜因素。也因此,我個人的「四書閱讀史」雖然微不足道,但也並非只是一個人文研究者切忌的記憶、體驗、感覺和認知,一種際此之世自覺的選擇、承擔和實踐,或亦是我人如何因應不斷變化中的當代閱讀史的一個註腳。
今不揣冒昧,稍作整理,並藉《香港作家》公佈於世,如能引起文林、學林、書林同道中人的共鳴與省思,俾此後既能「坐而論道」,亦可「起而行之」,則於願足矣。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日草於滬寓
(本文圖片為資料圖片)
王賀簡介:文學博士,《香港作家》網絡版作者、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合著;二〇一三)、《數字時代的目錄之學》(二〇二一),編有《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二〇二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