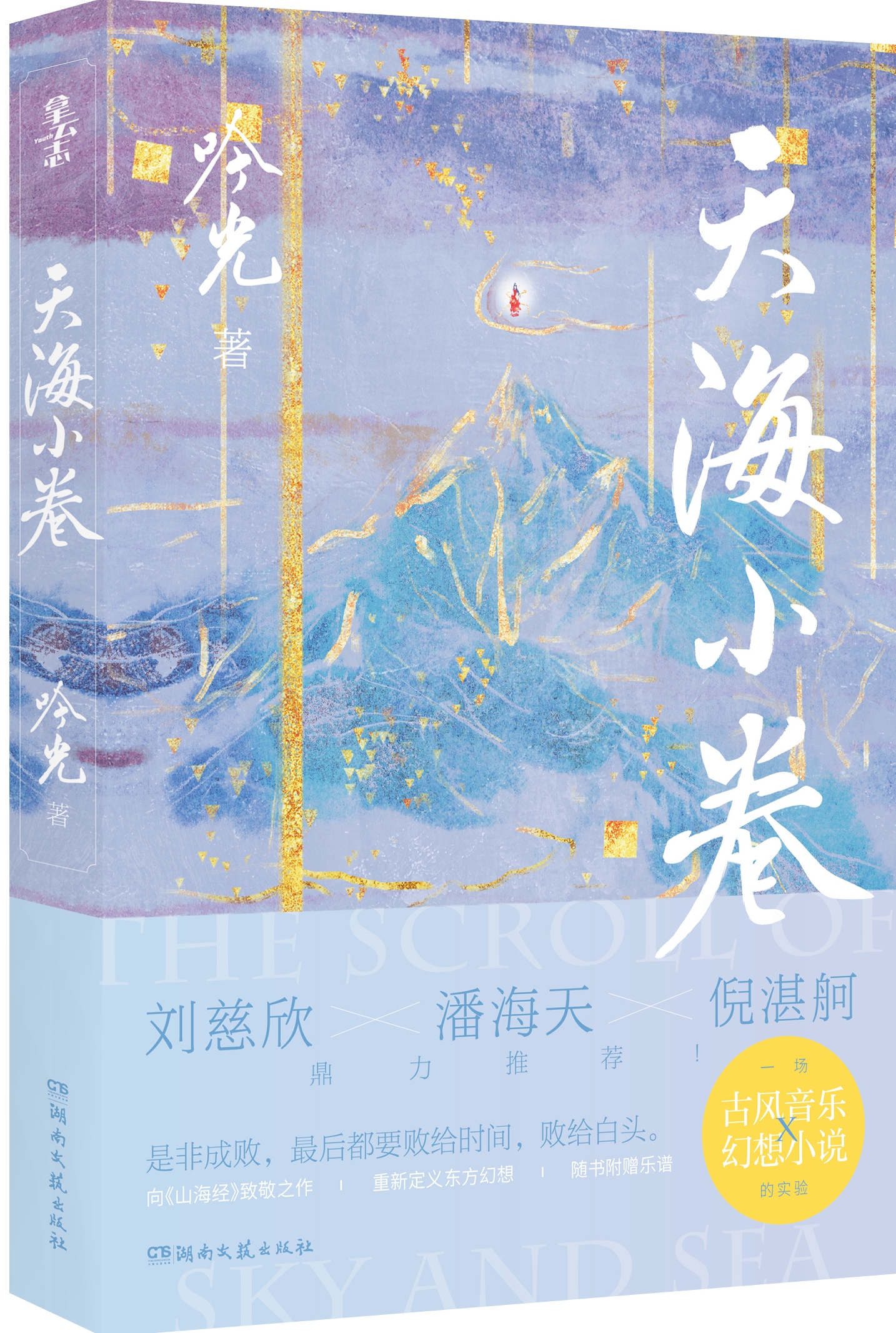阿濃
一個組織,定有積極成員和非積極成員,作聯也不例外。積極會員總是少數,非積極者定屬多數,我正是多數中的一員。
身為某氏宗親,希望有自己的祠堂或會所;身為某個宗教的信仰者,要有自己聚會的教堂、廟宇;身為某個行業的從業者,也希望有自己的公會或工會。
作家雖是個體戶,同樣需要一個同業組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香港作聯便是寫作人的祠堂、會所、公會,但不是教堂、廟宇,因為作聯允許會員有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做到有容乃大。
我之所以在作聯不積極,因為我在其他組織中扮演積極角色。我是教師,因此我是一個教師組織的理事;我寫兒童文學較多,因此我是香港兒童文藝協會的會員,做過理事和會長,如今仍是名譽會長。一個人時間和精力有限,無法在所有崗位上都積極。
關於作聯,我的記憶其實稀薄。我估計非積極會員對此次徵文響應者不會多,因此即使稀薄,也該一寫。

香港作聯便是寫作人的祠堂、會所、公會,但不是教堂、廟宇,因為作聯允許會員有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做到有容乃大。(本會資料室)
我記得曾敏之會長對後輩的愛護,我更尊敬他的正氣。如今他老人家仍寫作不輟,常在《明報月刊》上讀到他的大作。偶然我也會與他成為「同文」。
我跟劉以鬯前輩交往不多,只記得有一次在會所有活動,吃自助餐時我排隊在他身後,忘記當時說了些甚麼。當時他在編《香港文學》,後來約我在編輯部見面,為刊物寫一篇我與《青年樂園》的往事。寫當時兩份青年刊物中的《中國學生週報》的人多,不見有人寫《青年樂園》,這篇文字竟成史料。
記得那次活動進行時,參加者眾,有人要坐在會場較後的地方,看不到主席台,但聽到聲音。坐在後面的自然是非積極會員,記得我身邊有魯金,一位見多識廣的地方誌作家,我曾向他請教過一些問題,甚有得益,可惜如今他已歸道山。
跟作聯朋友接觸較多的是會刊的編輯們,包括梅子、陶然、蜜蜜。編輯會刊是辛苦事,因此每次約稿我都應命。而且跟這幾位朋友還有其他文字和非文字的往還。如今他們仍忙於創作和編務,精力過人。
我在港時張詩劍秘書長常親自送來他苦心經營的《龍香文學》,對張先生的熱心和刊物的精美留下深刻印象。
異鄉香港作家回港,作聯同人如果知道消息,都會熱情地來個招待會,我卻怕驚動大家,尤其是已屆高齡的前輩,因此常常是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只約會其中相熟的幾位。
不過「祠堂」、「宗廟」自有他的作用,前不久作聯秘書陳小姐就轉來一通電郵,是浙江湖州圖書館尋找阿濃的信。他們偶然發現我在湖州出生,想跟我聯繫,就找上香港作聯了。
值此香港作聯成立二十週年會慶,謹祝會務蒸蒸日上,會員創作碩果纍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