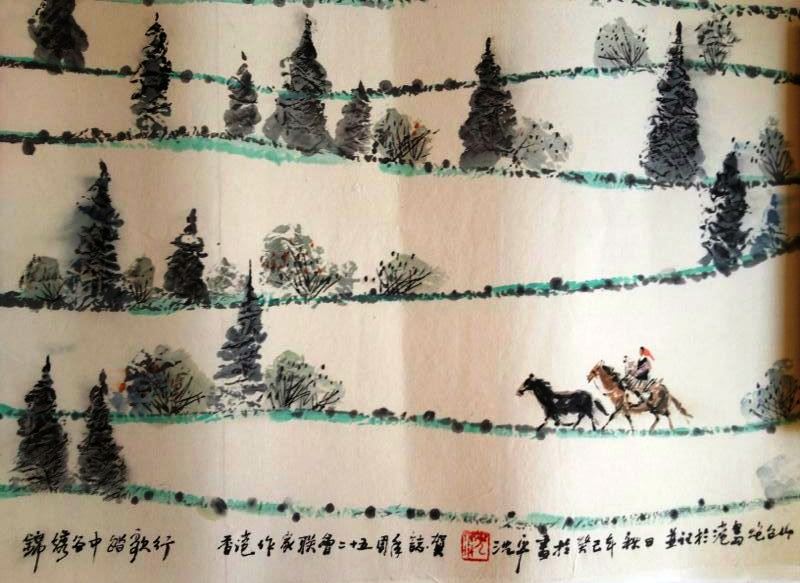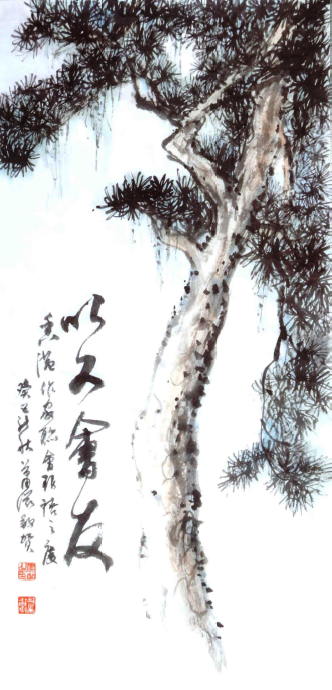楊永安
趙師令揚教授於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病逝,終年八十四歲。我在一九八○年正式投身趙師門下,趙師的品藻和言行對我的人生觀有很大影響。在此謹以哀思之離情寄託於緬懷的筆觸,追記趙師點點滴滴的生活片段。
教學與授徒
一九七七年,我進入香港大學文學院,因我喜愛歷史,所以只修讀中史和西史,但因西史年考的成績不太理想,所以在升讀二年級時,決定聚焦在中國文、史、哲方面發展,這是我主修中國歷史的其中一個原因。
一年級中史科目主要是介紹歷史入門,其中趙師的邊疆民族、歷史分期、人物評價等講堂令我重新審視中學階段的書本內容,開啟了未萌的心智。二三年級時,我唯一不走堂的,是趙師主講的明清史、政治思想史等課,他重視自由教學方法,傾向啟發學生思維,將過去史事與時事連結,並且意有所指。趙師不重視學子相信他在那些老舊大門內所教授的嶄新課題,事實上,由紅磚牆堆砌而成的象牙塔裏,不管做到與否,大家有的是到圖書館找尋推翻老師理論的欲望,這才是大學教育的真義。
我的個性一向疏懶,亦甚少思考將來的遠景,大三放榜後還未開始找工作。碰巧與昔年導師焯然兄和我幾個同屆好友如欽國、毅雄等諸兄北遊神州,於往華東漫長的硬臥廂中,眾人各言其志,我謂有意跟隨趙師修讀碩士,焯然兄慷慨答允替我傳達信息。如是者,我在七月中回港後便返大學找尋繼續進修的途徑,當時中文系的研究生配額只有三個,中文、中史、翻譯各佔其一,另一同窗松偉兄畢業成績較優,亦早向趙師申明升學意願,這在我返港前早已知道。豪麤如許的應聲緊隨著小子的叩門呼嘯而至,大門甫開,趙師以其一貫除下眼鏡、低首看公文的動作對來者投以瞪目的眼神,他不等待我鞠躬後第二句話,便直接的打斷我構思已久的講辭,直問「念書嗎?」也不等我答「是」,便直說「沒有工作的(意指研究生獎學金studentship)」;繼我慌忙回答「我僅為興趣」後,趙師即指「將來亦沒有工作的(意指將來亦無獎學金,甚至高等學位畢業後也不一定找到職位)」,隨著我一口答應,趙師便吩咐我草擬一份論文大綱給他過目,師徒關係就這樣在這簡單的幾句對話後展開。但事實上,趙師在我念碩士以至博士期間,一直在尋找機會填補我全無收入的慳囊,由教學助理(teaching assistant)、研究生獎學金、半職助教(half-time demonstrator)、暫時助理講師(temporary assistant lecturer),以至力薦我任教大學,全仗趙師「食言」之力,對驅趕不去的學生照顧有加。
在進香港大學前,趙師曾任職草創中的中文大學,因此他常暢論兩大的風雲人物和學術巨擘,曾有不少人建議他以此為題,補充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兩所大學的佚聞,但他一方面既表示述而不作,亦不屑撰寫掌故趣史,更重要的是,有些隱秘直筆書之或恐得罪早已過世的學者,惟曲筆出之則非趙師所願,所以除我們外,他總是在茶餘飯後與浩潮、達明、國燊、正光、萬雄等諸先生閒聊一下便算。此外,趙師歷任多屆高等程度中國歷史科試卷主席,曾有出版商多年前邀約他撰寫教科書或出任顧問等職,他一概婉拒謝絕。趙師課堂內外也有不少經典名句,他曾慨嘆清朝與日治時期,士夫走卒往往並非死於滿人或日人之手,實在死於漢奸之手;嘗稱有些人不宜多念書,否則將遺害社會;他亦不恥有些人常顧盼自得,總認為自己較其他人重要;又曾笑指人生在世,夠喫夠穿業已足夠,何必殷殷為利。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中環大會堂美心酒樓,港大中文系老師出席嶺南大學伍沾德博士伉儷傑出教職員服務獎頒獎禮。左起:陳遠止博士、楊永安博士、陳炳良教授、趙令揚教授、李雄溪博士(得獎者)、單周堯教授、李家樹教授。(楊永安提供)
閒居與生活
眾所周知趙師喜好熱鬧,茶飯宴飲成為他生活的部分,縱使近兩年身體漸不如前,但一旦門生舊遇招聚,遠方來朋叩扉,若情況許可,他仍欣然赴會。趙師在家頗能燒飯做菜,八九十年代菲傭阿福休假時,他親自到第二街興華買麵條,到結志街市場買豆腐、芽菜作炒料,偶爾光顧華豐燒臘,家居飲食甚為簡樸。但近廿年已罕有下廚,加上後來腎患繞纏,師母吩咐傭人煮菜務必清淡,反而令他亟欲光顧坊間食肆。
趙師不太著重筵席菜肴的貴賤,無論珍肴海錯,或山野清供,他隆重的是共良友而同席,對知交而飛觴。趙師素寓社交於飯聚,他愛湊興,西餐館不能提供他笑聲喧天的場地,他重視中式圓桌主客混融的陣式,較喜好侍應招呼,點菜作主,他甚至譏抨自助餐為無文化的飲食風俗。
趙師對粵、潮、滬菜均有不同的喜好程度。在八十年代的茶局裏,炸魷魚一度是趙師經常欽點的小食,原因是他指我們後輩好嘗烏賊滋味,惟事實只是他希望略沾句公誘惑的觸鬚;這慣技斷續的維持了幾十年,近七八年來,每次與恬昌先生飯聚時,他還硬說賴生喜愛九龍吊片,企圖以此為必然餐單。趙師這種心態於早年較明顯,雄溪兄與我當研究生時,趙師在一次周六的中午把我們拉到寧波菜館,二話不說便點了客紅燒圓蹄,在他品嘗一小片後,便把滅元重任交託兩個年輕人來承擔!然而,話得說回來,在我們念研究院時,他體恤學生收入有限,一切茶筵小酌,趙師每每爭掏腰包付賬,這亦是很多學長學弟們在出身後爭相宴請趙師的原因之一。除中菜外,趙師竟也思念咖喱風味;千禧前身體健康時,常嚷著要拉我們去國際咖喱館;年初心臟鬱翳,留院三周觀察,皆因在家饞嘴,多吃斯里蘭卡咖喱所致。

二○一五年十月,在中環翠亨邨酒樓,趙令揚的朋友、學生齊賀其八秩大壽。前排左起:羅球慶教授、趙令揚教授、賴恬昌教授;後排左起,全是趙教授學生:楊永安博士、李焯然教授、許振興博士、楊文信博士、梁紹傑博士。(楊永安提供)
在衣、食、住、行中,衣著並非趙師重視的要務,如要之,簡潔是他的特點。以色彩來說,異常沉實的白、藍色恤衫,早期曾穿白色上衣,後來一律穿藍、灰、杏色西服或上衣,灰、藍、啡色西褲,一切配搭不脫上述五色。順道一提的是趙師衣袋中的寶貝,小梳一把是常備的法寶;他不太喜歡髮乳、髮臘,故頭髮偶有披散,每當離開辦公室時,他必掏出梳子梳理一番,近數年華髮漸稀,昔日招牌動作已成追憶。趙師亦不注重配飾,他把紙幣、信用卡等都放在襯衣或西裝袋,方便掏出付賬;他插在上袋的都是廉價原子筆,用完即棄,亦不怕遺失。趙師曾笑稱不少友人、學生等都先後以錢包、名筆為贈,但他仍然保存一貫的自我風格,順手拈來更勝探囊取物。二○一二年中文學院自巍峨的本部大樓遷至明亮的逸夫教學樓時,振興、景輝、文信、偉幟諸兄和我在清理趙師辦公室之際,我還在那些塵封的抽屜中,找到上述一盒盒尚未拆開的禮物。我珍而重之的包裝入箱後,還千叮萬囑告訴趙師這些就是他曾提及的禮品,請他親自處理,但我相信時至今天,那紙箱仍是原封不動的放在他府上的房間之中。
正因趙師崇尚簡約,他對家居的要求也不太高,亦不注重擺設。自大學宿舍時代起,至現今私人住宅為止,趙師家中的布置以實用為主,黑色皮梳化和圓形木餐桌是貫串著前後家居的特色,縱偶有擺設,若非他人餽贈,即為早年外訪或學術會議時的紀念品。一九九九年他四出挑選房子時,也直指自己對樓宇要求十分簡單,四平八穩,能多一書房固佳,但三房一廳,足以給師母養老,能安頓兩位公子,亦於願足矣。
趙師身裁較肥胖,但腳掌略窄小,若干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步伐和平穩度。千禧以還,趙師搬到現址居住,約年餘後的一個茶聚中,他還高興地與我們透露剛成功在蒲飛路乘搭公車抵達中環的喜訊!二○○三年新加坡國立大學為他舉辦榮休學術研討會,在他拾級上台致詞時,在台下的我才理解趙師上落巴士和小巴均存在困難,這亦是他慣以計程車代步,或不介懷朋友接送的原因;誠然,一如其性格,縱使市內公幹的車資,他亦懶得向大學申報。
旅行並非趙師喜好的消閒活動,八十年代尚在暑期間舉家返回悉尼休假三數周,這已算是最悠長的假期;千禧後,師母擔心他日差的身體,長期在港陪伴在側,返澳渡假已成絕響。在出外開會時,除非主辦單位接送,趙師不喜參觀風景勝跡,他多光顧投棧後就近較可靠的小館食肆,或索性在酒店餐廳或酒吧用餐,主因無非是他活動能力不佳,加上腸胃亦不太好,恐防隨處進食將導致拉肚子。
心如澄海映朗月,人若醉霞浮浪花
九十年代中是趙師身體漸轉衰退的時期,自武漢會議後,因酒店房間過於悶熱至回港染上肺炎,過往大家都害怕走進趙師寒若冰川的辦公室,自手術後,他已調升了空調的溫度。近年腎病,也有血糖問題,身體日差,加上心臟血管閉塞,以至腹腔感染也未能清洗。
很多人認定豪放派詞人蘇軾是個十足的酒徒,皆因他遺下不少和飲酒有關的作品,但事實上,東坡先生既不縱酒,且是個酒量偏淺的墨客。同樣地,很多不知就裏的人,認為趙師好飲酒食肉,事實上,他寓情意於酒意,卻從不醉酒狂歌;他喜愛濃膩食物,但限於淺嘗即止,凡事看似不拘小節,惟處處均留情面。綜合而言,豪邁而不失大體,面惡而實在心慈,浮華但卻簡樸,更重要者,是看淡千秋世情,這正是趙師人生的寫照。
(本文轉載自《明報月刊》二○一九年八月號)
楊永安簡介:趙令揚弟子、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