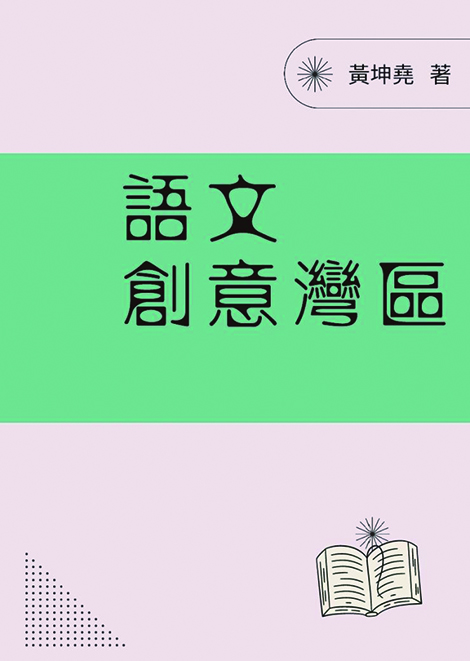潘耀明
廣州,這座歷經二千多年文化洗禮的南方都市,始終是漢語文學版圖中一座不可忽視的豐碑。從近代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的宣言,到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的實踐;從魯迅在中山大學播撒的火種,到當下「新南方寫作」的先鋒實驗,廣州文學始終以開放包容的胸襟、銳意革新的姿態,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的碰撞中,構建起獨具嶺南氣質的文學譜系。
廣州文學的基因裏鐫刻着敢於突破傳統的精神密碼。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歐陽山的《三家巷》以細膩筆觸勾勒出革命洪流中的市井煙火,黃谷柳的《蝦球傳》則通過流浪少年的眼睛,映射出殖民地的複雜肌理。這些作品不僅奠定了廣州城市敘事的雛形,更以「小人物見證大時代」的敘事策略,開闢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路徑。改革開放後,章以武與黃錦鴻的《雅馬哈魚檔》捕捉市場經濟初興時的市井活力,而當下林棹的《潮汐圖》則以魔幻筆法重構十三行的全球貿易圖景——廣州作家始終以文學為鏡,既映照歷史轉折中的個體命運,亦折射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獨特軌跡。

廣州文學的精神底色,是「雄直」、「風骨」與「市韻」美學的交融。圖為廣州塔(小蠻腰)。 (明報資料室)
廣州文學的獨特魅力,在於其將市井煙火昇華為美學哲思的能力。葛亮《燕食記》中,一盅兩件的飲茶文化成為百年粵港變遷的隱喻;宥予《撞空》裏海珠橋下的出租屋與生活,精準刻畫出當代青年的精神漂泊。這種「以日常見永恆」的敘事智慧,恰如珠江水的特質:表面波瀾不驚,內裏暗湧深流。更值得關注的是,新一代作家如索耳、路魆等,將粵語方言、嶺南文化等元素轉化為敘事實驗的燃料,使《細叔魷魚輝》這樣的作品既扎根地域,又超越地域,成為探討普遍人性困境的文學樣本。
廣州文學的精神底色,是「雄直」風骨與「市韻」美學的交融。黃禮孩的詩歌在茶樓炊煙與星際漫遊間自由穿行,鄭小瓊以《女工記》為流水線生命賦形,而張欣的都市小說則始終保持着對商業文明既擁抱又審視的辯證姿態。這種「在地性」與「世界性」的辯證,在「新南方寫作」浪潮中尤為凸顯:朱山坡從南方民俗走向非洲荒原,王威廉在科技倫理中注入嶺南思維——他們以文學證明,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站在嶄新的歷史階段回望,廣州文學始終如珠江入海般:既保有源頭活水的清澈,又敢於在鹹淡水交匯處激蕩出新的生命力。這在在昭示,真正的文學高地不在於標榜地域特色,而在於如何將一方水土的呼吸,轉化為人類共通的情感密碼。這正是廣州文學給予當代漢語寫作最珍貴的啟示——唯有扎根大地,方能仰望星空。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明報.明月灣區》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