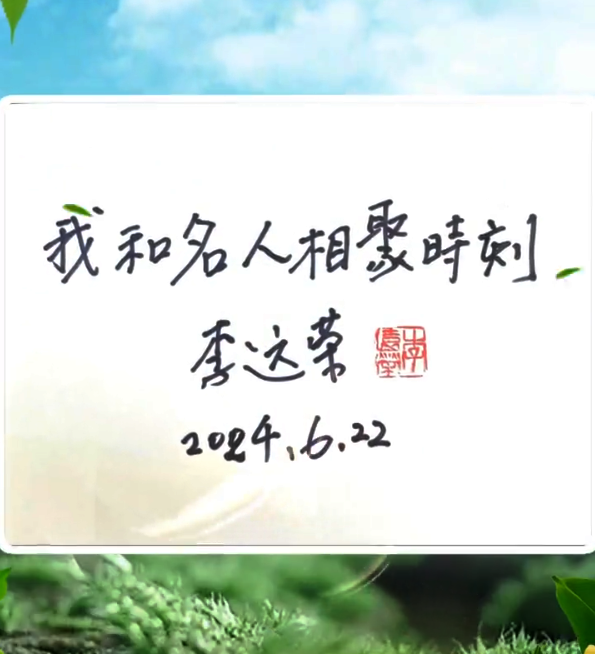東 瑞

劉以鬯與王家衛
在康城電影節獲特別技術獎、王家衛導演的《花樣年華》電影落幕時打出「鳴謝劉以鬯先生」的字樣。看來當時必有不少觀眾很奇怪,《花樣年華》和劉以鬯有什麼關係呢?
《花樣年華》多次引用《對倒》裏的詞句作為字幕。
其一是「那是種難堪的相對。她一直羞低著頭,給他一個接近的機會。他沒有勇氣接近。她掉轉身,走了」(《對倒》一一九頁)其二是「那個時代已過去。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對倒》九十六頁)其三是「那些消失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他一直在懷念著過去的一切。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對倒》九十六頁)
王家衛看來很欣賞這些充滿懷舊氣息、並散發著感傷意味的敘述語言,用它詮釋電影中人物的心境,並以字幕作為鏡頭的過度。
但「鳴謝」的意思應不止這些字幕的出處和摘錄嗎,而是整部《花樣年華》的構思和靈感。
王家衛在《對倒》寫真集前言中有這麼一段很重要的話:「《對倒》由兩個獨立的故事交錯而成,兩個故事的主要人物分別是一個老者和一個少女。故事雙線平行發展。是回憶與期待的交錯。對我說,tete-beche」不僅是郵學上的名詞或寫小說的手法,它也可以是電影的語言,是光線與色彩、聲音與畫面的交錯。」而最明顯的是這麼一句:「tete-beche甚至可以是時間的交錯,一本一九七二年發表的小說,一部二〇〇〇年上映的電影,交錯成一個一九六〇年的故事。」
這使我想到劉以鬯和王家衛兩人,雖用的和兩種不同的媒介。但在很多方面相似。
劉以鬯重視文學的藝術價值而不問它的市場價值,王家衛也如是;劉氏的小說沒有故事情節或情節不強,王氏的電影也如是;劉氏小說一部有一部的創意,引起讚嘆;王氏幾乎沒有一部不獲獎……「英雄識英雄」,變成是很自然的事了。

《對倒》和《花樣年華》
劉以鬯《對倒》的內容和結構特點,以楊義概括得最好:「淳於白象徵沉落的蒼老,亞杏象徵浮薄的青春。這一老一少從不同的方向或坐巴士,或步行,來到香港旺角商業區,對相同的街景、車禍和劫案,戲劇性地激發了不同的、或灰暗或粉紅的意識流…..作品用類乎電影蒙太奇的連綴方式,交替敘述兩個人物的街景見聞和意識滑動」,離中見合,同中顯異,關照呼應,於意象跳躍之處未失結構安排的細針塵縷。「這種把意識流手法用於陌生人街頭對行,從而產生隔代人不同心態的強烈對比的敘事謀略,實在是匠心獨到的創作。」
這種「電影感」,看來是王家衛喜歡、看中《對倒》的原因之一。不過,從小說語言變成電影語言,要照搬《對倒》顯然很困難,王家衛從《對倒》的結構和形式獲得靈感,觸發了《花樣年華》的故事內容。他設計了梁朝偉和張曼玉這兩個同時代的人物,很偶然同時搬入一棟上海人聚居的同一層唐樓,毗鄰而住。梁是報館編輯,張是寫字樓女文員,那麼巧,梁的太太常常不回家,而張的先生不時出差日本。她常為三餐而下樓買粥什麼的,在梯間經常和上下班的梁朝偉相遇。張衣著入時。正處「花樣年華」而心境寂寞,不免引起梁的關注;而梁的淳厚老實,常是一個人在家也惹來張曼玉的留心,但他們顧忌別人的閒議,思想還是挺保守的,始終保持一段距離。直至一次相約出外吃飯,從彼此的探詢,竟意外地發現兩人的配偶正背著他們搞婚外情……情節急轉直下,從同病相憐到互生愛意,但也一直克制著。梁為逃避這段感情到新加坡,張追之卻沒有遇上;梁回到香港,也一線之差,沒能再見張……
電影結束,故事情節淡淡的;敘述婚姻的陰差陽錯中一對小男女囿於傳統觀念下戀情的悲劇;命運讓他們走在一起,也是命運令他們始終沒能完滿地結合,這不正是《對倒》中兩個不同時代男女「無緣無分」「擦身而過」的變奏嗎?
(本文圖片為作者提供)
東瑞簡介:原名黃東濤,香港作家。一九九一年與蔡瑞芬一起創辦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迄今,任董事總編輯。代表作有《雪夜翻牆說愛你》、《暗角》、《迷城》、《愛在瘟疫蔓延時》、《快樂的金子》、《轉角照相館》、《風雨甲政第》、《落番長歌》等近一百五十種,獲頒第六屆小小說金麻雀獎、小小說創作終身成就獎、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傑出貢獻獎、全球華文散文徵文大賽優秀獎、連續兩屆台灣金門「浯島文學獎」長篇小說優等獎等三十餘個獎項,連續於二〇二〇年、二〇二一年榮獲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十大新聞人物榮譽。曾任海內外文學獎評審近百次。目前任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會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國立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名譽會長、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名譽會長等。